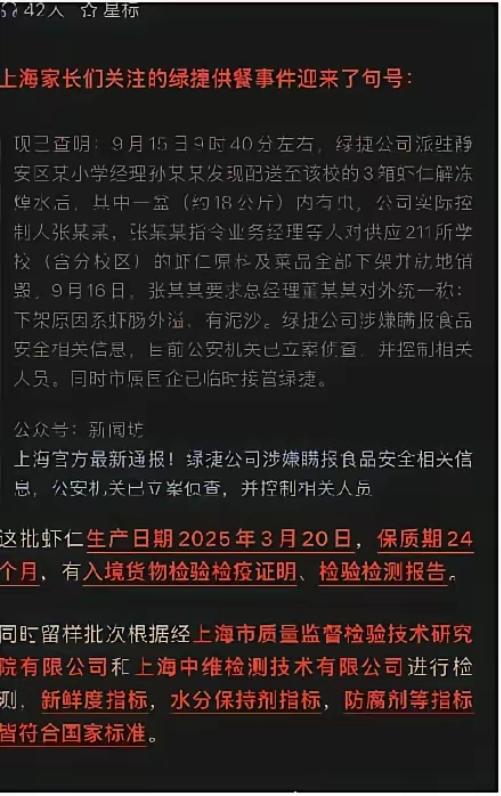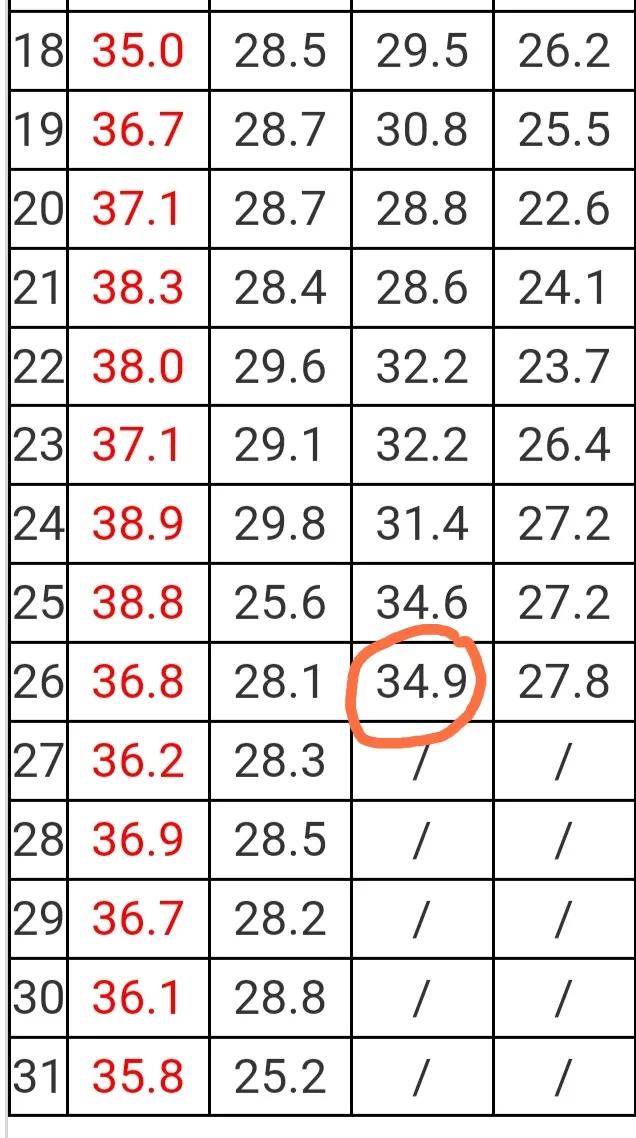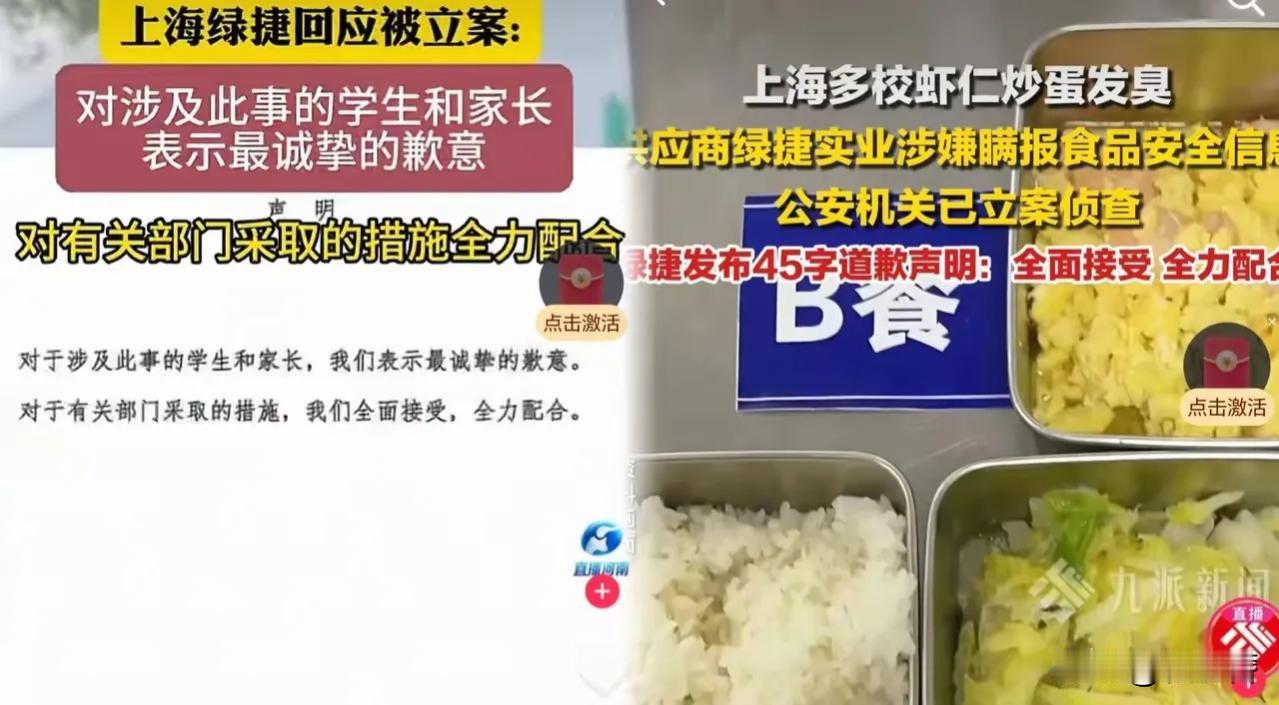“家?不记得了……只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个大坑……”
“名字?好像姓刘吧……‘文强’是我自己取的,听人讲上海滩有个许文强……”
今年8月,罪犯刘文强(化名)从上海市吴家洼监狱出狱了。可这样一个连姓名和户籍都不知道的人,要如何回归社会、怎样走向新生呢?这个故事,要从他入狱时说起。
确认身份
刘文强因犯盗窃罪被判处6年6个月,2020年至上海市吴家洼监狱服刑。他随身携带的档案薄得可怜,是一个“双重三无”人员——既无身份证、无户籍、无家庭住址,也无亲人会见、无通信、无汇款。
“‘三无’人员本来就很难管,‘双重三无’更是难上加难。”主管民警蔡宏清说,没有根,就没有牵挂,改造无从谈起。帮他找回身份,确认他是谁,找到他的来处,是稳定他情绪、引导他改造、最终确保他顺利回归社会的关键,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然而,其中难度超乎想象。公安机关在居民身份证信息系统进行了多次人脸比对,却毫无收获;“网上追逃”信息库也查无此人。唯一的突破口,只剩下刘文强口中那些模糊的地理记忆——“江西”、“大坑”、“XX村”。
监狱狱政科民警在电子地图和行政区划资料中反复查找,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名称可以匹配、且有显著“大坑”地貌特征的村子。在与江西省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后,监狱民警终于得到了一个关键信息:该区域历经多次行政区划调整,记忆中的地名可能与现实存在偏差,有一个叫“某某”的乡镇,其地理特征与刘文强的描述最为接近。
2021年1月,吴家洼监狱将一份详细描述刘文强特征及自述信息的协查函,连同他的照片,寄往了该乡镇派出所。春节临近,在外务工人员集中返乡。当地派出所民警利用这一人口聚集的时期,将刘文强的信息打印成告示,在几个村落密集张贴;村干部也上门走访,询问村中的老人,是否有三十多年前失踪的男孩信息符合描述。然而,经过一个月的排查,没有一户人家能对上号。

就在监狱考虑是否要派人去江西实地走访时,一位名叫刘凡(化名)的村民得知监狱正在调查,急忙赶到派出所,激动地说:“我看到描述,这太像我三十年前走丢的堂弟了!”于是,刘凡拨通了吴家洼监狱的电话,道出刘文强的身世——
刘文强,出生在1980年前后,幼年丧父,母亲患有严重的智力障碍,后改嫁他乡。年幼的他被托付给伯父(即刘凡的父亲)抚养。刘文强9岁时,因琐事与堂兄堂姐发生激烈争执,从而离家出走,音讯全无。
“我们家里人像疯了一样找他,广东、福建、上海,能想到的地方都找遍了。”刘凡说,得知堂弟可能还活着,且在监狱服刑,亲人们悲喜交加,都表示希望能尽快见面认亲。刘文强在得知找到亲人后,改造的积极性也高涨起来,还获得了减刑机会。
再起波折
然而,就在今年8月刘文强出狱前夕,事情又发生了转变。
DNA鉴定显示,刘文强与生母存在血缘关系,但与抚养他的“伯父”不存在生物学上的关系,他真正的父亲无从得知。
于是,原本热情高涨的堂兄堂姐们,态度一下子发生了转变。当监狱教育科民警再次联系他们,沟通刘文强即将刑满释放、需要家属配合落户和安置帮教事宜时,电话那头很激动:“户口?不行!不能落到我们家!他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没联系,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家属的拒绝,将刘文强推到了悬崖边缘。没有身份,意味着他刑满释放后还是“黑户”。有犯罪前科,在社会上谋生的难度很大。一旦处置不当,他很可能再次犯罪,六年的改造也将前功尽弃。

“监狱党委决定将他的刑释衔接工作提升到最高优先级,成立了多部门骨干组成的‘刘文强刑释衔接工作专班’,制定了工作预案,确保他在剩余刑期内的思想稳定和行为可控。”蔡宏清说。
与此同时,监狱民警也在努力进行外部协调。经过数次电话沟通,刘文强同母异父的弟弟王军(化名)同意将他的户口落在其母亲的户籍地址上,他的堂哥堂姐也表示愿意来接他。
监狱又多次与当地沟通,敲定了刘文强的回归方案——监狱民警将其送回原籍,与当地司法所对接;当地公安机关在收到监狱提供的材料后,7个工作日内为其完成落户手续;当地司法所和村委协助其尽快申请办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司法所根据技能培训情况,联系辖区内企业,争取为其匹配适合的就业岗位。
千里护送
释放当日,监狱派出三位民警护送刘文强返回千里之外的老家。警车上,他显得格外拘谨,一直蜷缩在座位上,怔怔地望着窗外。
途中,他再次断断续续地讲起自己的经历:9岁离家的恐惧,睡桥洞的寒冷,在工地扛水泥的艰辛,做小工的卑微……“太饿了,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偷点吃的、偷点钱。”他摩挲着粗糙的手掌说。在监狱劳动所得的七千多元,是他此时唯一的“资产”和微弱的底气。
抵达目的地后,监狱民警与当地完成了交接。几位堂哥堂姐姗姗来迟,他们一边打量着刘文强,一边抛出很多问题“DNA结果到底怎么算?他到底和我们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么多年在外面,谁知道他变成什么样了?以后还会不会再偷东西”“生活费我们可以凑一点,但住一起不行,各家都有老小,担不起这个责任”……
家人当面的明确拒绝,让刘文强更加沉默,他蹲在司法所院子外的花坛边,用力抠着手上厚厚的老茧。更雪上加霜的是,司法所工作人员此时得知,之前联系好愿意接收他做学徒的一家小型汽修厂,老板临时变卦了。

“没有亲情的助力,还没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所,他短时间内再犯的风险很高。”监狱办公室副主任张盼盼说,“他有七千多块钱,当务之急是找个落脚点。村里有没有闲置的、能简单住人的房子?租金便宜点的?”
村支书听闻,表示村头有间老屋空着,简单收拾一下就能住,“每年500块,我跟房东说。我们还可以安排个热心的村民,带他一周,认认路,买买东西,教教他怎么在村里生活。”
在监狱民警说明了刘文强在狱内参加汽修培训的情况后,当地司法所所长表示:“工作的事,我再想办法,镇上有几家汽修厂、摩托车修理铺,我一家家去问。”
当村支书将临时住房和工作正在落实的消息告诉蹲在门外的刘文强时,他很激动:“真的?有地方住?能学修车?我愿意,不给钱也行,有口饭吃就行!”
第二天一早,当监狱民警准备告别时,发现刘文强换上了一身新衣服。“堂姐一大早送来的,说是给我换洗。”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拉了拉衣角,脸上露出一丝腼腆。临别时,刘文强紧紧握住监狱民警的手,反复道谢。
“每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是多部门、多环节协同作战的结果。它体现了‘惩治犯罪’与‘创造新生’的辩证统一,是将‘以人为本’、‘修复性司法’理念贯穿于刑罚执行全过程的必然要求。”吴家洼监狱党委委员、政委王自龙说,做好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挽救一个个体,更在于有效预防重新犯罪,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为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建设夯实根基。
栏目主编:王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