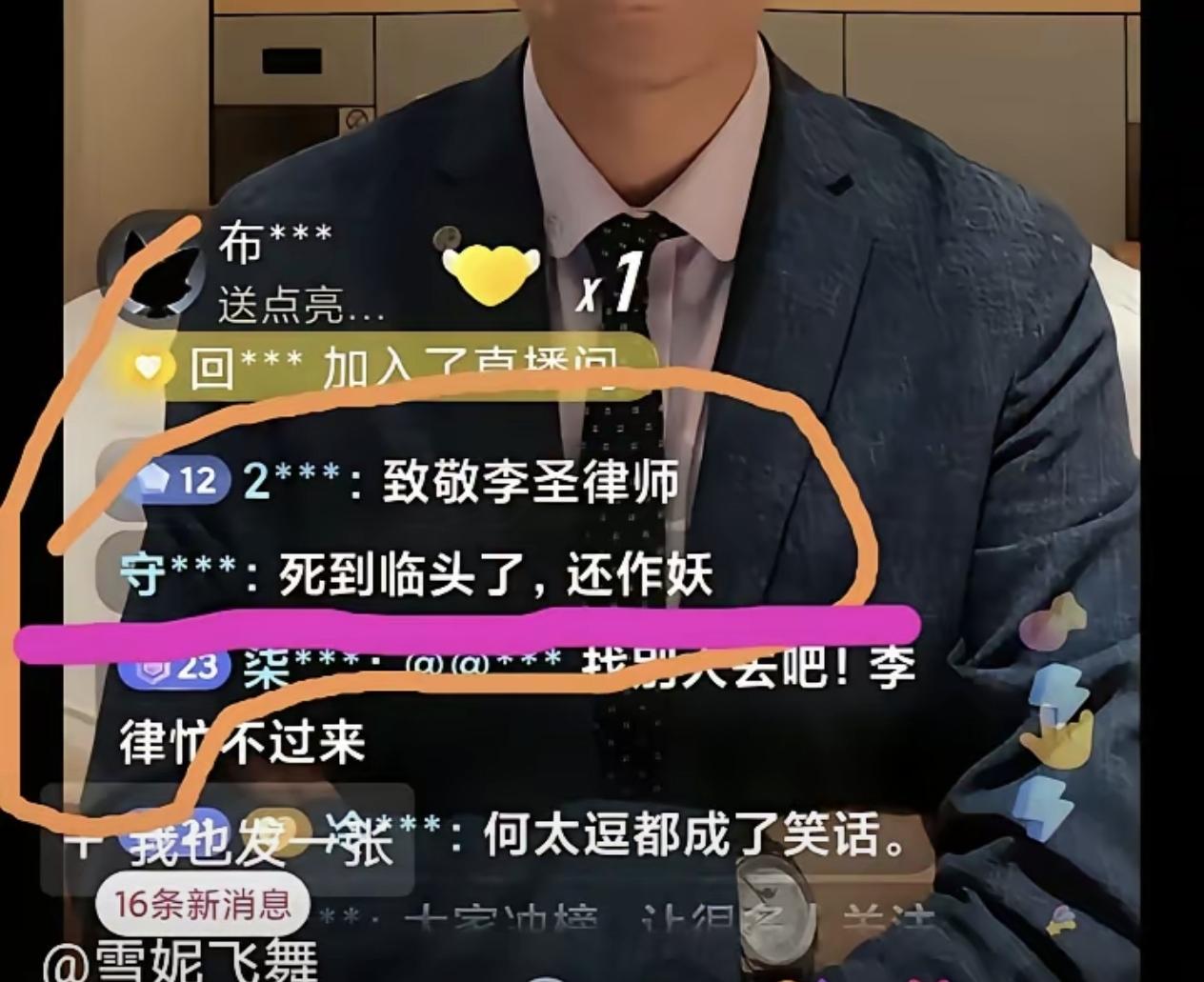1956年,35岁农民咳嗽10年,竟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咳嗽,“哇”的一声,一个黑色且带血地异物喷射出来,妻子将异物拿给医生看,谁料,医生看完居然立马冲出病房报警。 县博物馆的展柜里,一颗锈迹斑斑的步枪子弹头静静躺在绒布上,弹尾残留的暗红痕迹虽已褪色,却仍能让人联想到它曾嵌在人体里十年的岁月。 展柜旁的说明牌上,“1946年韩家寨战役遗留,1956年由高其煊咳出”的字样,总能吸引参观者驻足——没人能想到,这颗普通的子弹,背后藏着一位农民与战火、病痛抗争的十年人生。 高其煊的名字,在山东马庄村的老人口中,总是和“能扛”两个字连在一起。 1956年深秋之前,村里人只知道这个35岁的汉子有个咳嗽的老毛病,咳起来能把院里的梧桐叶震得簌簌落,却没人知道他每天清晨扶着犁头咳到直不起腰时,肺里正有一颗子弹随着呼吸摩擦着器官。 直到10月23日那天,王桂花拿着从丈夫嘴里咳出的“黑疙瘩”冲进镇卫生所,这个秘密才被撕开一道口子。 卫生所的张志远医生接过王桂花兜来的异物时,指尖最先触到的是铁锈的粗糙感,再仔细一看,弹头上粘着的血丝和肉丝让他瞬间攥紧了拳头。 1956年的中国,民间武器早已收缴干净,人体里咳出子弹头,这绝非普通的健康问题。 他没敢耽搁,锁好抽屉就摇通了县公安局的电话,话语里的急促让接线员都察觉到了异常——“马庄有村民咳出子弹,可能是重大案件线索!” 民警赶到高其煊家时,看到的不是预想中的“可疑人员”,而是一个虚弱地蜷在炕头的农民,嘴角还沾着未擦净的血。 面对荷枪实弹的民警,高其煊只是慢慢坐起身,用粗布擦了擦嘴角,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这子弹是1946年韩家寨打仗时留下的,国民党54军打的。” 这句话让满院的紧张气氛突然松了下来,却又在每个人心里掀起了新的波澜——这个天天在田里种地的汉子,竟然当过兵、上过战场。 高其煊记得清楚,1946年7月的韩家寨,炮火把天炸得通红。 他还是华东野战军的副班长,带着12个战友守阵地,对面是国民党的精锐54军。 冲锋号响的时候,他刚喊出“冲啊”,腰部就被一股巨力击中,低头一看,肠子正从伤口里往外冒。 他没敢多想,左手把肠子塞回腹腔,右手扯下皮带勒紧伤口,抄起步枪又冲了上去,直到敌人撤退的号声响起,他才眼前一黑栽在阵地上。 战友们把他抬到三里外的战地医院,那是个用地瓜窖改成的临时医疗点,只有一位老医生和两个卫生员,医疗器械是开水煮过的剪刀,消毒用的是白酒。 老医生检查后摇着头说,子弹卡在右肺和腰椎之间,周围全是大血管,硬取就是死路一条,只能先消炎保命。 高其煊就在地瓜窖里躺了两个月,靠战友们凑的粗粮和草药续着命,竟真的挺了过来。 战后部队给高其煊评了三级伤残,还在县供销社留了管仓库的工作,可他看着手里的《伤残军人证》,想起韩家寨牺牲的27个战友,把证件塞进了包裹最底层。 他说“战友们都没了,我哪能坐着享福”,然后卷起铺盖回了马庄,拿起锄头当起了农民。 只是没人知道,那颗没取出来的子弹,成了他往后十年的“影子”——春天播种时咳,夏天割麦时咳,冬天挑水时咳,连1960年粮食最紧缺的时候,他把公社发的救济粮分给村里老人,自己饿到头晕,咳嗽都没停过。 县医院的X光片最终揭开了咳嗽的根源,胶片上右肺区域的金属阴影周围,环绕着一圈不规则的絮状纹路。 主治医生指着胶片告诉高其煊,是肉芽组织把子弹裹了起来,像个“保护罩”隔离开器官,可每一次呼吸,子弹都会摩擦肺壁,这才让他咳了十年。 而那颗子弹能在体内待十年不引发败血症,在当时的医学上,算是个少见的奇迹。 子弹被咳出后,高其煊的咳嗽慢慢停了。他还是每天去田里种地,只是腰杆比以前直了些。后来有人问他,十年咳嗽就没觉得难受吗? 他摸着炕头那件留着弹孔的旧军装,笑着说:“比起韩家寨埋在土里的战友,我能活着种庄稼,这颗子弹就是老天爷赏的军功章。” 如今,高其煊的旧军装和军功章挂在马庄村的村委会里,村里的老人给孩子讲故事时,总会指着那些展品说:“你们看,这是高爷爷当年打仗时穿的衣服,他肺里藏着子弹咳了十年,却从来没说过自己是英雄。” 参考资料: 【第46期】高其煊忆“小八路”的烽火岁月》——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