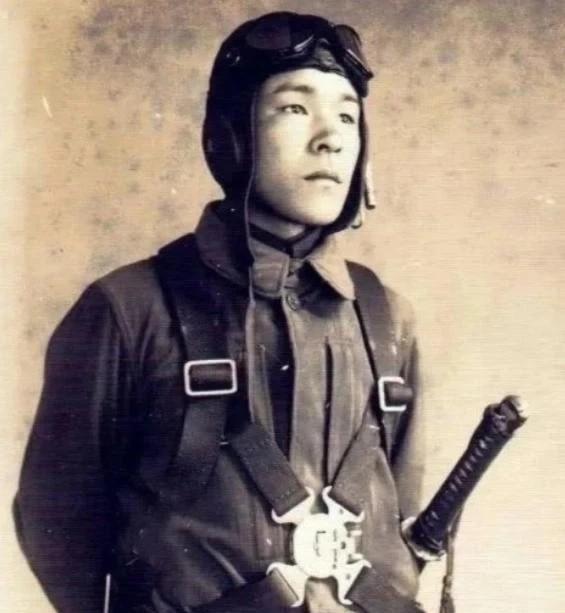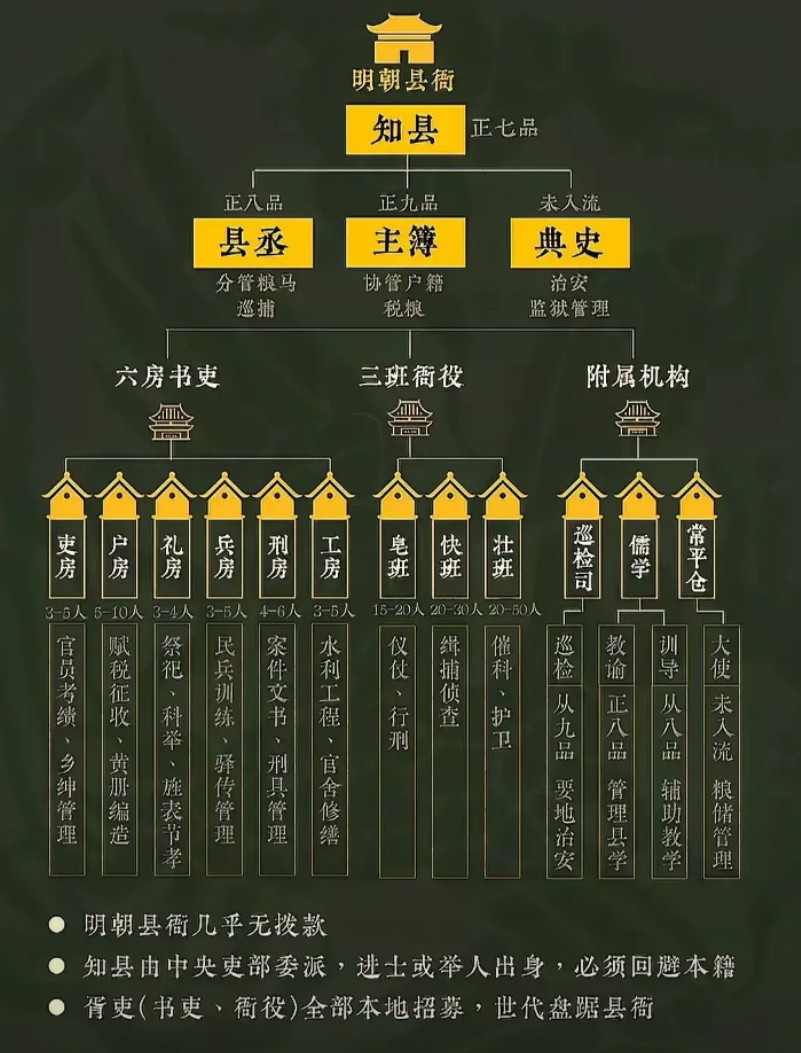49年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遭遇,特意致信中央:希望解决其工作问题 “袁先生到底怎么说的?”——1949年10月12日,北京东安市场旁,一位报界同仁侧身低声追问。章士钊放下青花茶盏,只回了两个字:“求人。”短短一语,道尽一位落魄长子的窘境,也推开了一段横跨清末、民国与新中国的曲折往事。 那封信不长,纸张微黄。袁克定在信里没有诉苦,只简单说明生活捉襟见肘,想找一份与史料、文字相关的差事。章士钊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终决定写信给中央统战部,理由很直接——“此人虽非善类,却有笔墨之长,可为文史之用。”信发出一周后,中央文史馆寄来回函,答应以馆员身份安置,每月津贴六十元。章士钊这才松了口气:“总算给他留下一条体面活路。” 许多人不理解章士钊的决定。1949年刚解放,普通北京人提到袁克定,想到的大多还是“逼父称帝的逆子”。可如果把镜头拉远,你会发现,这个名字背后折射的是旧式家族式微、个人选择与时代洪流的多重碰撞。 先把时间拨回1890年代。袁世凯在朝鲜总理衙门任上时,总把年幼的袁克定带在身边。洋枪队、条约文本、关内外政务——这些少年眼里的“家常事”,普通少年连听都没听过。为了让儿子比同龄人更“洋气”,袁世凯还请了德国外教教英语和德语,顺便灌输几句“欧洲强盛因君主立宪”的私货。袁克定记住了,也深以为然。 辛亥革命爆发,朝局剧变。袁世凯南北议和那阵,袁克定二十九岁,他替父亲与革命党人谈条件。谈判桌上,他提出“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保留蒙藏皇帝名义”等三条,革命党最终点头。那一年,他风光无两,自认离权力核心只差一步。 可留学德国带回来的“帝制”执念,很快把父子俩推向深渊。1915年袁世凯接受“洪宪帝制”,袁克定自封“太子”,还制造伪《顺天时报》蒙骗父亲。事情败露,袁世凯抽他皮鞭,“逆子,欺父误国”六字传出,引来朝野笑谈。帝制不到百日就土崩瓦解,袁氏家道随之滑坡。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袁克定痛哭在灵前,却救不回袁家的权势与名声。 分家时,他分得古玩字画若干、现银四十万,表面上仍是不小的富户。可是挥霍习气难改,缺乏可持续收入,到了1930年代,钱基本败光。更雪上加霜的是,国民政府以“逆产”名义查封袁宅,大批藏品被仆人骗走换钱。一夜之间,昔日太子变成了为柴米奔波的残腿老人。 1937年,北平沦陷。土肥原贤二两次登门,开出高官厚禄拉他出山。按常理,他只要点头,就能衣食无忧;可袁克定偏偏回绝,并在《益世报》刊登声明:“身体有疾,拒绝过问时政。”这一次,他没再选错队伍。有人说他怕再栽跟头,也有人说他还有几分民族气节,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决定让他彻底断了经济来源。 抗战胜利,他的股票又被长子挪作他用。解放前夕,全家靠表弟张伯驹接济。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人心思定,新政府急需团结知识分子。章士钊看准了时机替袁克定递话:“留这把老骨头在文史档案堆里,胜过把他赶去街头卖字画。” 中央文史馆馆员的职务算不上显赫,但六十元月薪足以温饱。袁克定每月领了钱,总要先送去张伯驹家,算是还情。张伯驹连推三次:“别来这套,人情抵得干粮。”最后索性把钱折回塞进袁克定袖口。那一幕,被街坊看见,只摇头:“太子落难终遇贵人。” 进入1950年代,北京补给紧张,他的餐桌上常年是窝头片、咸菜疙瘩,偶有豆腐算奢侈。腿脚残疾,出门不便,他索性在小院里整理旧稿,摘抄父亲留下的政治文牍,自嘲“余今乃为父史之编外伊藤”。毛主席得知此事,特批从个人稿费里拨二十元,算是变相加薪。秘书把钱送到门口,袁克定愣了半晌,只说:“承情,惭愧。” 1955年冬,袁克定病逝于张伯驹府上,身边只有二夫人马彩云。遗体入殓时,穿的仍是一袭粗布长衫,兜里找不到半张银票。后事由张伯驹操办,送去八宝山火化。消息悄无声息,京城茶余饭后再议起他,更多的是叹息,而不是指责。 若把袁克定的一生写成坐标,巅峰停在1915年,谷底落在1937年,尾声则定格在1949年那纸调令。功过如何评说,史书自会给出分寸;可就个人命运而言,能在风雨中保住一点不事敌寇的底线,又在新局面里获得基本尊严,已属不易。章士钊那封推荐信,看似微不足道,却让一个跌到尘埃里的旧人重新站直了腰,也为动荡时代画下了一个略显温和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