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账难翻:战后赔偿的曲折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宣告无条件投降,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终于尘埃落定。战后初期,盟国为此成立了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 FEC),负责处理对日管制和赔偿等事宜。依据当时各方提出的方案和初步估算,中国作为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损失最惨重的国家,被认为有权获得相当份额的赔偿。

战后赔偿的落实过程远比预期复杂,充满了变数。首当其冲的是中国国内局势的剧变。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国便陷入了大规模内战。当时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对抗中。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国的对日政策,也在迅速发生转变。
随着冷战铁幕的落下,美国开始将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视为其首要战略目标。在此背景下,曾经的敌人日本,其地缘战略价值被重新评估。美国逐渐将日本视为其在亚洲对抗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和潜在盟友,其对日政策从战后初期的惩罚、限制转向扶持、重建。

1949年5月,在美国的主导下,远东委员会事实上停止了日本赔偿的支付计划,美国单方面宣布不再推进对日索赔的拆迁工作。紧接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在朝鲜半岛直接军事对抗。这场战争强化了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成为美军重要的后勤基地和“反共桥头堡”。
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导和操纵下,包括苏联、中国(无论是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均未被邀请参加)在内的多个二战主要参战国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签订。该和约第14条虽然原则上承认日本有支付赔偿的责任,但同时又声称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经济状况不足以完全赔偿所有损失,因此对赔偿问题做了诸多限制,并允许通过双边协议来处理具体的赔偿事宜。

更重要的是,该和约的签订本身就将对日作战最久、牺牲最大的中国排除在外。随后,在1952年,在美国的压力和斡旋下,日本与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当局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Taipei),在该条约中,中华民国当局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添了麻烦”?谈判桌上的风波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破冰”——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极大地改变了冷战的战略格局,也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冲击,被称为“尼克松冲击”。长期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日本,意识到需要调整其对华政策,以适应新的国际现实,并寻求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

同时,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经济界也期待打开巨大的中国市场。1972年7月,田中角荣当选日本首相,他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其内阁的首要任务之一。经过双方紧锣密鼓的接触和准备,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等一行抵达北京,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正式拉开帷幕。
谈判的核心议题主要包括:结束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即战争状态的法律终结)、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日本承认并尊重中国关于台湾是其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以及战争赔偿问题。

中方在谈判伊始就明确了立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理应进行赔偿。日方在赔偿问题上处境微妙。一方面,他们需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以回应中方的要求和国际社会的关切;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受到《旧金山和约》以及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华日和约》中放弃赔偿条款的约束,同时也面临国内财政和法律上的考量。
在一次讨论战争责任的会谈中,日方代表、时任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发言中使用了「迷惑をかけた」(给贵国添了麻烦)的表述来形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为。种措辞,在中方听来,显然是过于轻描淡写,未能充分体现战争罪行的严重性和日方的反省诚意。据报道,中方代表对此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认为这种表述回避了“侵略”的实质,是对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的不尊重。

伟人拍板:一笔勾销换未来
当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因战争赔偿、历史认识以及台湾问题的最终表述等关键分歧而陷入僵持,紧张气氛持续数日之后,毛主席的介入成为了打破僵局的关键。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其位于中南海的书房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
据事后披露的信息和参与者的回忆,会见的气氛相对轻松。毛主席以其特有的风格主导了谈话,他以一句“架吵完了?”作为开场。这次会谈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内容广泛,涉及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亚洲乃至世界局势等宏大议题。田中角荣表达了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意愿。

毛主席则从更高的战略层面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对未来两国关系的设想。在谈及最为棘手的战争赔偿问题时,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却又影响深远的决定。他表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共产党人是着眼于未来的,我们更关心的是中日两国人民能否长期友好下去。基于这种考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毛主席在表示放弃赔款的同时,也提及了未来两国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暗示性地表达了希望日本能以某种形式(例如资料中提到的长期低息贷款)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愿望。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将眼前的、具有惩罚性质的战争赔款,置换为了一种着眼于未来、带有友好互助性质的经济合作前景。

它打破了持续数日的僵局,使得双方能够在《中日联合声明》的最终文本上达成一致。1972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声明第五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不算数”不行!大国博弈的智慧
毛主席在1972年决定放弃对日战争赔款,这一举动在当时和后世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要理解这一决策,需要将其置于毛主席处理国际事务和国家战略全局的一贯思维框架之中。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可以发现,毛主席在面临重大抉择时,常常表现出一种超越眼前得失、着眼于长远战略利益的特点。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内外面临严峻挑战。当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逼近中朝边境鸭绿江时,国内对于是否出兵朝鲜存在巨大争议。反对者认为中国国力孱弱,不宜与世界头号强国直接对抗。
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他提出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论断,认为通过一场硬仗打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轻视与封锁,为国家建设赢得一个相对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国际社会的尊重。
同样体现这种战略思维的,还有中国独立自主研制核武器的决策。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尤其是在朝鲜战争和数次台湾海峡危机中。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撤走了援助专家,使得中国的核武器研发一度陷入困境。

当时国内经济十分困难,但毛主席对此态度坚决,他认为,在帝国主义依然存在的世界上,没有原子弹、氢弹这样的战略武器,中国就无法真正保障国家安全,无法在大国博弈中挺直腰杆。他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个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打破了核垄断。
无偿援助?不,是互利共赢的长跑
放弃上千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表面上看是中国做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这一决策换来了更为宝贵的战略和经济利益。作为对中国放弃赔款的回应和中日友好的体现,日本政府自1979年起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ODA)。
这主要形式是低息日元贷款,辅以部分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截至2007年,日本累计向中国提供了约3.3万亿日元的优惠贷款及其他形式的援助。这些资金如同及时雨,注入了当时资金极度匮乏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中。

北京地铁1号线的建设、秦皇岛港煤炭码头的扩建、上海浦东机场的建设、以及遍布全国的铁路、公路、港口、能源、通讯、环保、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总计156个重点项目,都得到了日本ODA的关键支持。
更具深远意义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款的决定,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美国试图构建的对华包围圈。在中日建交后的短短半年内,许多重要的西欧国家,如联邦德国、英国(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法国等,纷纷跟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与之建立或升级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功打破了长期的外交孤立局面,为之后实行改革开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打开了重要的国际通道。当时间来到2008年,日本对华ODA项目在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宣告基本结束。同年,北京成功举办了举世瞩目的夏季奥运会,主场馆“鸟巢”的雄伟钢结构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中国在新世纪的崛起与自信。
回望历史,那些曾经通过日元贷款等形式支持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的资金与合作,无疑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画卷,化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基石之一。
参考资料:[1]杨加坤.中日赔款问题与日本近现代经济的发展[J].黑河学刊,1996(Z1):118-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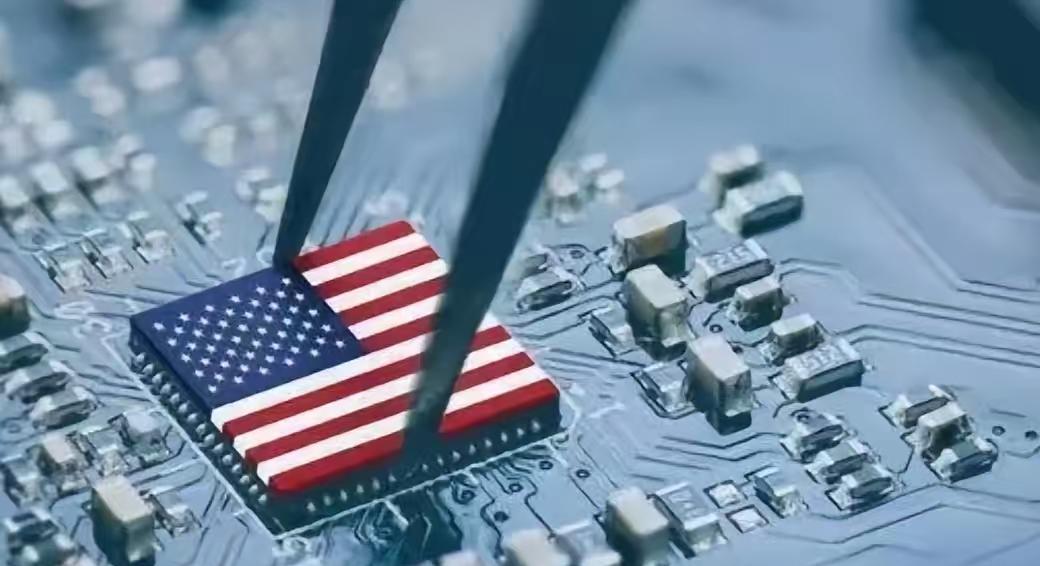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