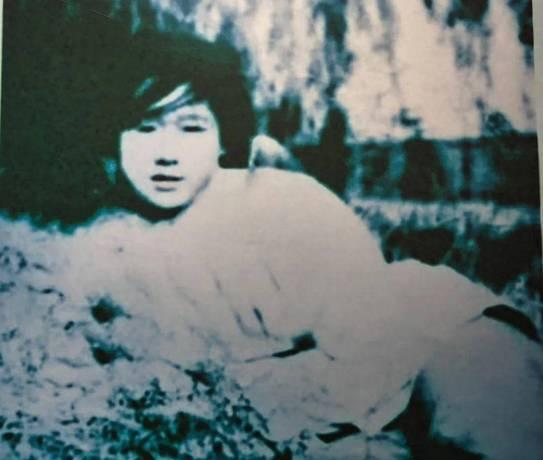1958年,志愿军撤军前,黄继光弟弟当逃兵被抓回,他含泪承认:黄继光是我哥。 主要信源:(中国军网——黄继光侄子追寻父辈足迹:讲好英雄事迹传承革命精神;长江日报——黄继光牺牲后其弟侄11人参军入伍) 1958年的朝鲜上甘岭,山风凛冽,阵地荒芜。 黄继恕独自跪在一处残破的地堡前,手中紧攥军帽,指节绷得发白。 散落四处的弹壳碎片仍依稀可见,那一刻,他仿佛回到了1952年的夜晚。 枪炮轰鸣,火光冲天,他的哥哥黄继光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他缓缓俯身,用手拂去浮土,小心翼翼地捧起一抔泥土,又从怀中取出一块母亲交给他的蓝色布帕,将土仔细包裹好,重新贴胸收好。 他想遵从妈妈的愿望接哥哥回家。 —— “逃兵”俩字,像烙铁一样烫在黄继恕背上。押送他的战友没绑他,只让他自己走,枪倒背着,像给留点脸。他低着头,脚上的解放鞋踢得土疙瘩乱飞,心里却翻着滚:哥,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晚了,连你最后一捧土都带不回去。 事情其实简单。部队接到撤军命令,他趁夜溜出营,想再跑一趟上甘岭。没人比他熟那条炮火搓出来的山路,可刚摸出山脚,巡逻队就把他“请”了回来。连长一拍桌子:“黄继恕,你哥是堵枪眼的英雄,你倒好,当逃兵?”他憋得脸红到耳根,半天吼出一句:“我哥在那儿,我得接他!”全场愣住,随后静得能听见外面风卷弹壳的哗啦声。 —— 1952年10月19号夜里,哥哥临走前给他留了个苹果,拳头大小,青得发涩。黄继光把苹果往他怀里一塞:“明天打完仗,咱哥俩分着吃。”结果仗打完了,人没回来,苹果被他一直揣到烂,只剩两粒籽。他偷偷把籽埋在了坑道背阴的土里,没想到竟冒了芽,如今长成了胳膊粗的小树,叶子被炮火削掉一半,却还活着。撤军前夜,他跑去掰了根枝条,削成筷子长,刻了“继光”俩字,打算带回家,给老娘当“儿子”。 —— 母亲邓芳芝在家书里写得很白:活要见人,死要见土。黄继恕揣着那封被汗水浸得发软的药纸信,一路从四川中江跑到朝鲜,就想捧一抔哥哥牺牲地的土回去。信纸背面还有母亲用铅笔画的两个小娃,一个写着“光”,一个写着“恕”,中间一道杠杠,像要把两兄弟永远拴在一起。他想着,把土带回去,往祖坟边一撒,老娘哭一鼻子,就算把哥哥“接”回家了。可部队有纪律,撤军要统一行动,他等不及,这才当了“逃兵”。 —— 连长听完他的哭腔,沉默半晌,只丢下一句话:“明早五点,统一登车,我准你提前一小时去,但得给我全须全尾回来。”说罢把武装带往桌上一扔,算是默许。黄继恕啪地敬了个军礼,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夜里他再没合眼,坐在坑道里,把母亲给的蓝布帕叠了又叠,拿针线把四个角重新缝牢,怕土路上漏掉一星半点。 —— 天刚泛白,他背着空挎包,一溜小跑蹿上高地。五年过去,上甘岭早没了当年的火海,只剩焦黑的土、碎成渣的岩石,还有风卷着弹壳叮叮当当。他跪在塌了半截的地堡前,手像犁头,狠命刨,指甲缝里塞满黑土,偶尔碰到弹片,划道口子,血珠子冒出来,和土搅在一起,他也顾不得。刨了半尺深,他捧出满满一捧带硝味的土,凑到鼻尖闻,一股铁锈混着火药味,像哥哥当年身上的硝烟。他把土包进蓝布帕,扎成小结,贴胸口揣着,心脏咚咚跳,仿佛那抔土里还残留着哥哥的心跳。 —— 回程路上,他脚步轻快,却撞见一群朝鲜老乡在修简易公路。领头的大爷瞅见他胸前的蓝包,鞠了一躬,用生硬的汉语说:“中国哥哥,英雄。”一句话把他钉在原地。大爷指着远处一座新立的水泥碑,上面用中朝两国文字刻着:“黄继光烈士牺牲地”。原来朝鲜百姓没忘,他们自发把高地铲平,立碑,种松树。黄继恕扑通跪下,给大爷磕了个头,额头沾了泥。那一刻他懂了,哥哥不光是老娘的儿,也是中朝两国共有的儿子,他带走的这捧土,只是哥哥留给家乡的一份“念想”,而真正的“魂”,早已长在这片高地上,谁都带不走。 —— 五点整,他喘着粗气跳上卡车。连长瞅他胸前鼓囊囊一包,没吭声,只递过来一块压缩饼干。车子发动,黄继恕回头望,上甘岭渐渐缩成一条黑线,像哥哥最后挥别的手。他摸了摸怀里的土包,轻声嘀咕:“哥,回家喽。” —— 回国后,他把土撒在祖坟旁,老娘跪在地上,用手把土拢成小堆,插上那根刻着“继光”的小木条,哭着笑:“老二,你把老大接回来了。”可黄继恕心里明白,哥哥其实永远留在了朝鲜,留在那块碑、那片松林、那些叮叮当当的弹壳里。1959年,他重新入伍,成了工程兵,专修公路,一去就是三十年。他说,路修到哪儿,哥哥就能“看”到哪儿,子弹打不断的路,才是回家真正的方向。 —— ——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