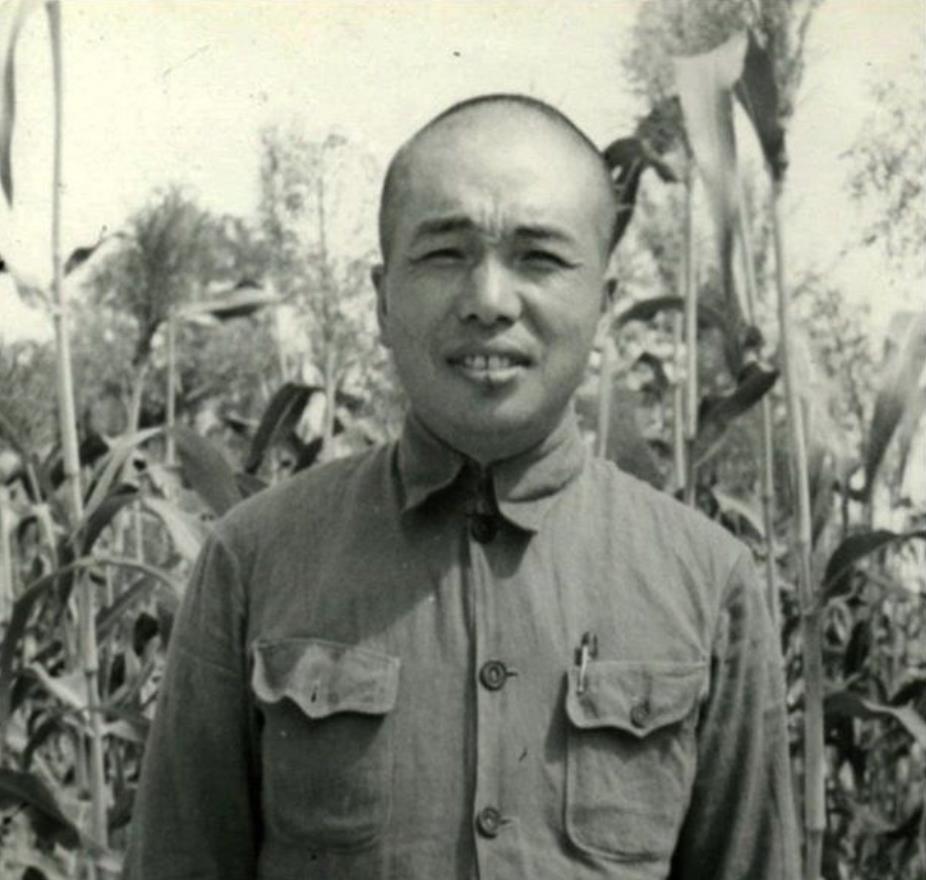他要求辞去中央委员,德高望重又被选为中顾委常委,政治待遇不变 “1985年初,这把交椅该让年轻人坐了。”——1月的一天,宋任穷对王震说完这句话,顺手合上了文件夹。屋外寒风凛冽,屋里却安静得能听见钢笔落在桌面的清脆声。两个同龄的老将心里都清楚,此举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在为制度探路。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干部新老交替成为显性课题。宋任穷已七十六岁,王震也七十五岁。以往,一名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离开一线往往要等到身体撑不住;可改革年代讲求效率,“能上能下”正在成为共识。于是,两位老同志联名致信中央,请求辞去中央委员并退出一线岗位。信写得简短,态度却非常坚决——“位子让给后来者,改革急需新血。” 这封信递出之前,宋任穷的履历在领导层里堪称浓墨重彩。解放战争,华野第三副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分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军区政委……职位滚烫,战区频繁转换,他却总能迅速进入角色。有意思的是,1955年初拟授衔时,他一度列入大将名单;人数缩编后落为上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军衔多一颗星少一颗星,干活不变。” 从军队转到地方,本是许多将领的“坎”。宋任穷却主动请缨,离开热火朝天的总参,前往第二机械工业部。那些年,装备工业基础薄弱,连图纸都要翻译几遍才能下车间。技术人员私下感叹:“没想到一个打仗出身的部长,懂得比我们还多。”他并非真懂所有参数,而是勤跑现场、勤抄笔记,把“外行领导内行”这件事干成了“外行逼着自己变半个内行”。 1960年春,东北局恢复设立,他临危受命担任第一书记。时值三年困难时期,东北是全国最大的粮、煤、钢基地,稳定大局意义重大。宋任穷一到沈阳,先下工人宿舍,再进会议室。后来有人回忆:“他住的房子冬天连暖气都时冷时热,可每天照样往工厂跑。”当年年底,他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六大局”书记群体里,李井泉、柯庆施是委员,宋任穷、李雪峰是候补;由此可见党内对他的期望。 遗憾的是,1966年风暴骤起,他被打入冷宫,整整十年。十年里,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在书页空白处记录当天思考,连标点都省略。复出时,他已满六十七岁,却马上接过中组部,肩负“拨乱反正、恢复准则”的重担。那段岁月,最难的不是选拔干部,而是平复人心。审阅材料到深夜是常态;遇到复杂历史问题,他常自言自语:“先把错误纠正,再谈进步。”身边工作人员一度担心他身体,可他只笑笑:“组织信得过,咬牙也要干完。” 1982年,十二大闭幕,他进入政治局。外界把这位新晋委员与李德生、余秋里并列,称作“战将中的政将”。然而不久,他就递交报告,建议在组工系统物色更年轻的接班人。那年他七十三岁,依旧常常穿一件旧呢子大衣,骑着那辆用了十多年的凤凰牌自行车去开会。周围人劝他:“换辆小轿车吧。”他仍是淡淡一句:“走得顺就行。” 进入1985年,改革节奏加快,中央要求地方和部门大面积推行“新老结合”。宋任穷心里清楚:自己已完成历史任务,是时候彻底退出。于是,与王震商议后,两位老同志提笔写下“请求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十个字。比起普通调职,这一步意味着主动放弃党的最高权力结构席位,可他连夜把信交给机要秘书,说:“夜长梦多,赶紧送。” 组织部门很快给出回应:中央同意两位老同志“让贤”,但基于党内威望与经验,建议他们转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顾委委员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会议参与权,常委与政治局委员同级,只是着重提供咨询。换句话说,新岗位“二线不离线”,既体面又能继续发挥作用。宋任穷没有推辞,点头道:“顾问就顾问,能出力就出力。” 这一决定在十三大得到正式确认。他被选为中顾委副主任,与薄一波协助陈云负责顾委日常工作。会上,几位年轻代表私下感叹:“老宋还在,我们心里有底。”副主任任期五年,1987至1992年期间,中国改革攻坚层出不穷,顾委多次提出“稳中求进”“尊重实际”等建议,许多报告都留下了宋任穷的批注。有人翻阅会议记录时发现,他最常写的两个词是“可行”和“再议”,寥寥数笔,却给政策执行预留了回旋空间。 1992年,十四大决定取消中顾委,标志着这一过渡机构完成使命。宋任穷由此彻底离开权力舞台。此后,他只在极个别重要会议露面,大多数时间埋头回忆录编纂。朋友问他:“还能静得下心?”他合上稿纸淡淡一笑:“心里没事,自然静。”他逝世时,官方讣告列举了他一生职务,却没有一句豪言壮语;对于熟悉他的人来说,这正契合他的低调风格。 不得不说,宋任穷的“退”与“被留”呈现了一个特殊年代的制度探索:让权力有序交接,又保留经验财富。试想一下,如果当年没有老同志主动让位,年轻一代何时才能挑起重担?反过来,没有老同志继续在二线指导,改革能否少走弯路?其中微妙平衡,远比表面风平浪静。 如今,干部新陈代谢已成常态,可那封写于1985年的联名信,依旧值得反复端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