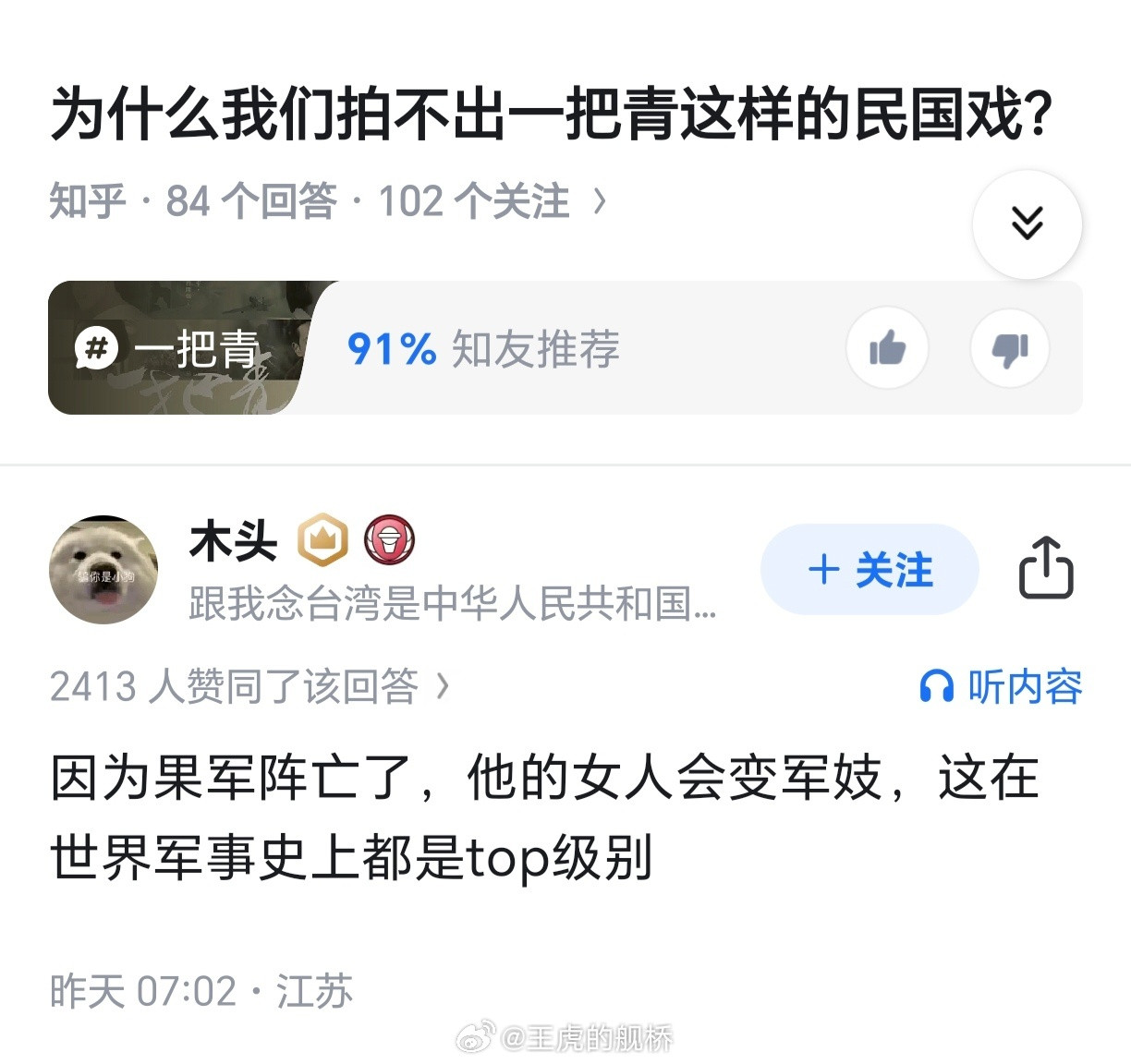195年,名震北方的公孙瓒决定金盆洗手,不再征战天下。谋士关靖大惊:“将军勇猛盖世,天下谁不害怕,为何要止步不前?”公孙瓒闻言感叹道:“以前是我年少天真,以为天下挥手可定,如今才知道,事不由己!我要修建一处固若金汤的堡垒,从此坐观天下,颐养天年!” 关靖还想再劝,公孙瓒已经转身叫来了亲兵,让他们去勘察易水边上的地形。没几天,亲兵回话,说易水南岸有片高地,既靠山又临水,是建堡垒的好地方。公孙瓒听了当即拍板,调了三千士兵和两千民夫,带着砖石木料就往高地去。 一开始,大伙都以为将军是想建座新城池,好再图大业,干活都有劲儿。可等图纸画出来,大伙才傻了眼——这哪是城池,分明是座“铁疙瘩”。城墙砌得有两丈厚,每隔三步就有一个箭楼,城里面挖了十几口深井,粮库堆得能让全城人吃五年,连士兵的营房都修得跟堡垒似的,只留着窄窄的窗户。民夫里有个老石匠忍不住问:“将军,这墙砌这么厚,是怕谁来打啊?”公孙瓒摸了摸城墙,没说话,只是让士兵把老石匠的话传开,说谁要是偷懒,就把谁扔到易水里去。 日子一天天过,堡垒渐渐有了模样,公孙瓒给它起名叫“易京楼”。可跟着他的老部下却越来越慌,尤其是校尉张蒙,跟着公孙瓒打了八年仗,从辽东打到冀州,从来没见将军这么“龟缩”过。有天晚上,张蒙揣着一壶酒,偷偷摸到公孙瓒的住处。刚进门就看见将军对着一张地图发愣,地图上画满了红圈,都是以前打仗的地方。 “将军,”张蒙把酒放在桌上,“兄弟们都憋得慌,以前咱们见了敌军,都是抢着往前冲,现在天天守着这楼,跟关在笼子里似的。”公孙瓒拿起酒壶,给自己倒了一杯,又给张蒙倒了一杯:“你还记得三年前打袁绍那回吗?咱们三万弟兄,最后活着回来的还不到五千,你胳膊上的伤,不就是那时候留的?”张蒙摸了摸胳膊上的疤,低头没说话。“我不是怕了,”公孙瓒喝了口酒,声音沉了下来,“我是怕了再看到弟兄们死在我面前,怕了城里的百姓再遭兵灾。这易京楼,我就是想让大伙有个安稳地方。” 可安稳日子没过上几天,袁绍的使者就来了。使者站在易京楼外,扯着嗓子喊,说袁绍要公孙瓒归顺,不然就带十万大军来踏平易京楼。公孙瓒站在城楼上,看着使者嚣张的样子,手不自觉地按在了腰间的佩剑上。旁边的关靖赶紧劝:“将军,咱们现在粮草足,城墙厚,耗也能耗死他们,别冲动。”公孙瓒咬了咬牙,最终还是让士兵把使者赶走了。 可没过半个月,就传来消息,说袁绍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易水北岸,还杀了几个外出打柴的士兵。张蒙带着伤兵来见公孙瓒,伤兵的胳膊被砍了一刀,血还在渗:“将军,袁绍的人太狠了,见人就杀,连老百姓都不放过!” 公孙瓒看着伤兵,又想起以前战死的弟兄,突然一拍桌子站了起来。他快步走到城楼上,对着下面的士兵喊:“兄弟们,我以前以为躲在楼里就能安稳,可现在才明白,乱世里哪有躲出来的安稳!袁绍要打过来,咱们就跟他打!不是为了争天下,是为了护着楼里的百姓,护着身边的弟兄!” 士兵们听了,都举起兵器喊“杀”,声音震得易水都跟着响。公孙瓒亲自披挂上阵,带着士兵渡过易水,跟袁绍的部队打了起来。他的长枪还是像以前一样快,杀得敌军节节败退。张蒙跟在他身边,笑着喊:“将军,这才是咱们认识的公孙将军!” 后来,易京楼虽然还是没躲过战火,但公孙瓒再也没提过“坐观天下”。他带着士兵守着易水两岸,护着周边的百姓,哪怕兵力不如袁绍,也没退过一步。有人问他,当初为啥要建易京楼,又为啥后来还要出去打。公孙瓒笑着说:“建楼是想求安稳,可打起来才知道,真正的安稳,是得用手里的枪护着的。” 这故事后来在河北一带流传很广,老人们说起公孙瓒,总说他不是退了,是懂了——争天下不如护一方,再坚固的堡垒,也不如人心齐。(本故事根据《后汉书·公孙瓒传》及民间传说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