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2岁章太炎穷得连2块钱的烟都买不起。杜月笙掏出1000大洋,想请他写篇文章。章太炎:不写!几月后,章夫人瞒着丈夫,笑眯眯地收下了1000大洋。 1931年的上海,法租界的茶楼里,烟雾缭绕,章太炎一口茶呛在喉头,听到有人议论杜月笙送来的“银票”。他皱紧眉头,旱烟杆在桌上磕得咚咚响,周围的文人窃窃私语,眼神里带着几分揶揄。 章太炎,62岁的国学大师,一身傲骨,骂过光绪、袁世凯,连蒋介石也没放过,如今却被传与青帮大佬杜月笙扯上关系。 他攥紧拳头,起身拂袖而去,留下茶碗里未喝完的龙井在桌上晃荡。回到家,他推开书房门,埋头翻阅《汉书》,却不知这“银票”背后,藏着一个他从未察觉的秘密。 上海的法租界,霓虹灯下藏着无数暗流。 杜月笙,43岁,青帮的头面人物,长衫一丝不苟,腕上的刺青被袖子遮得严实。他坐在公馆里,手指摩挲着翡翠扳指,面前摊着一封信——章太炎的亲笔,字迹遒劲,求他帮侄子摆平一桩房产纠纷。 杜月笙眯起眼,嘴角微扬,这是个机会。他早听说章太炎的学问,崇拜得紧,却苦无门路结识。如今,国学大师主动求助,怎能不抓住?当晚,他派人带上律师,风风火火赶到巡捕房,几个电话打出去,章家侄子连夜回了家,房产的事也一并了结。 三天后,杜月笙提着两盒上等云土,亲自登门苏州章宅。章太炎在书房接见他,屋里堆满书卷,空气中弥漫着墨香和淡淡的药味。老先生握着杜月笙的手,眼神复杂,半晌才吐出一句:“多谢杜先生仗义。” 杜月笙摆摆手,笑得谦逊:“章先生言重了,小事一桩。”他瞥见屋檐下晾晒的旧长衫,心中一动,临走时不动声色留下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两千银元的庄票,压在茶几的杯子底下。 这事本该到此为止,可杜月笙不甘心。他想让章太炎为杜氏宗祠写篇碑文,既能帮衬这位落魄大师,又能给自己添几分文人光彩。1931年春,他再次登门,手里多了一张一千大洋的银票。章太炎听明来意,脸色一沉,旱烟杆磕得更响:“我章某人不是卖字的!”他转身进了书房,门砰地关上。 杜月笙站在院子里,望着厨房里升起的青烟,笑了笑,没再坚持。 厨房里,汤国梨正低头熬粥,米缸里只剩薄薄一层。她是书香门第出身,却跟着丈夫颠沛流离,陪嫁的玉镯早已当掉换药。 杜月笙的随从悄悄找上门,提到那张一千大洋的银票,说是“杜先生的心意”。汤国梨攥着围裙,犹豫再三,还是接过纸袋,藏进了米缸深处。 她知道丈夫的脾气,若被发现,这钱非但留不住,还得闹翻天。可家里揭不开锅,药费、米钱压得她喘不过气,这笔钱是救命稻草。 两个月后,章太炎的学生陈存仁带来一卷宣纸,上面是老先生亲笔写的碑文:“孝友传家,诗书继世。”杜月笙捧着卷轴,笑得眼角皱纹绽开。 他知道,这文章不是章太炎心甘情愿写的,而是汤国梨的默许换来的。他没点破,只派人每月送去米面和药材,章家的小院从此不再冷清。 这事在上海文人圈传开,有人暗讽章太炎晚节不保,收了青帮的钱。 章太炎在茶楼听到风言风语,拍案而起:“杜先生帮我章家大忙,我这是还人情!”他嘴上硬气,可心里不是滋味,关在书房三天三夜,把新得的润笔费全换了古籍,像是用书卷洗刷自己的清白。 时间转到1934年,章太炎决定迁居苏州,专心讲学。搬家那天,苏州街头黄包车排成长龙,足有二十辆,车夫齐声说是“杜先生安排”。章太炎抱着装满手稿的樟木箱,汤国梨攥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当票和药方。夕阳洒在青石板路上,车轮吱吱呀呀,影子被拉得老长。章太炎抬头望天,喃喃自语:“杜镛,倒是个人物。” 他却不知,那一千大洋早已在米缸里化作柴米油盐,撑起了他最后的岁月。 杜月笙的仗义不止于此。1931年江淮水灾,他奔走募捐,筹得53万元,占国民政府赈灾款的五分之一。他还带头响应新生活运动,戒掉多年的鸦片瘾,试图洗去“流氓”标签。 章太炎则在苏州继续讲学,修订《章氏丛书》,直到1936年病逝。他留下的学问如星光璀璨,却掩不住晚年的落寞。 章太炎走了,杜月笙派人送去最后一笔慰问金。苏州的小院空了,书桌上还留着未写完的批注。黄包车的声音早已散去,只剩米缸里那张银票的故事,在上海滩的巷弄间低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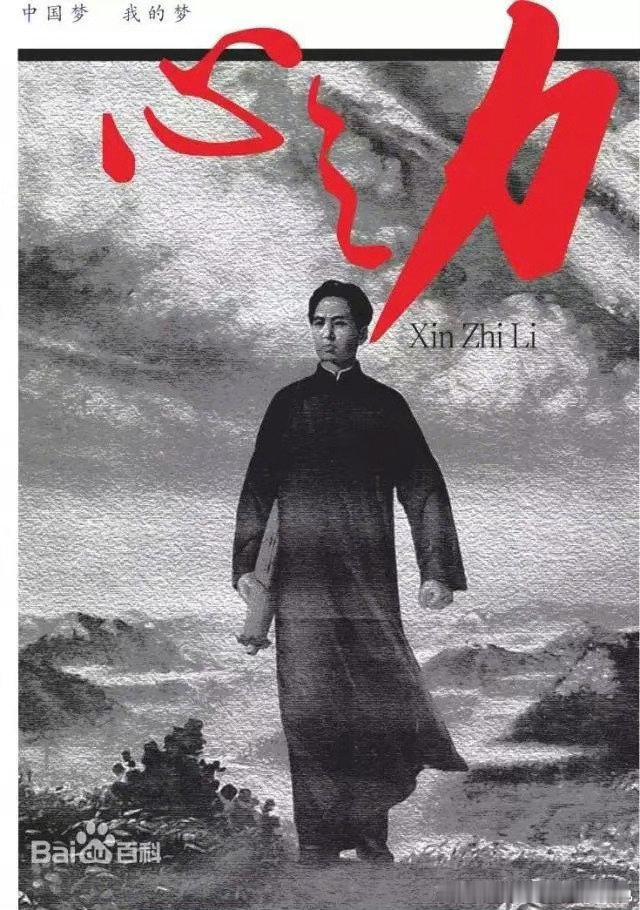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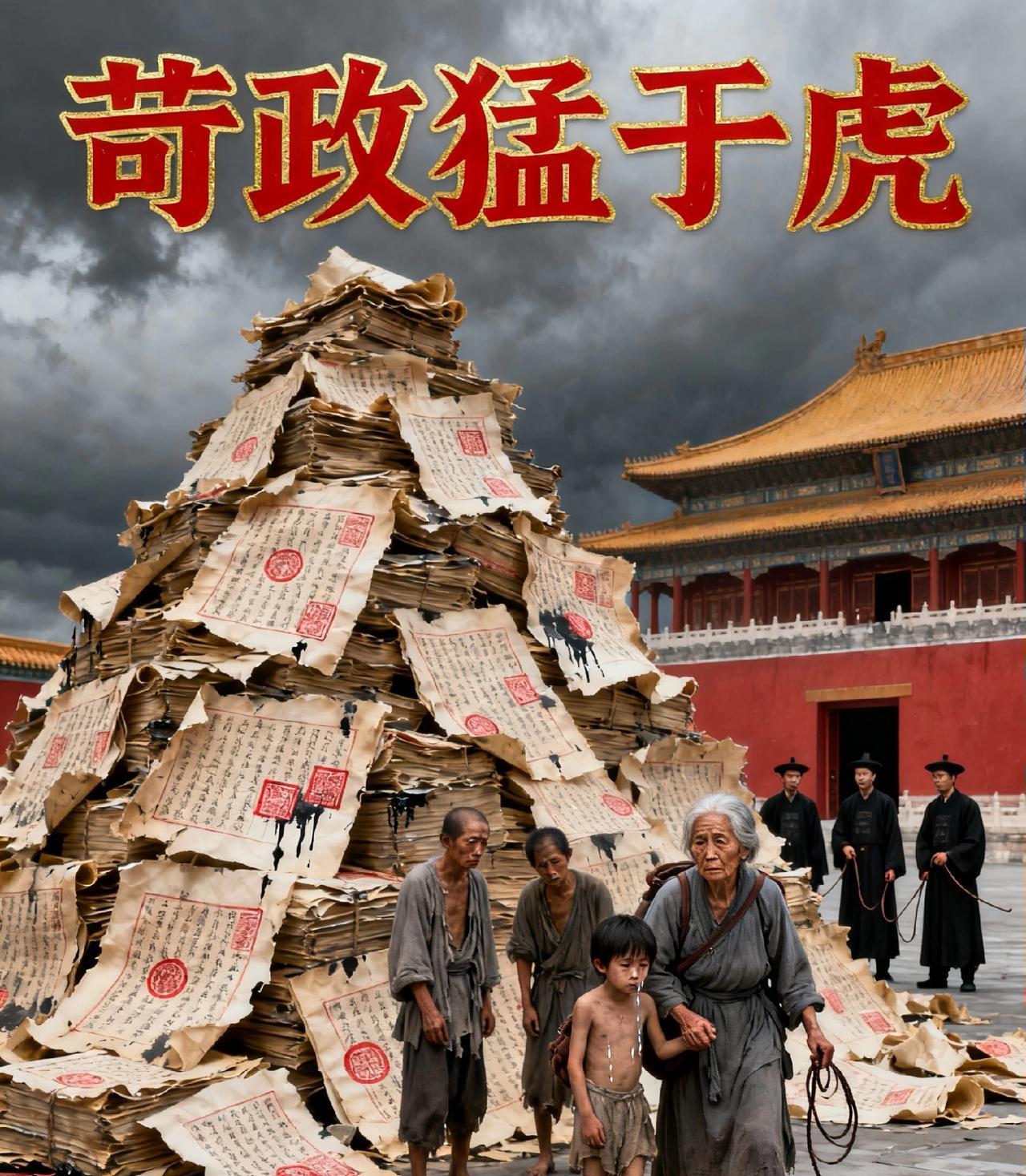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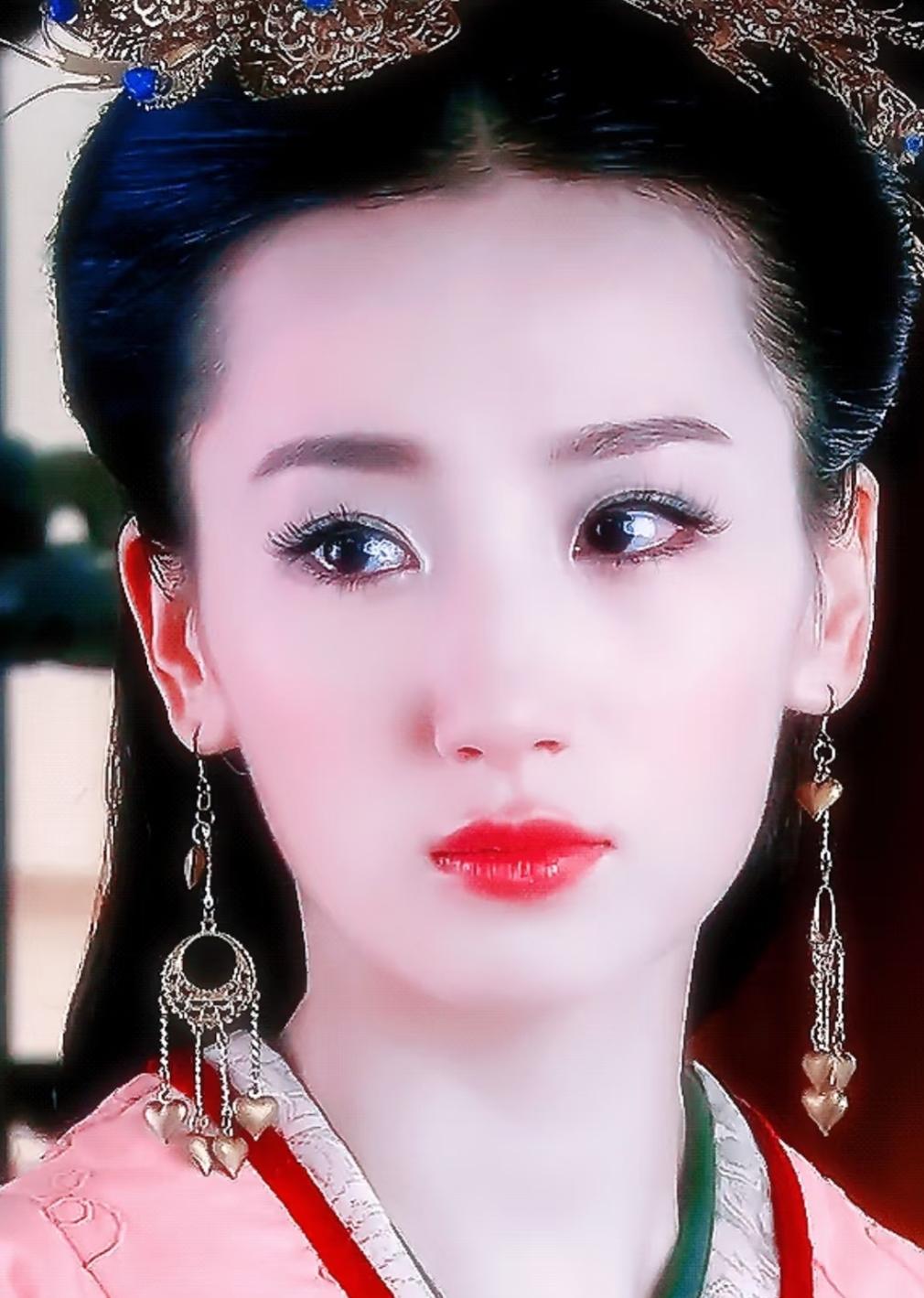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