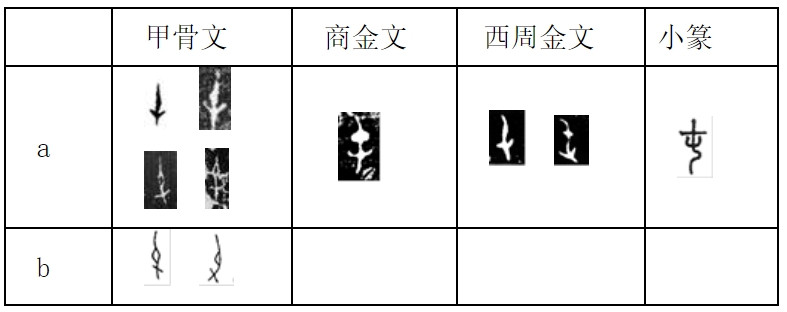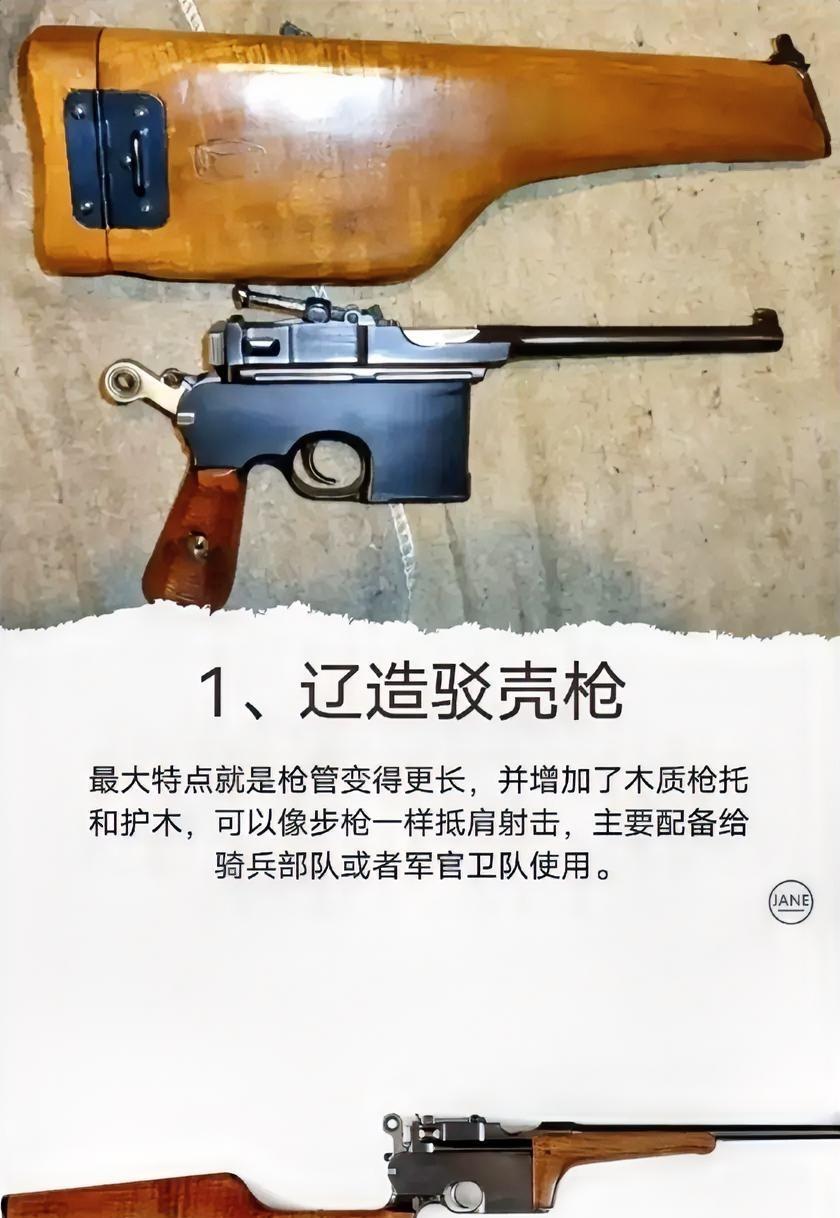转自:团结报
□黄鸣鹤
1943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激战正酣:东线战场上,苏联红军在多地段强渡第聂伯河,试图突破德军“东方壁垒”防线,因德军反扑受阻。欧洲南线,意大利脱离法西斯阵营,英美军队困在那不勒斯山脉中与德国苦战。太平洋战场上,美国采取蛙跳战术,和日本逐岛争夺。中印缅战场,中国驻印军完成训练和装备整备,开始向缅北边境集结,准备再度打通滇缅公路,畅通中国抗战物资运输生命线。
伦敦会议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
10月20日,一次特殊的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17个同盟国派代表参加,决定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使命是在交战区系统地搜集、调查、提取、保存战争期间所发生的战争罪行证据,为战争结束后的战争国际法庭审判作准备。
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是有国际法依据的,例如《海牙公约》规定,不得杀害或伤害已投降的战斗人员,然无论是在欧洲战场还是亚洲战场,大规模杀害或伤害战俘行为时有发生:在中国,日本军队随意杀害投降的士兵,将其作为士兵练习刺杀的活标靶,或作为“731”生化部队冻伤、细菌感染、毒气测试等实验活体的“原木”(日军文件中对活体实验对象的代称)。再比如禁止虐待战俘,战争中虐待战俘行为普遍存在,日本军队的虐俘行为尤其严重,1942年日本占领菲律宾后的巴丹死亡行军,约7.8万名美菲联军战俘被迫在高温缺水的环境下徒步120余公里,途中饥饿、毒打和随意杀害,超过1.5万战俘短时间内死亡。
此外,日本人所设立的战俘营普遍存在食物短缺、卫生条件极差的问题,导致霍乱、痢疾等疾病蔓延;强迫约6万名盟军战俘和30万东南亚劳工修筑铁路,修建著名的“桂河大桥”,大量战俘因过度劳动、饥饿非正常死亡。纳入调查范围的战争罪行还包括“杀害、虐待平民或将其驱逐为奴隶劳工”“抢劫和无故破坏城镇与村庄”“使用毒气或不必要的残忍武器”等违反国际战争法和人道主义的行为。
会议决定,“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由同盟国自行组建,有计划地开展轴心国军队、组织或个人所实施的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主义的罪行,收集整理相关物证,记录证人证言,列出应该为这些罪名承担责任的个人或组织名称等。
1943年11月1日发布的“莫斯科宣言”更是确定了“审判归属地原则”,犯下战争罪行的被告人,将被送往其罪行发生的国家,由当地人民依法审判和惩处,罪行没有特定地理位置的被告人,将由同盟国政府作出联合决定进行惩罚,这一条款为“德国纽伦堡审判”埋下伏笔。“莫斯科宣言”警告所有尚未参与暴行的人员,宣言发布后仍实施相关罪行、拒不停止者,可能被视为态度恶劣、顽冥不化。
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战争罪行调查
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伦敦会议的,是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顾维钧代表中国作了发言,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成立该委员会的全力支持,还特别强调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严重性、持续性和广泛性,应当将远东地区的罪行调查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他呼吁为委员会设立一个负责远东事务的分支机构(即后来的“远东及太平洋分委员会”)。
事实上,在伦敦会议开始前的1943年6月,国民政府就开始筹备成立“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这一组织1944年2月在抗战陪都重庆正式成立,直属行政院。委员会成立后,首先确定调查的时间范围是自九一八事变至中日战争完全结束后,日本侵华对国家、人民公私财物、生命尊严的伤害(包括人口伤亡、财产破坏、文物劫掠等),特别是违反国际法及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
调查委员会分门别类拟定不同的调查表:《敌人罪行调查表》,用于记录日军的屠杀、伤害、强奸、虐待等个人暴行;《敌人滥炸罪行调查表》,专项调查日军对非军事区的无差别轰炸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公私财产损失调查表》,用于统计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平民家庭等的财产损失;《文物损失调查表》,专项统计被劫掠、被破坏的珍贵书籍、字画、古董、碑拓等文化财产。
调查委员会总部设在重庆,在全国各省市设立分处或办事处。抗战胜利后,调查工作与接收工作同步开展,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大城市迅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委员会,特别在南京,成立“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日本军队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收集铁证、血证。委员会组成人员中,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法学教授。他们精通法律程序和证据规则,知道如何搜集、甄别和固定证据,如何向当事人询问并记录,如何勘查现场(例如发掘集体屠杀或尸体掩埋地),委员会还聘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医学专家(法医)以及在社会上享有声望的公正人士担任顾问,以提高调查的科学性和公信力,同时对调查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技能包括走街串巷,寻找受害者和目击者,进行访谈、登记,并整理笔录。调查人员除政府工作人员外,也吸收社会团体、学生、志愿者参加。
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所记录的日寇罪名及国人遭遇,令人悲愤,例如调查员在访问一位名叫李秀英的老人时,她已怀有身孕却被日军连刺数十刀,幸而未死,在讲述经历时数度昏厥,调查员在笔记中写下誓言:“若不能为死者伸冤,生者何安?国魂何安?”
实地勘查和挖掘集体埋尸的“万人坑”南京中华门外的普德寺,慈善团体“崇善堂”曾在此掩埋了数万具尸体。战后,调查委员会组织人员来此取证,在法医的指导下进行挖掘。当成百上千具残缺不全、堆叠交错的骸骨重见天日时,现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地狱般的景象所震撼。
这些证据后来在东京审判及其他的日本战犯战争罪行审判中,起到“铁证如山,不容狡辩”功能,用证据在法庭上说话,为这些历史性审判奠定基础。
调查工作还延伸到国境之外。根据“受害人国籍原则”,中国政府有权对国籍属中国的华侨在海外受战争迫害情况进行调查。为了调查日寇在占领东南亚期间对华人华侨犯下的罪行,调查委员会借助我国驻外使领馆、海外分支机构以及华侨社团,将调查活动延伸到了东南亚等华侨聚居区。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后,借口南洋华侨捐款、组织华侨回国参战(如南洋机工),对华侨开展了有计划的清除屠杀,强行向华侨社团勒索巨额“奉纳金”,系统性地没收、查封和掠夺华侨的工厂、商铺、银行存款、房产等私人财产;强征华侨民工,修建泰缅铁路(二战历史中有“死亡铁路”之称),使他们因恶劣劳动条件高比例死亡;在东南亚设立“慰安所”,强征包括华侨妇女在内的当地女性为“慰安妇”。许多调查的证据,用于在马尼拉、新加坡进行的战犯审判的法庭证据。
调查所得证据的使用
调查委员会将搜集到的海量资料进行整理、分类、翻译和审查,形成系统的罪证档案,分为“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和“违反人道原则”两大门类。同时以调查所得证据编列战犯名单,根据证据所显示罪行的严重程度,决定起诉人员名单,用于在中国进行的战犯审判的法庭证据,例如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以及进行“百人斩”的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都是在该委员会调查的基础上被列为战犯并最终受到审判的。
作为引渡证据使用。根据“受害人国籍原则”,犯罪行为发生在第三地,若受害者是中国国民,中国便拥有司法管辖权。根据这个原则,多名日本战犯被引渡回中国接受审判,其中最著名的是驻安达曼群岛的三名日本海军,被指控为消除罪证,临近战争结束时,将岛上750名华侨劳工骗到船上,将船驶到深海后引爆安装在船上的炸弹,并用机枪扫射逃生劳工,三名被告人被判处死刑。也有一些凶手逃脱了审判,如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日本投降后在印尼失踪,普遍说法是其在印尼沦陷期间掌握了大量日本罪行证据,日本宪兵队担心其战后以笔为武器揭露罪恶,将之秘密杀害,由于缺乏直接证据和明确的犯罪嫌疑人,这桩罪行终无人被起诉。
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掠夺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化、文物。调查委员会非常重视该领域专项调查,组织专家清点被劫掠和损毁的文化遗产,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故宫文物的南迁与损失、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藏品损失等。可惜许多文物已经损毁在战争期间,或下落不明,例如被日本人劫掠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中国的许多古城墙、古建筑,毁于日军炮火之下。文化掠夺和破坏是国际法确认的战争罪行,但在战后审判中,没有日本战犯被专门以“文化掠夺”“破坏文物”为罪名起诉,更无人因此项罪名单独被定罪。调查的意义不仅为了追诉,也为事后追讨提供依据。例如中国文物被侵略者抢夺并隐匿,数十年后突然出现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上,当年的调查证据,就可能为中国政府的追讨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