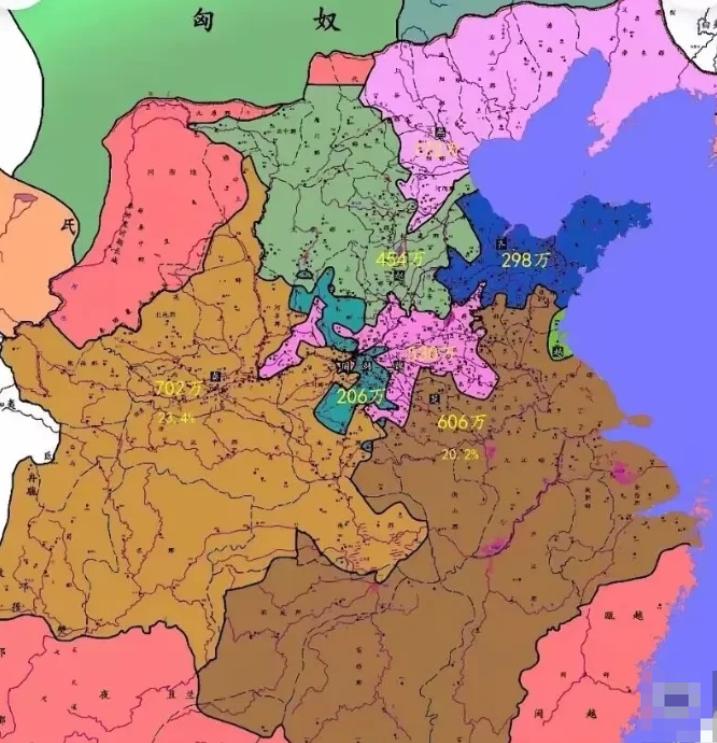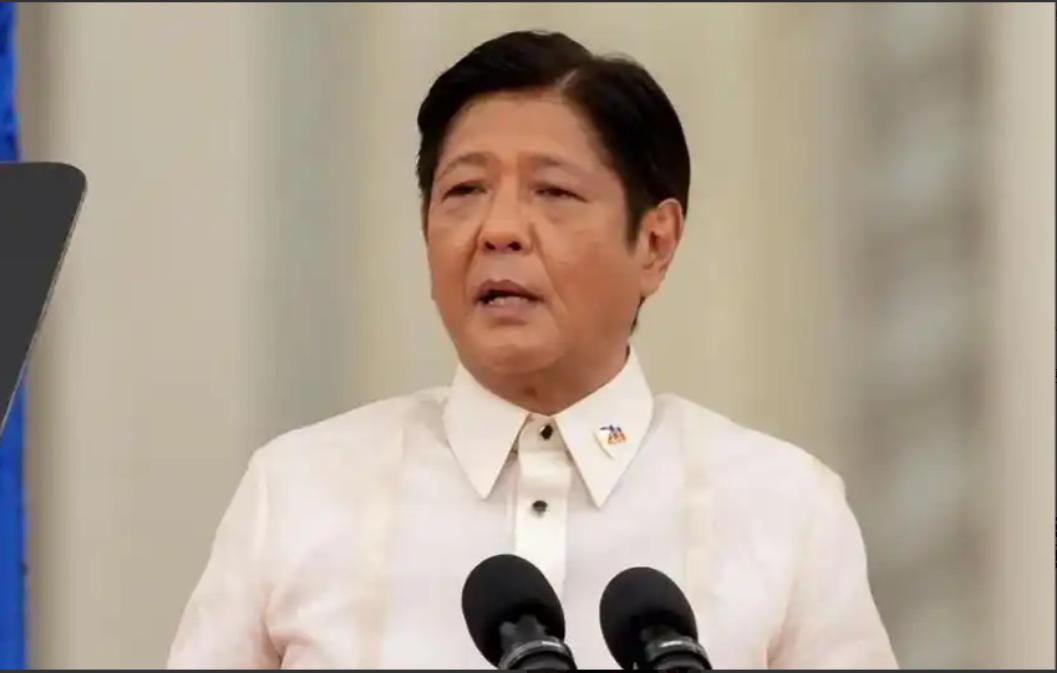解放战争中,有几场战役(包括局部战斗)解放军打得异常艰难,赢得也最为困难。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以约27万兵力攻击总兵力达45万的国民党军,最终将张灵甫的整编74师围歼在山东蒙阴县孟良崮山区。此战,华野伤亡约1.2万,歼敌3.2万,因为打得太惨烈,战后当地老百姓三年不敢上山。 在辽沈战役中,1948年10月攻打锦州时,东北野战军3纵7师20团1营奉命攻打城北制高点配水池。敌人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战斗结束后,800人的加强营,仅剩下25人,还能站起来的只有6人,营长赵兴元9次负伤,在解放战争中,这一场局部战斗可谓是最艰难惨烈一仗。 —— 配水池那一仗,说白了,就是拿人命往水泥墙上撞。老兵回忆,敌人把钢筋插进岩石,再浇混凝土,厚得能抗住舰炮。上面几层火力点,交叉得像剪刀,子弹打过来“嗖嗖”带哨音。进攻前一天,赵兴元把营里会写字的兵集合起来,一人发张纸:“想留啥话写啥,别省墨水。”纸收上来,内容却简单得吓人——“娘,儿不孝”“媳妇,再找个好人家”“孩子,别忘了交公粮”。没有豪言壮语,句句像刀,扎得赵兴元一晚上抽完三包烟。 凌晨四点,炮击开始。我们的山炮口径小,砸在配水池外壁只崩几个白点。炮声一停,1营就往上冲。头道铁丝网,用钳子剪不完,工兵干脆滚上去,让战友踩着背过;二道壕沟,敌人倒汽油点火,火海里听见有人喊“斑鸠斑鸠,飞!”——那是让后面人踩着肩膀跳。最惨的是斜坡,三十度角,滑得站不住脚,上面机枪“哒哒哒”像缝纫机,一梭子过去,坡面红了,血把土和成泥浆,踩下去“咕唧”一声,拔鞋都费劲。 赵兴元第九次挂彩,是离碉堡只剩十米。一颗手雷滚到脚边,他捡起来反掷,胳膊刚扬起,子弹从侧面穿进肩胛,骨头“咔嚓”一声。他后来回忆:“当时听见自己骨头折,比听见炮响还清楚。”手雷扔出去了,碉堡口喷火,他也被爆炸气浪掀翻,脑袋磕在石头上,昏过去。醒来时,副营长正拖他往后爬,赵兴元嗓子冒烟,第一句话是:“别管我,把旗子插上去!”那面红旗,是炊事班用被面染的,边儿已经焦黑,最后由通信员小刘插到配水池顶,小刘刚插稳,背后中弹,手还死死攥旗杆,人站着没倒,像根钉子。 战斗结束,800号人只剩25张活嘴,能自己走路的6个。担架队抬下赵兴元,他非要数人数,数到第23个,眼泪混着血往下淌:“别数了,再数心碎了。”抬担架的老乡是锦州郊区的,后来回忆:“那营长身上窟窿多得像筛子,可他还给每个死人合上眼,嘴里念叨‘兄弟慢走,天堂没机枪’。” 配水池拿下来了,锦州北门洞开,整个辽沈战役的天平“咔嗒”一声往我们这边歪。可1营几乎打光,后续部队经过配水池,全都摘帽低头,有人小声说:“这不是阵地,是砧板。”赵兴元在医院躺了半年,出院时左胳膊短了两厘米,阴天下雨就疼,他笑称“天气预报器”。每逢清明,他不进烈士陵园,而是去配水池旧址,坐在地上点三支烟,烟烧完才走,从不说话。 我采访过一个锦州老兵,他当时是2营的,战斗结束上去接防。他说:“我们爬过1营冲锋路线,脚底踩的全是弹壳,‘哗啦哗啦’像踩在干玉米秆上。有个新兵弯腰捡弹壳,被排长一巴掌:‘别捡,那是人家的命。’”老兵讲到这里,眼圈红,摆摆手不说了,只给我一张照片:配水池顶,旗子只剩半截,旗杆下横七竖八躺着穿解放鞋的脚,有只脚还勾着破袜子,白底蓝条,像家里妈妈缝的。 有人问我,这么惨的仗,值吗?我想起赵兴元晚年写的一句话:“胜利不是数字,是800条命换的城门钥匙,钥匙交到后面人手里,别弄丢就行。”今天我们去锦州,配水池早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碉堡外墙弹孔用水泥补了,可还留一个洞,拳头大,导游说:“让后人伸手摸摸,摸得到烫,才算摸到历史。”我摸了,确实烫,像那年冲锋的枪口,也像现在胸口的心跳。 战争不是电影,没有主角光环,只有血肉磨盘。磨盘转完,出来的不是英雄,是幸存的人。他们带着缺胳膊少腿的身子,回到田里、厂里、教室里,把弹片当故事讲,讲累了,就摸摸伤口,那是岁月给他们留的勋章,也是提醒我们:别光记得胜利,要记得胜利是怎么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