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眉山,一男子回乡创业17年,开了个工厂,但欠银行债务1400万元,然而银行却突然将这笔债务以126万元打包转卖给4个自然债权人手中。谁知这笔债务越滚越大,5年多时间已达到了5125万元。现在这4个债权人将要求将男子的厂房拍卖掉还钱,但男子不同意,甚至质疑债务的虚高,以及债权的真实性,可债权人们却坚称获得债权的程序是合法的。 据9月16日时代周报的报道,2006年白某决定离开在外打拼多年的浙江温州,带着积蓄和梦想回到老家眉山。那几年地方政府正大力招商引资,他心想既能发展产业,又能带动家乡经济,何乐而不为?他投入了全部身家,规划在青龙园区建起一座金属制品工厂。2008年工厂拔地而起,占地30亩,一度成为当地的重点项目。工人招了200多人,其中一半是周边村里的乡亲,对于当地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就业“顶梁柱”。 可因为厂区靠近岷江,排污许可证迟迟下不来,整整拖了五年,直到2013年才批下来。后来面对资金链吃紧,他只能四处找钱。先是从天府银行贷了900万,以厂房作抵押。但2012年银行突然要求提前收回贷款,他只好勉强还上100万本金和177万利息,剩下的缺口根本填不平,最后在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的介入下,他借新还旧,才凑够了资金,1400万的新贷款成了他继续维持工厂运转的唯一办法。 按理说贷款是风险和收益的博弈,银行收息,企业发展,大家互相扶持。可到了2015年金属行业行情急转直下,原材料上涨,订单下滑,工厂营收骤降三成,几万块的月供,对白某来说越来越吃力。 经过十几次谈判,他和大连银行达成缓还协议,2018年开始每月只还1万,2019年起每季度还5万。后来他甚至主动提高到每季度6万,表现出了最大的诚意。就在他觉得能熬过难关的时候,2019年大连银行不良贷款率飙升至3.93%,为了压低指标,他们启动了所谓的“不良清收百日会战”。 白某的债务和另外30多家企业的债务被打包在一起,总额近6亿,却以不到一成的价格整体甩给了厦门一家资管公司。他的贷款部分,估值仅126万,还不到本金的十分之一。 这一笔“甩卖”,白某完全不知情,就这样他和银行之间的债务关系,突然被切断了。更蹊跷的是债权随后又流转到了一家名叫上海庚埠商务的合伙企业。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却接下了上亿的不良资产。业内人士质疑:这样的资质,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更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短短几个月后,这家公司又把白某的债权拆出来,单独卖给了4个自然人。成交价1300万元,比银行给出的估值翻了10倍。至此白某的债务彻底脱离了正规金融体系,落入了“私人追债”的轨道。 在外界眼里,白某似乎成了一个“赖债不还”的典型。可他从2013年至2015年,陆续偿还利息319.9万元;2020年起,他更是按照法院要求,把每笔钱直接汇入彭山区法院的执行账户,累计偿还本金145万元,从未拖欠。 但如今4个自然人拿着债权合同找上门,要求他偿还的总额却高达5125万元。换句话说,光利息就飙升到了3748万元,足足是本金的两倍多。这其中的计算方式,至今没有明确解释。白某提出质疑:“利率不是当初和银行签的吗?基准利率6%,上浮35%,也就是8.1%,即便算上罚息,也不能超过24%。怎么可能涨出一个天价?” 律师们给出的意见也很直接:若利息计算超过法律规定上限,属于无效部分。更何况,自然人受让债权,本身需要提供合法的转让凭证。可是当白某向对方索要付款凭证时,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要么拿不出来,要么说“合同里有”。 法院已经受理强制执行申请,但由于争议过大、凭证不全,拍卖程序迟迟没有启动。白某和他的律师团队也在极力要求,重新审计债务,厘清本金和利息的真实情况。这场纠纷一经报道,迅速点燃了舆论。 网友议论最多的有两点:一是“债务利息怎么可能涨得比本金还快”,很多人直言这里面一定存在虚高;二是“银行把债务低价甩卖出去,是否也应该对后续合理性负责?”毕竟如果银行当初能适度减免或延长周期,或许企业还能喘口气,而不是被逼到绝境。 有人担心这种低价甩卖债权的做法,会成为压垮民营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旦大面积发生,势必影响整个地方经济生态。毕竟像白某这样的企业解决了就业,还承担了纳税义务,如果因为资本运作被“围猎”,那对谁都没有好处。 些银行采取了打包甩卖,这和政策导向背道而驰,也让类似的纠纷不断上演。从1400万元到5125万元,这个数字的膨胀,本身就足够令人震惊。此事折射的不只是一个企业家的困境,更是当下民营经济发展中潜藏的制度矛盾。白某说得很直白:“我不是不还钱,但不能让我还糊涂钱。”这句话或许道出了无数中小企业家的心声。 信息来源:时代周报2025-09-16发布:1300多万贷款被大连银行低价甩卖后,变成5000多万债务,一家川企困在债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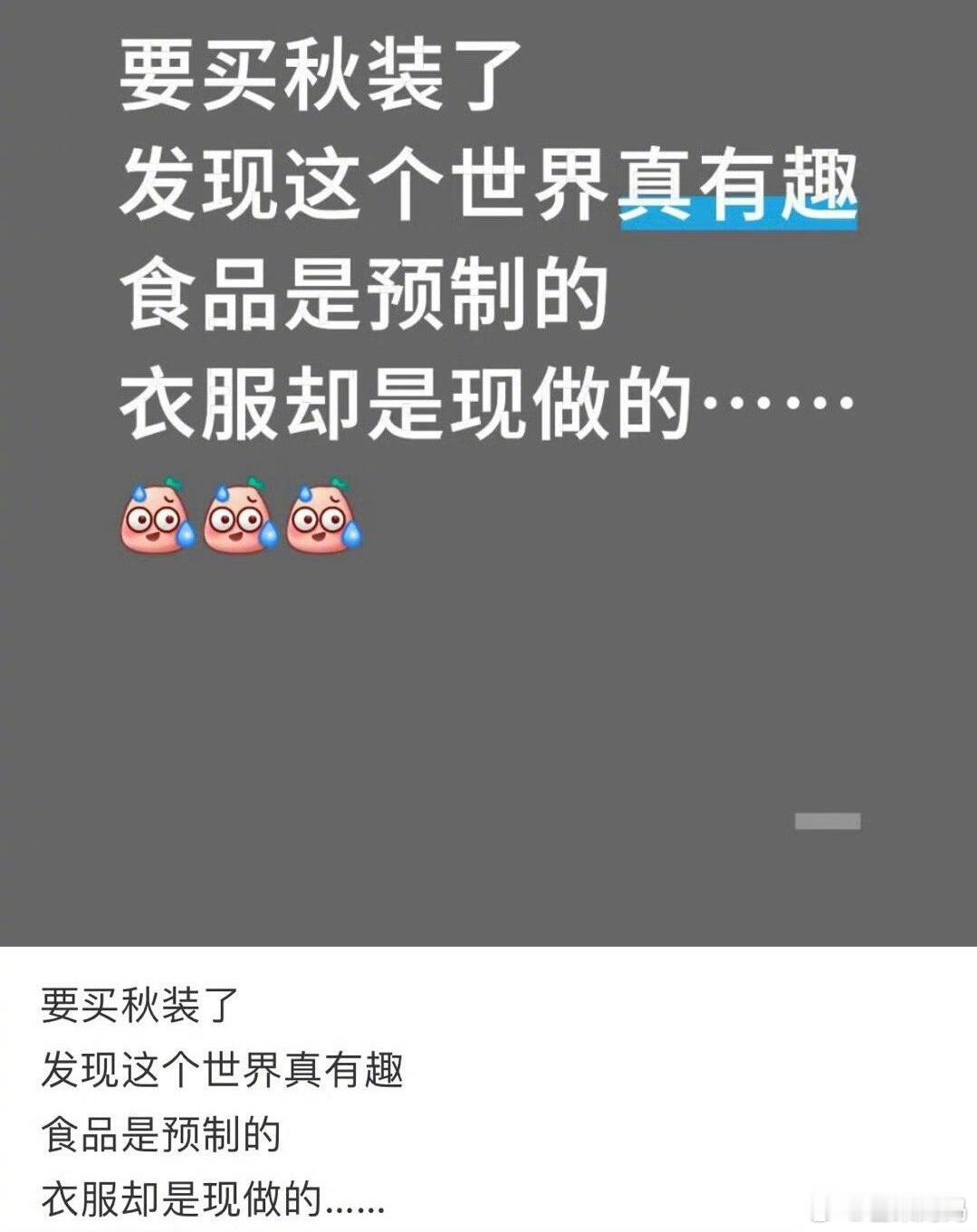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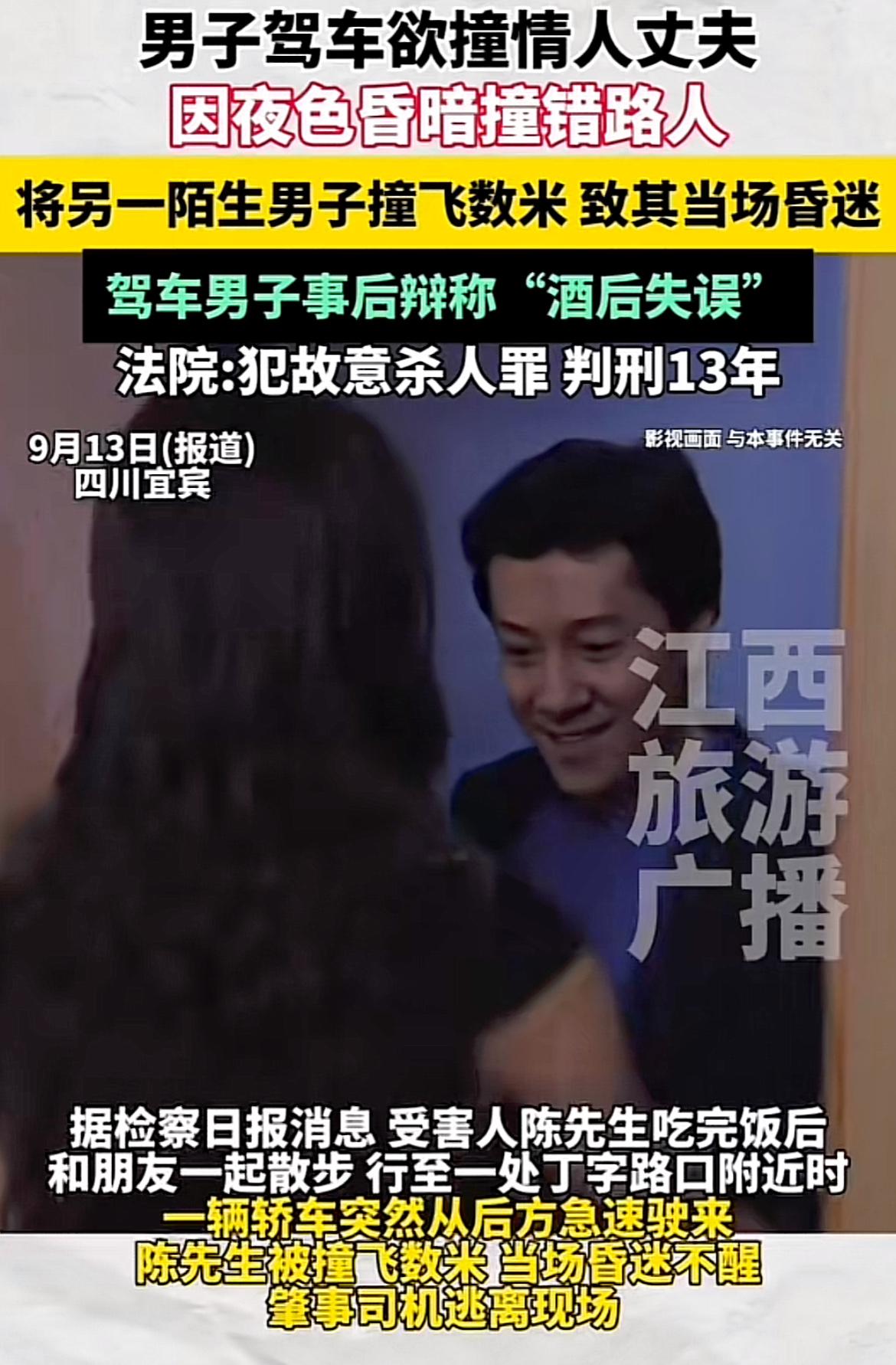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