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酸,父亲半夜快不行了,给家人提出个要求说:心里热,想吃个冰棍,家人问吃奶油的行吗?父亲说:不对口味,我就爱吃老冰棍,然后家人半夜跑了好几家超市,才买到老冰棍,拿回来敢紧让父亲吃,父亲吃后,不到二个小时安祥的走了,家人都悲痛万分。网友:就欠这一口老冰棍。 老头儿嘴挑,一辈子只认三块五一根的“老冰棍”,白糖水加香精,冻得梆硬,嚼得咯吱响。小时候我偷舔一口,冰得跳脚,他笑我没出息:“这点凉都扛不住?”谁想到,临了临了,他竟要靠这点凉扛过最后的热。 那晚十一点四十七分,医院走廊的灯白得吓人。妈贴着病床,嗓子发干:“真只要冰棍?奶油的行不?”爸摇头,像当年拒绝我买的奶油蛋糕一样固执:“腻,齁甜。”两个字,把眼泪给我砸下来。我转身就跑,电梯等不及,从十二层楼梯间一路蹦下去,心脏砰砰,跟小时候偷跑出去给他买烟一个节奏。 楼下小卖部卷帘门半拉,老板正打王者。“老冰棍有吗?”“奶油?老冰棍!”我吼得破音。老板吓一跳,指冰柜最底层:“就两根,冻了仨月,你要给你。”我掏出十块,连零钱都不要,攥着冰棍往外冲。零下五度的夜,手冻得没知觉,可棍子在我掌心冒白气,像抓住最后一口阳气。 回病房,妈已经哭成泪人,护士悄悄撤了监测仪。爸看见我,眼神亮了一下,像孩子看见放学来接的家长。我剥开包装,纸黏在棍上,他接过去,先舔一口,再咬一口,咯吱咯吱,声音大得整个病房都能听见。我别过脸,眼泪往口罩里灌。他吃完半根,摆摆手:“够了,凉到心了。”说完靠在枕头上,长出一口气,像夏天干完农活,灌下第一口井水。 一点零九分,心电图画成直线。妈扑过去,我握着爸的手,还残留冰棍的凉,慢慢被体温捂热,最后一点凉气散去,我知道,他真的走了。那根木棍被我偷偷塞进兜里,回家洗净,立在书桌笔筒里,谁看都像根普通冰棒棍,只有我知道,它撑住了一个老头儿离开前的最后体面。 后来整理遗物,翻出他年轻时写的日记:1978年8月,领第一月工资,花四毛八分钱买了根老冰棍,请工友们吃,大家轮流嗦,甜到心里。我这才明白,他惦记的不是冰棍,是那段穷得叮当响却有人一起笑的岁月。老冰棍于他,是青春,是日子,也是“我还活着”的明证。 出殡那天,我买了整整一包老冰棍,放在灵堂前。来吊唁的亲戚一人一根,孩子们吃得满嘴冰碴,大人们边吃边抹泪。齁甜的凉气混着香火,竟也不违和。有人在朋友圈发图:老爷子请全楼吃冰棍,爽!底下一排蜡烛表情。我盯着屏幕,突然笑了——老头儿要是看见,肯定又得骂我:“臭小子,又浪费钱!” 现在每年夏天,我都会批一箱老冰棍,塞满冰箱冷冻层。热得受不了时,掏一根,咯吱咬一口,白糖水混着冰碴子,从舌尖凉到心口。那一刻,我仿佛又听见病房里咯吱咯吱的声音,听见他说:“这点凉都扛不住?”我扛得住,也必须扛得住。因为老冰棍教会我:人这一辈子,总要留一口念想,好让离别不那么苦,让记忆有处安放。 网友说“就欠这一口老冰棍”,其实欠的是一次好好告别。别让“等有时间”“等有钱”变成遗憾,爸妈要的不是海参鲍鱼,也许只是一根三块五的冰棍、一次散步、一句“我在呢”。趁他们还能张嘴,趁我们还能跑腿,跑一跑吧,别等凉气散了,才想起热得难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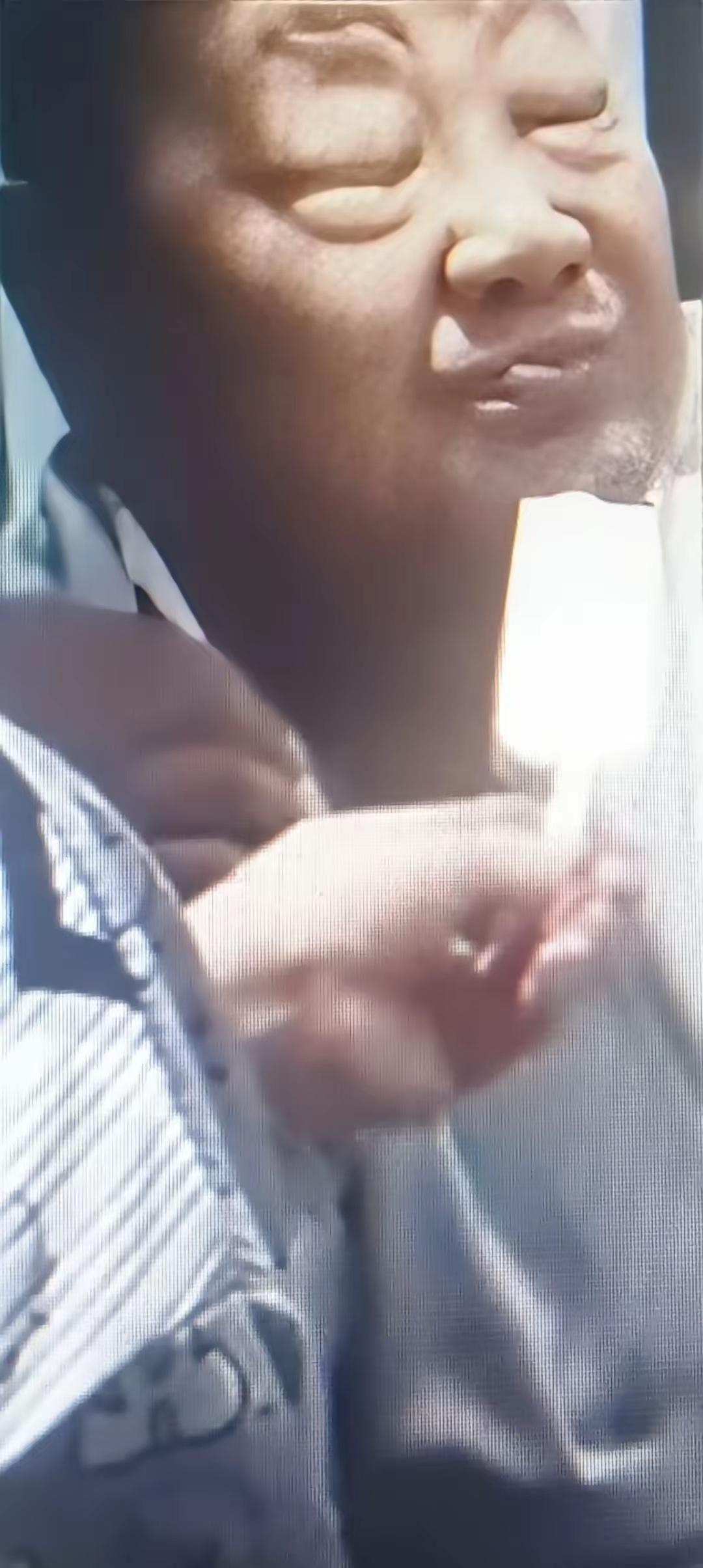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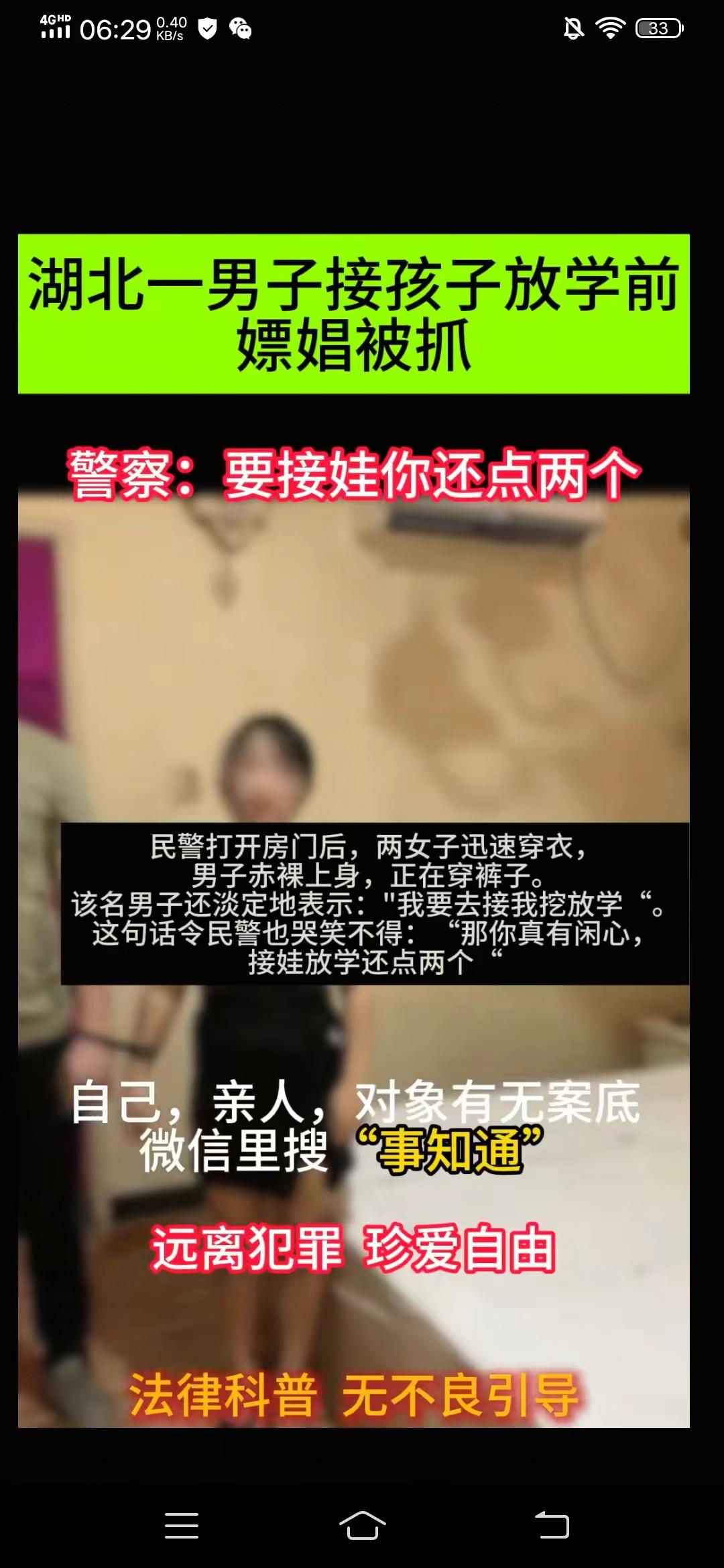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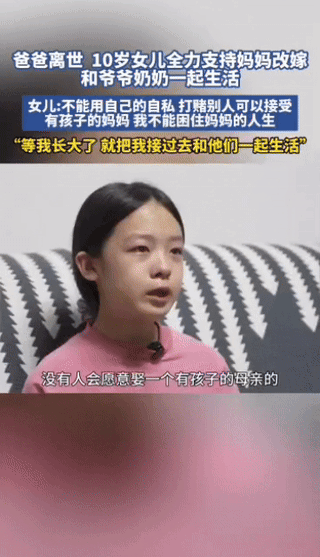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