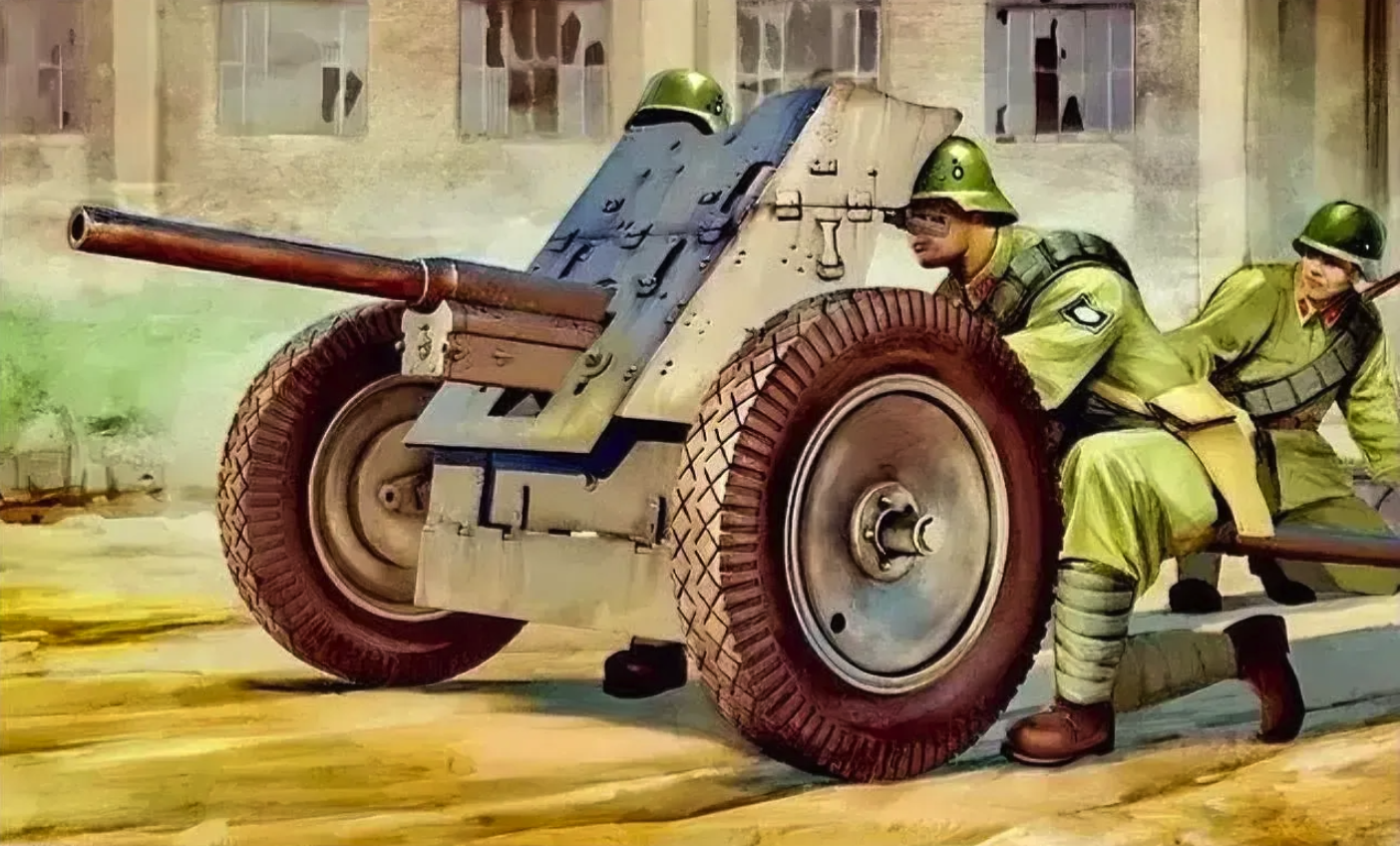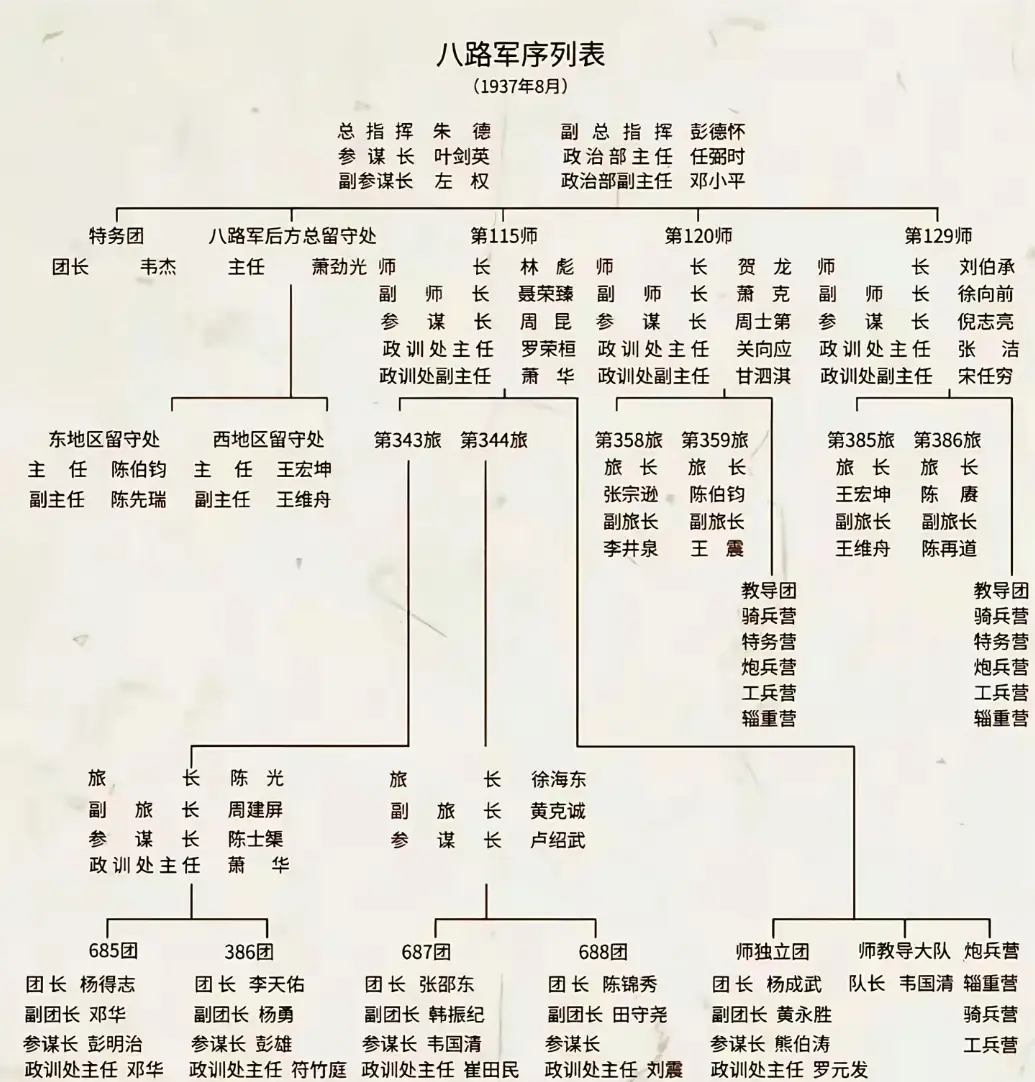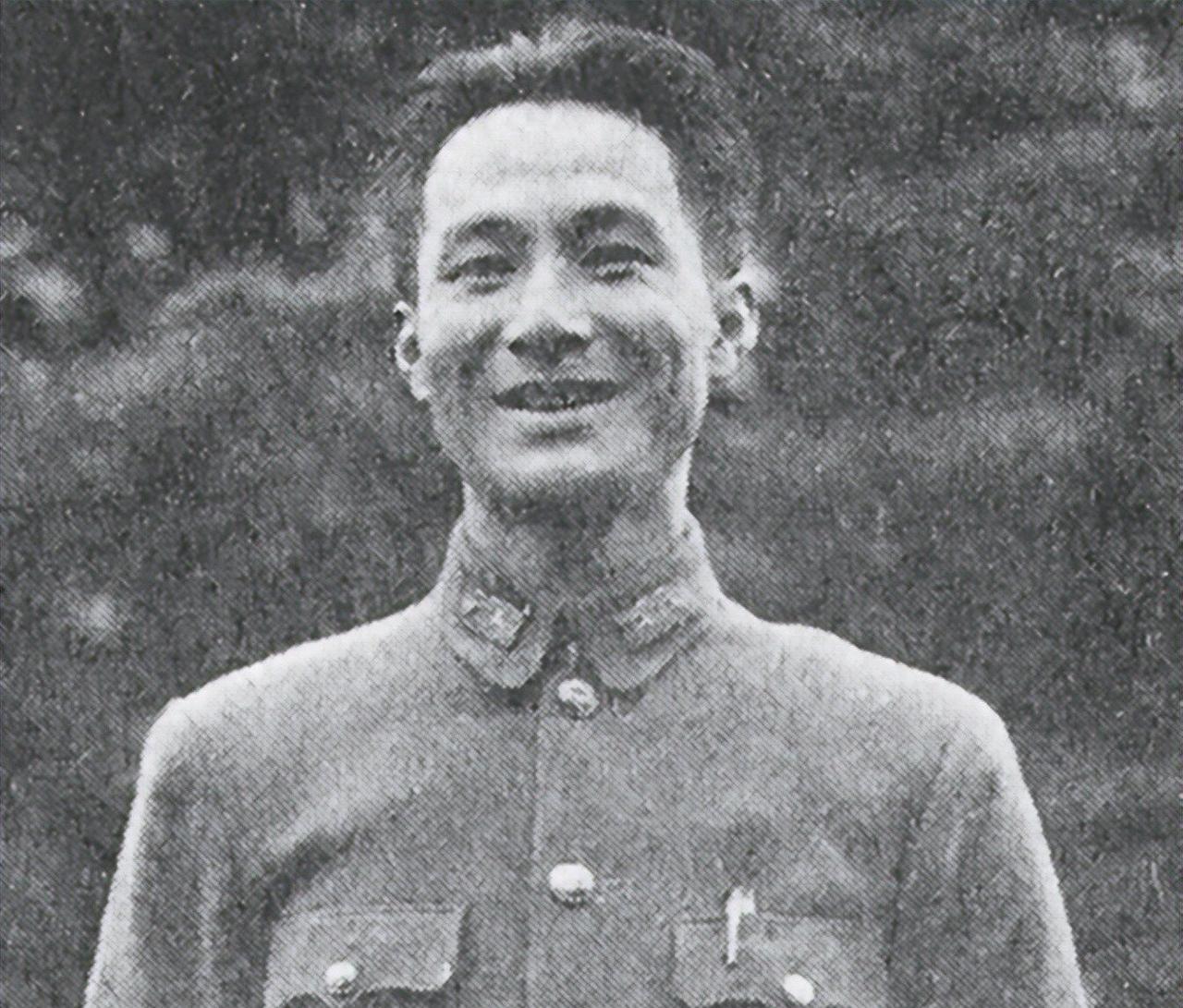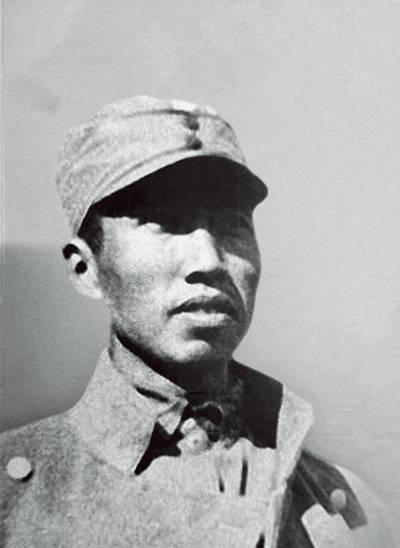1942年,八路军战士赵培宪被俘,日军捆住他的双手,把他押到训练场给新兵练刺刀,但被赵培宪察觉到了异常,他一把推开日军,转身跳下悬崖! 1942年,赵培宪被日军押送出营地,手脚紧缚,步履沉重,他是前线八路军中的一员,在一次突围行动中因情势突变而被俘,连同数百名战士一同羁押于所谓的“工程队”劳役场所中。 这里名为工程,实为囚牢,日军在此地实施各种酷刑,并将中国战俘当作活体工具,训练新兵的杀戮本领。 那一日他与十余人被选出,说是要接受“日军安排的新劳役任务”,赵培宪一贯心思缜密,自踏出牢门的那刻起便警觉地打量四周,他留意到这次不同寻常,押送的兵士多了,带枪者占了大多数,道路也不是通往营地工区的方向。 最为异常的,是他们行经的一片空旷地带周围架设着粗陋的篱笆,还有数名日军正在检查刺刀,他意识到这并非普通调度,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感在心头升腾。 行至开阔地,他看见泥土地上零散残留着褪色的血迹和一些未掩的浅坑,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腥味,他们被分组排队,每人双手反绑,赵培宪处于中列。 日军一名军官站在高台之上,手握望远镜,冷漠地巡视着周围的动静,似乎在确认一切安全无误,场地另一端,几十名新兵正排成一列,刺刀寒光闪烁,神情紧张又隐隐兴奋,这一切无声地揭示着即将发生的残忍行径,这是一场精心组织的处决训练。 赵培宪心如止水,神经紧绷,他默默观望地形,注意到空地南侧有一处向下倾斜的陡坡,尽管坡下地形难测,但他判断若能跳下,或许能借坡势摆脱困境。 他开始有意识地调整身体重心,在不引起注意的前提下试图活动手腕,将麻绳悄悄地向外拉动,他知道机会稍纵即逝,一旦被发现,只会加快死亡的到来。 前两组战俘已经被推至近前,新兵在敌人的命令下开始进行刺杀,一声声惨叫划破天际,赵培宪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寻找破绳的节奏和突围的最佳时机上。 很快战俘队伍依次前移,轮到了他的那一组,当他被推至空地边缘,面对敌兵亮出的刺刀时,他猛然向前撞击,肩膀正中敌兵胸膛,将对方击倒在地,场面顿时混乱,赵培宪借势猛力扯断残余的绳索,转身朝坡地方向奔去。 后方传来喊叫与枪声,日军在慌乱中开火,子弹擦着他的身后破空而来,激起尘土,他没有回头,纵身跳下,那处坡度极陡,碎石与荆棘遍布,他在下滑中被刮破皮肉,衣物撕裂,鲜血与汗水混作一团,但这痛楚于他而言远不及被刺刀穿透的那种绝望。 滚至坡底,他迅速爬起,冲入一片林地,林中枝繁叶茂,光影斑驳,他穿梭其间,凭借过去多次执行任务对地形的熟悉,迅速找到可藏身的隐蔽点。 他藏入一处树根交错形成的低洼处,尽量屏住呼吸,抑制心跳,不多时几名日军追兵进入林内,他咬紧牙关,直到他们的声音渐远,才敢再次移动。 林中曲折而幽深,赵培宪在枝叶遮掩下跌跌撞撞地穿行,饥饿与疲惫如影随形,他最终绕行至一处小溪,凭借积年记忆分辨方向,朝八路军某处秘密联络点前进。 历时近一天的奔逃,当他终于靠近那处根据地外围的哨岗时,整个人几乎脱力,他挥手示意,险些瘫倒在地,被守岗战士扶住。 赵培宪的归来让战友们无比震惊,他的身上遍布伤痕,神情却坚定如旧,在治疗后,他不顾身体虚弱,向上级详述所见所闻,特别强调日军设立战俘刺杀训练场这一事实,最终这一残暴行为得到了广泛揭露,并被列入反侵略宣传材料之中。 此后赵培宪继续坚持在敌后开展敌工工作,参与组织数次反击,直至抗战胜利,他认为自己活下来,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侵略者的罪行必须被记住,战士的牺牲不容白费,这份信念支撑他走完了此后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