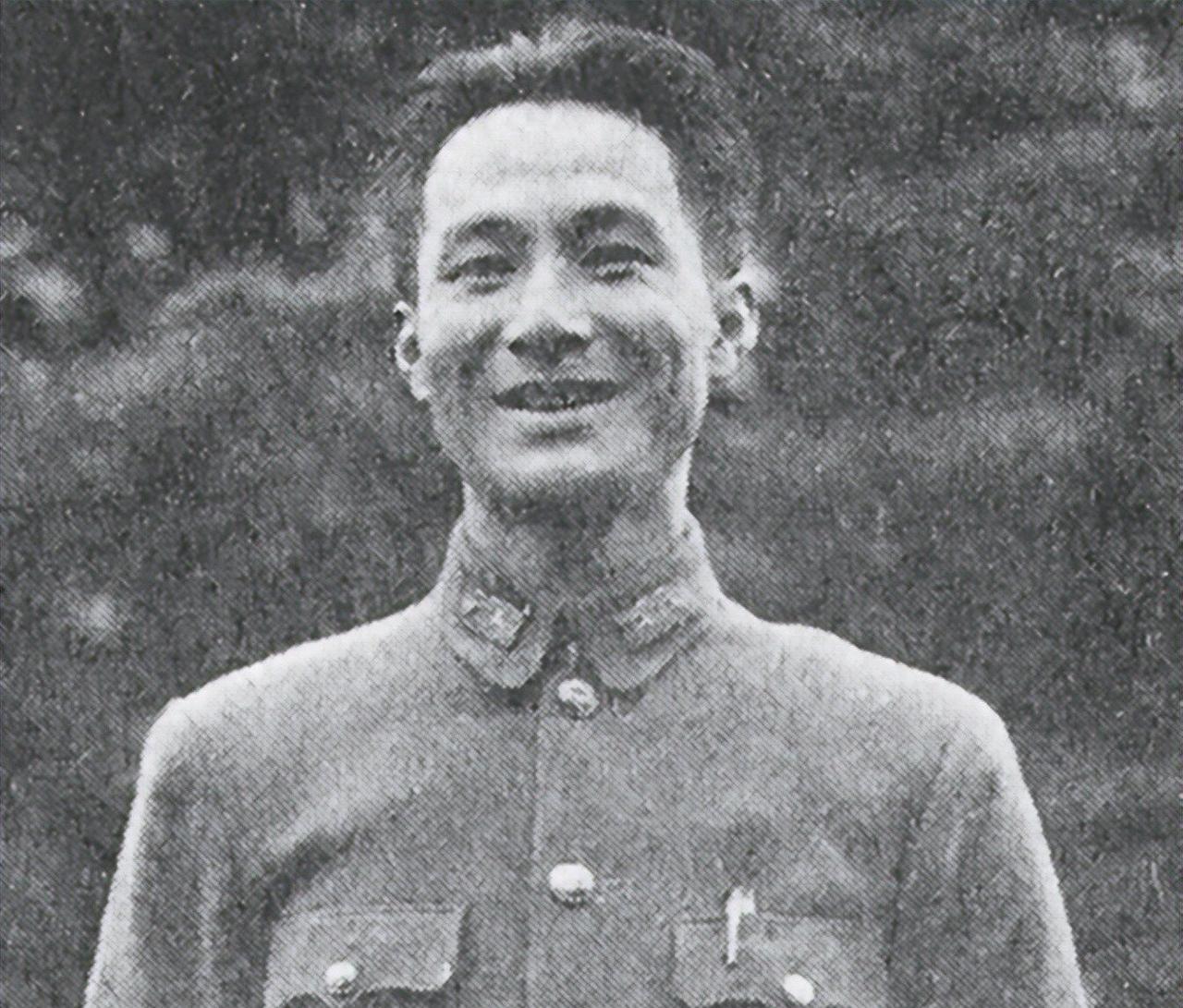1941年,朱凡被俘,日军见普通酷刑无法让她开口,就把她带到湖边,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你说不说?” 1941 年深秋的太湖,两艘日军汽艇像嗜血的鲨鱼,在芦苇荡边缘焦躁地游弋。 艇身之间,30 岁的朱凡被粗麻绳紧紧捆住,左腿系着左侧汽艇的尾锚,右腿连着右侧艇的缆桩。潮湿的芦苇叶粘在她渗血的裤腿上,混杂着额头流下的血珠,在下巴尖凝成细小的血滴。 “朱凡小姐,最后问你一次。” 日军少佐松井的军靴碾过船板,皮靴上的铜扣在阴雨天里泛着贼光,“中共苏常太工委妇女部长的位置,不是让你逞英雄的。说出来,藏在芦苇荡里的电台在哪,你们的武装小队今晚要袭击哪个据点?” 朱凡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干裂的嘴唇扯出一丝冷笑。 三天前在常熟徐市的那场突袭,她本有机会带着机密文件撤离,却为掩护两名年轻交通员,故意把日军引向反方向的粮仓。当她砸碎电台密码本吞下腹时,就没想过活着看到明天的太阳。 被捕那天的情景还在眼前翻滚。朱凡刚在张家浜开完妇女救国会的会议,藏在旗袍夹层里的是新拟的《抗日救亡妇女动员章程》。 忽然听到街面上传来枪声,她迅速将文件塞进灶台的砖缝,转身想从后门转移,却被两个端着三八大盖的日军堵住。 “你就是那个给游击队送药的女共党?” 松井晃着从她住处搜出的《论持久战》,书页间还夹着半截没烧完的情报。朱凡挺直脊背,藏在袖管里的碎瓷片已悄悄攥紧 —— 那是准备随时自尽的工具。 审讯室里的煤油灯忽明忽暗,映着墙上 “效忠天皇” 的标语格外刺眼。松井把搪瓷缸重重墩在桌上:“你们的地下交通线有多少站点?上个月从上海运来的药品藏在哪里?” 朱凡盯着他军装上的旭日徽章,忽然想起入党时宣誓的场景,那面用红布缝的党旗,边角还沾着同志们的体温。 “我不知道。” 三个字像石头砸在地上。松井的指挥刀猛地劈向桌角,木屑溅了朱凡一脸:“给我打!” 两个宪兵立刻扑上来,皮鞭带着风声落在她身上。蓝布旗袍很快被抽得粉碎,露出的皮肤上渗出血痕,但她始终咬着牙,连闷哼都没有。 第二天清晨,朱凡被拖进刑讯室时,看到墙上挂满了刑具。烙铁在炭火里烧得通红,旁边的木架上还挂着沾血的镣铐。 松井坐在太师椅上,慢条斯理地擦拭指挥刀:“听说你是苏州女子师范毕业的高材生,何必跟着土八路吃苦?只要说出情报,皇军保证送你去东京深造。” 朱凡咳出一口血沫:“你们烧杀抢掠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中国的姑娘也想好好读书?” 话音未落,宪兵就将烧红的烙铁按在她的胳膊上。 “滋啦” 一声,皮肉烧焦的气味弥漫开来,朱凡疼得浑身颤抖,眼前阵阵发黑,却死死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倒下。 松井看着她臂上鼓起的燎泡,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像太湖底的顽石。他们试过灌辣椒水,她呛得肺都要咳出来,却还是摇头;用竹签钉指甲,十指连心的剧痛让她几次昏死过去,醒来依旧只有三个字:“不知道。” 第三天傍晚,松井终于失去耐心。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却眼神依旧锐利的朱凡,突然露出狰狞的笑:“看来普通的办法对你没用。太湖的水很清,正好让你清醒清醒。” 松井站在船头,举着望远镜看向远处的芦苇荡:“你的同志们大概就在那片芦苇里吧?只要你点头,这一切都能结束。” 朱凡深吸一口气,潮湿的空气里带着水草的腥气。她想起三个月前,刚担任妇女部长时,工委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妇女工作是前线的后盾,你们的笔和针线,都是杀敌的武器。” 那些被她动员起来的农村妇女,有的送子参军,有的冒着风险传递情报,她们的笑容此刻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 “开船!” 松井见她不语,狠狠挥了挥手。左侧汽艇首先发动,麻绳瞬间绷紧,朱凡的左腿传来撕裂般的剧痛。她疼得眼前发黑,却用尽全身力气喊道:“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右侧汽艇也随即启动,两股巨大的力量同时撕扯着她的身体。骨头断裂的声音在引擎声中显得格外清晰,朱凡的意识开始模糊,但嘴里的口号始终没有停止。鲜血顺着裤腿流进湖里,染红了一片水面,像极了她最喜欢的那朵红牡丹。 松井看着在痛苦中依旧挺直脊梁的朱凡,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这个看似柔弱的中国女人,身体里仿佛藏着无穷的力量,那是他们用枪炮也无法摧毁的信仰。 当汽艇终于停下时,湖面已经恢复了平静,只有几片染血的芦苇在水波中沉浮。松井站在船头,望着茫茫太湖,第一次对这场战争产生了怀疑。 三个月后,在朱凡牺牲的地方,游击队成功伏击了一支日军运输队。战士们在冲锋时,都想起了那个被绑在两艘汽艇之间,却始终高昂着头颅的女战士。他们说,那天的风里,仿佛还能听到她喊出的口号。 如今的太湖早已碧波荡漾,芦苇荡里建起了纪念馆。 朱凡的事迹被刻在石碑上,供后人瞻仰。每当有人问起那段历史,当地的老人总会指着湖面说:“看见没?那片最清澈的水域,就是朱凡同志用生命守护的地方。” 风拂过湖面,带着遥远的回响,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永不褪色的誓言:有些东西,比生命更重要;有些信仰,能让柔弱的肩膀,扛起一个民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