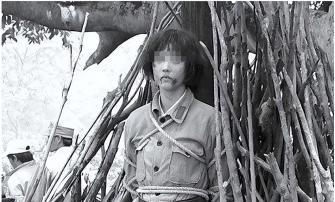1918年,广东茂名。一位年轻女子站在旧祠堂外,手中紧攥着一张休书,眼神空洞。她才二十出头,已被丈夫抛弃六年婚姻。她说她不能生孩子。可谁能想到,几年后,她却成了“广东之母”,一连生下11个孩子,还嫁给了日后名震南粤的军阀陈济棠。 她的名字,叫莫秀英。 莫秀英出生于广东茂名一户人家,祖上经营过些小生意,日子还算过得去。可惜年纪小,她刚记事,家道便中落。十二岁那年,她被迫嫁人,对方是邻村有钱人家的三房妻。 她年纪小,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婚姻。家中上下对她并无太多期待。六年过去,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婆婆说她命硬,丈夫越来越冷漠,最后干脆另纳新妾。她成了摆设,成了不被需要的人。 1918年秋天,婆家终于“下了决定”,送她一纸休书,让她卷铺盖走人。她拿着那张纸,没处可去。回娘家遭拒,亲戚避之不及。一个没有孩子的被休女子,在那个年代等于废人。 为了活下去,她走上街头,加入戏班、跑码头、进茶楼,用一把好嗓子唱戏卖艺,换点饭钱。她唱的是《贵妃醉酒》《荀灌娘》,但没人关心剧情,只看她长得好看,听她嗓音清亮。 她习惯夜晚收摊时自己抱着衣包走,没人接送。她习惯数着铜钱睡觉,第二天睁眼继续唱。这种日子一过就是一年多,她早已不相信男人,不相信命运。 可命运偏偏选中她,要和她开个玩笑。 1918年底,一个秋夜,她照例在歌厅演出。 那天观众不多,灯光昏暗,只有前排几位军人打扮的客人引人注意。其中一位身材挺拔、目光坚定,听得极为专注。他就是陈济棠,当时在国民党粤军中任职,年轻有为,风头正劲。 演出结束后,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留下赏银,而是通过茶馆老板,悄悄送来一封信与一套金钗,说希望与她见一面。 一见之后,两人频繁往来。她警惕,他坦率;她回避,他执着。很快,陈济棠提出娶她。 她一口拒绝。她告诉他自己“有病”,不能生孩子。她不愿耽误他,不愿再受一次被弃的苦。 可陈济棠摆手,说他不在乎。 这句话,没换来她立刻点头,但却埋下了一颗种子。 过了一个月,她终于答应嫁他。没有隆重仪式,没有吹打迎亲,只有一场小型的家宴。从那一刻起,她脱下花衣,改口称“陈太太”,真正走入他的生活。 谁也没料到,她的命运,从此彻底翻篇。 婚后不久,她就怀孕了。 她不敢相信,也不敢告诉别人,直到胎动清晰,才鼓起勇气告诉丈夫。陈济棠高兴得连夜设宴,亲自去买补品。从此之后,这个“不能生”的女人,变成了一台生育机器。 十多年里,她接连不断生下11个孩子。 前后有男有女,长幼排列整齐,几乎每年一个。每次坐月子,她都亲自喂奶,不请乳母。她坚持亲手带孩子,训导他们读书写字,连家仆都被她分门别类管理清晰。 孩子多,家务多,可她从不乱。 除了持家,她还陪陈济棠走南闯北,从广州到潮汕,从海南到韶关。陈济棠官至广东省主席,主政岭南,她便成了“将军夫人”。 但她没有张扬,而是用另一种方式赢得百姓尊敬。 她出资在家乡修路架桥,设义学、办诊所,还在广州开设贫儿育婴所,专收弃婴、难民儿童。每次赈灾,她必亲自分粮发药。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只说一句:“我做母亲的人,看不得别人孩子饿。” 到了1935年前后,她在广东妇孺中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官方。“广东之母”的称号,逐渐传开。报纸上开始出现她的名字,儿童画册上出现她的形象。她,已经不是那个被抛弃的小妇人了。 1936年,陈济棠因政治斗争被迫下野,离开广东。 她没有怨,也没有哭,只是默默收拾家当,带着孩子跟随丈夫迁往香港、后又转往越南、重庆。战火纷飞,她一个人照顾全家十一口,身心俱疲,却没有一个孩子辍学或受难。 1947年,她病重,卧床多日。临终前没有说教,没有嘱托,只让人把她生前亲笔写下的一封信和一些财产分交给家乡学校和育婴所。 那一年,她的孩子们几乎都长大成人,其中多人成才。她的丈夫陈济棠终其一生都说:“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就是娶了她。” 她的祠堂,如今还在广东茂名。村口有一条路叫“秀英路”,那是乡亲们为纪念她而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