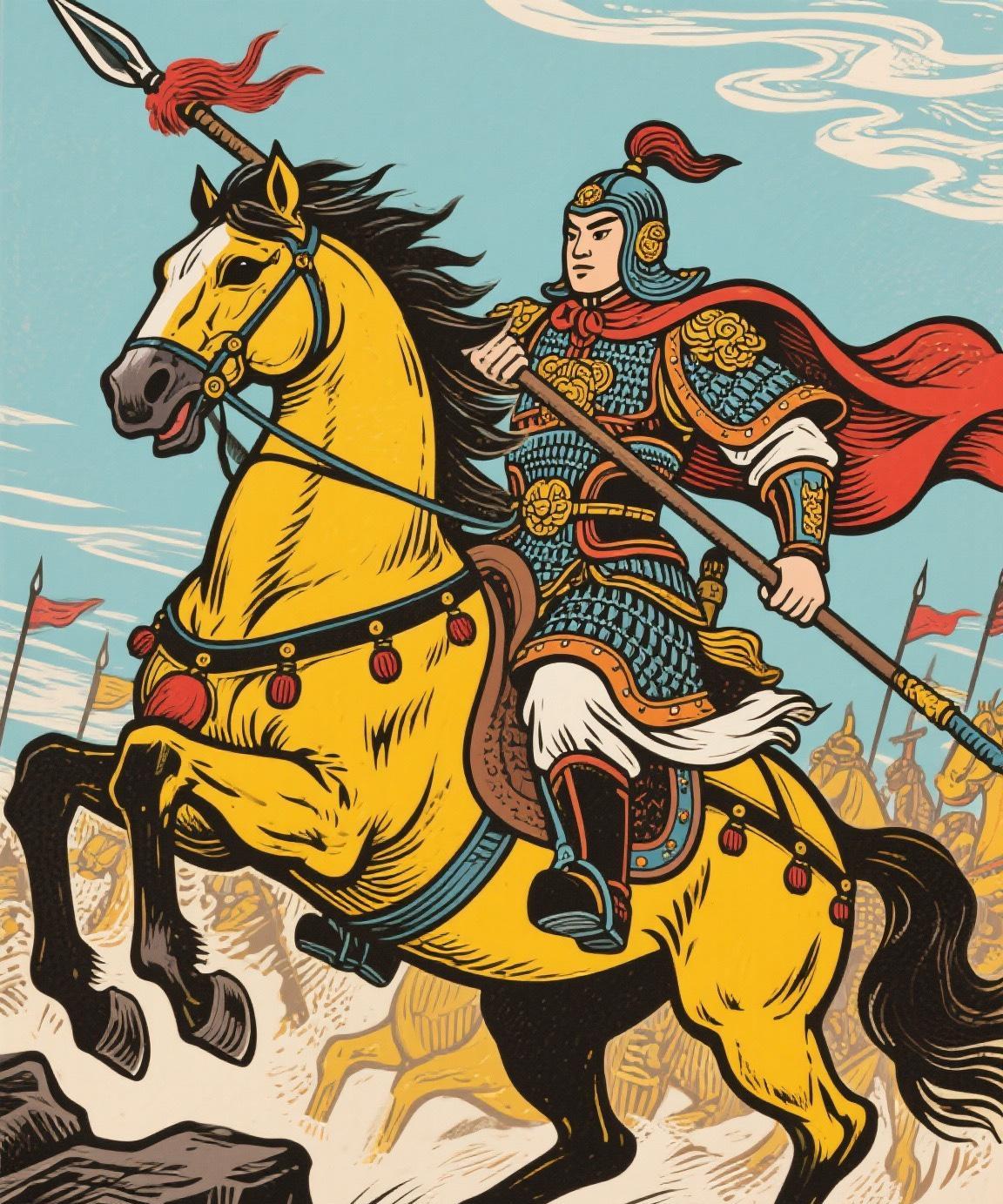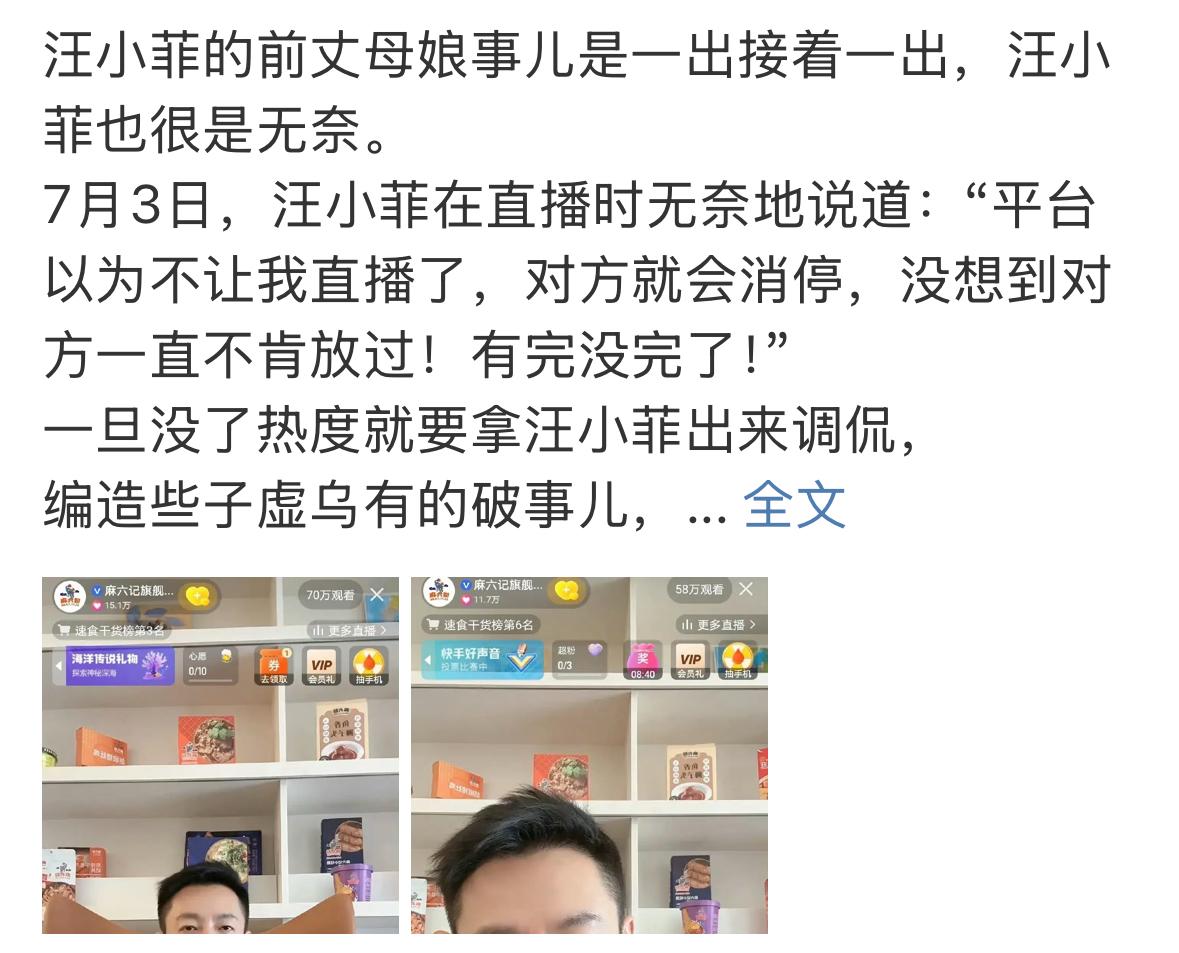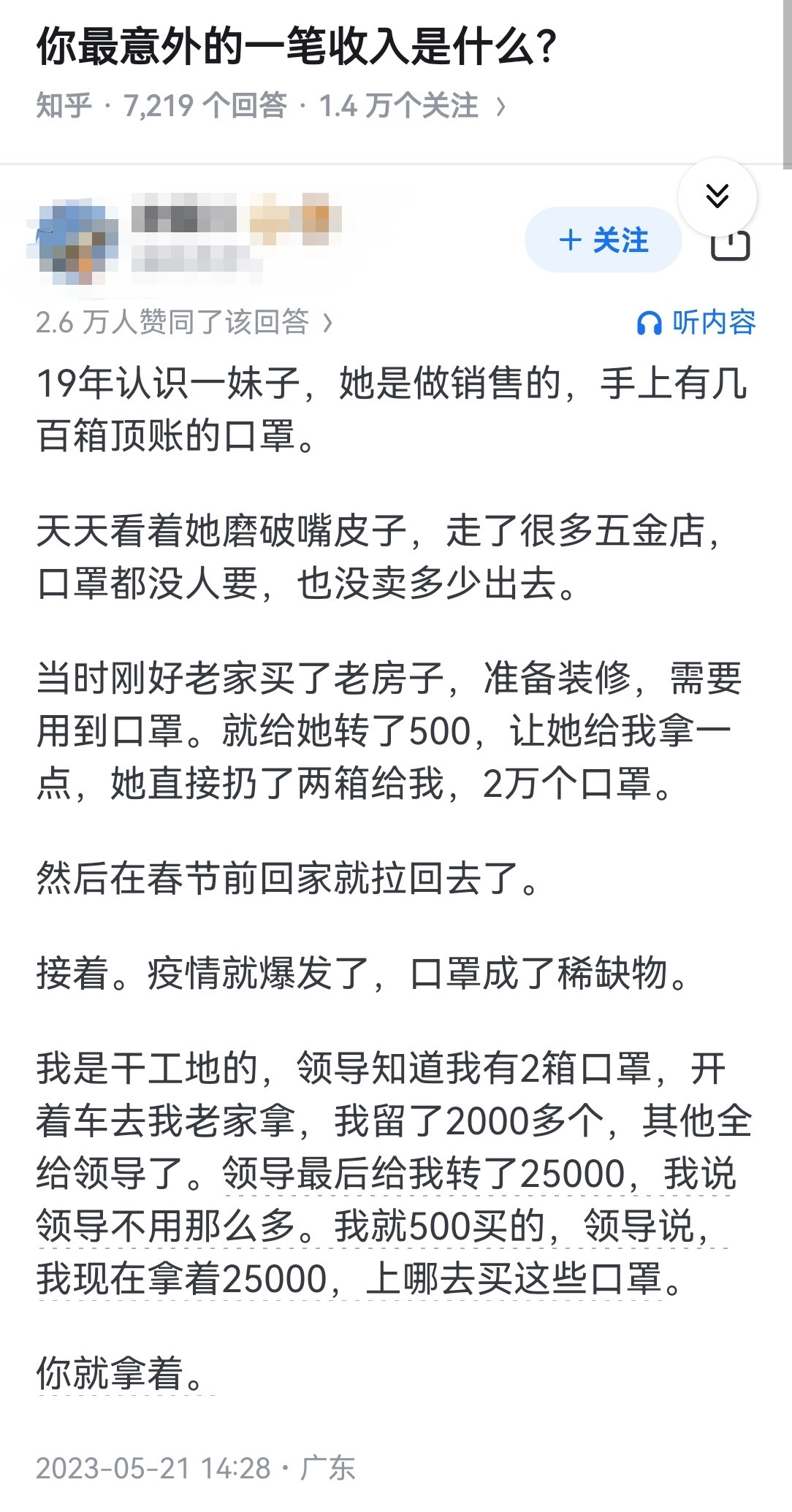东汉末年,17岁的刘兰芝遭到婆婆焦母刁难,无奈之下回了娘家。焦母以为自己赢了,没想到儿子焦仲卿只对她说了一句话:“不能承欢膝下,望珍重。”焦母不以为然,结果,焦仲卿在刘兰芝再嫁人后上吊而亡。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东汉末年,一首《孔雀东南飞》让一对夫妻的悲剧流传千年。17岁的刘兰芝嫁入庐江郡小吏焦仲卿家,本以为是良缘,却在婆婆焦母的刁难下走向生死离散。 焦母最初对刘兰芝的“热情”,像精心设计的局。刘兰芝出身庐江大姓,十三岁能织机杼,十四岁善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已是方圆百里闻名的“才女加贤女”。 焦家虽非高门,焦仲卿也已二十岁未娶,在当地算“大龄男青年”。为给儿子说亲,焦母隔三差五拎着酒肉去刘家,嘴上说着“讨教持家之道”,实则早把刘兰芝的底细摸得透熟。 刘家父母起初有些犹豫,焦仲卿虽在县衙当差,却只是个“吏”,俸禄微薄,未必能护女儿周全。 但架不住焦母“礼数周全”,又听闻她“最是通情达理”,到底应了这门亲。婚前焦母拍着胸脯保证:“我儿子娶媳妇是为疼人,家里事你说了算,不用你伺候我。”刘兰芝听着贴心话,带着对小家庭的期待嫁了过去。 现实却像盆冷水兜头浇下。新婚第三日,焦母就变了脸:天不亮就要刘兰芝起来奉茶,饭要做得合全家口味,打扫要一尘不染,还得抽空织布贴补家用。 从前说“不用伺候婆婆”的承诺,早被抛到九霄云外。最让刘兰芝崩溃的是焦母的“双标”:在儿子面前,她是“慈母”。 见了儿媳,立刻变成“恶婆婆”。焦仲卿下班回家,常见妻子眼眶泛红,问起来只说“无事”;焦母却总在他耳边念叨:“你媳妇懒得很,饭做得寡淡,地扫得不干净。” 矛盾在焦仲卿的调解下暂时缓和过。当刘兰芝哭着说“娘,我真的尽力了”,焦仲卿气冲冲找母亲理论:“儿子娶妻是为有个伴,您何苦这样苛待她?” 焦母一听更恼,拍着大腿哭:“我辛苦把你拉扯大,你倒护着外人!你要是不休了她,我就去寻短见!”在“孝道大于天”的汉代,“休妻”是丈夫的权利,“被休”却是女人的耻辱。 焦仲卿夹在中间,既怕母亲气出病,又舍不得妻子受委屈,最后只能咬着牙说:“娘,咱们暂时分开吧。” 刘兰芝回娘家的日子,远比想象中难熬。哥哥觉得“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转头就给她定了亲——对方是太守家的公子,聘礼丰厚,能给刘家挣足面子。 迎亲那日,刘兰芝穿着红嫁衣站在门前,远远看见焦仲卿站在街角。他没敢靠近,只是红着眼眶看了她最后一眼,转身消失在巷口。 刘兰芝在新房里坐了整夜,天一亮就投了村外的河。消息传来时,焦仲卿正攥着她留下的绣帕发抖。 他跪在母亲床前哭:“儿子不孝,让您白发人送黑发人。”焦母这才明白,自己当年赶走的,是儿子命里的光。她抱着儿子的尸体,哭到声嘶力竭,三天后也跟着去了。 后来,刘兰芝和焦仲卿被合葬在华山脚下。当地人说,每年清明总能看见一对身影在墓前徘徊,像在诉说当年的遗憾。 《中国国家地理》曾分析汉代家庭矛盾:“当时的'孝道'更多是维护家族秩序的工具,个体情感常被制度碾压。” 《光明日报》在解读《孔雀东南飞》时也提到:“这个故事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真实记录了普通人在伦理枷锁下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