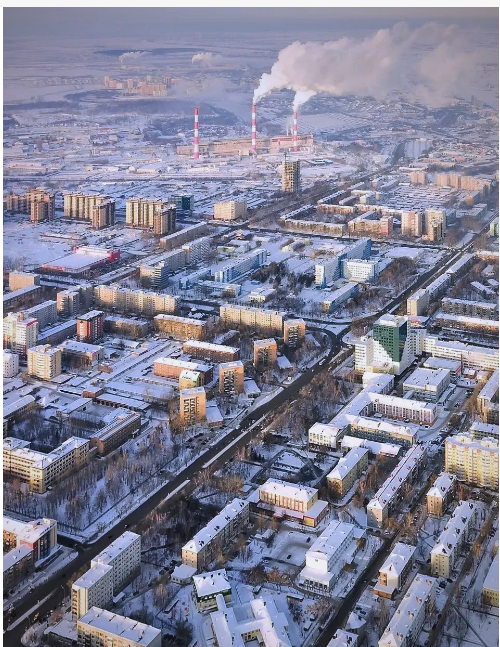1979年,51岁刘禄曾在美国餐馆吃饭,一名美国中年男子猛地冲上前问:“你是朝鲜战场上的刘翻译吗?我是您的俘虏啊!” 1979年春天,北京飘着细雨,51岁的刘禄曾整理着行李,准备随教育代表团赴美访问。作为外事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的出国任务对她来说已不算新鲜。然而,她未曾想到,这次平常的访美之行,会让尘封已久的往事重新浮出水面。 访问团抵达美国后行程紧凑,一连几天的会议和参观让大家疲惫不堪。这天午餐时间,刘禄曾与几位同事走进了一家装修简洁的美式餐厅。她正低头查看菜单,忽然,餐厅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天啊,是您吗?"一位中年男子站在她面前,双眼通红,声音微微颤抖,"您是朝鲜战场上的刘翻译吗?" 刘禄曾抬头,面前这位已有些发福的美国人眼中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他热切地用英语问道:"您还记得我吗?我曾是您的俘虏,我28年都没有忘记您。" 餐厅里的喧嚣仿佛一瞬间消失了。刘禄曾望着这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二十八年前的画面一帧帧在脑海中闪回:寒冷的朝鲜战场,拥挤的战俘营,那个发着高烧的美国士兵…… "伯特纳?詹姆斯·伯特纳?"刘禄曾试探性地问道。 "是的!是我!"中年男子激动地握住她的手,泪水已经在眼眶中打转,"我就是那个被您救了的美国士兵。您还记得我!" 周围的同事和餐厅顾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重逢场景吸引,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伯特纳连忙向餐厅工作人员打了个手势,然后对刘禄曾说:"这是我的餐厅,请允许我招待您和您的同事。" 在一旁的安静角落,伯特纳向刘禄曾展示了他的家庭照片:一位和蔼的妻子,两个已经上高中的孩子。"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生活,从退伍军人变成了小餐馆老板。"他指着照片中笑容灿烂的一家人说道,"但我从未忘记那个在朝鲜战场上对我伸出援手的中国女翻译。您的善良,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显得尤为珍贵。" 刘禄曾听着,脑海中浮现出1950年那个寒冷冬天的场景。那时的伯特纳还是个瘦弱的年轻士兵,被志愿军俘虏后,因高烧被误认为是"装病",登记在了"表现不好"的名单上。如果不是她坚持让军医为他检查,如果不是她在俘虏转移中特意为他安排了车辆,也许眼前这个现在已是餐厅老板的中年男子,早已不在人世。 "那是1950年的冬天,"刘禄曾望着餐厅窗外的阳光,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寒冷的季节,"朝鲜战争刚爆发不久,我还是个刚从东吴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子。" 当时的刘禄曾只有22岁,精通英语的她在听闻志愿军急需英语人才后,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战场上不仅需要能冲锋陷阵的勇士,也需要能沟通交流的桥梁。因为俘虏问题和美军装备辨认问题,志愿军急需精通英语的人才。 "我们一共有23人,都是精通英语的青年,从全国各地赶来。"刘禄曾回忆道,"我们跋涉了上千里,才到达朝鲜中部地区,我被分配到了第九兵团。" 伯特纳听得入神,这些细节是他从未知晓的另一面。在他的记忆中,刘禄曾只是突然出现在战俘营中的一位翻译官。 "我们的任务不是杀敌,"刘禄曾继续说道,"而是辨别美军装备,翻译军事文件和宣传品,还有就是审讯美军俘虏。上级给我们下达了任务,72小时内必须搞清楚所有被俘美军的底细,按照兵种和职务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俘虏营中。" 刘禄曾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伯特纳的场景。那天,她正在审核"表现不好"的俘虏名单,伯特纳的名字赫然在列,原因是"装病"。作为负责审讯的翻译,她决定亲自去了解情况。 "当我看到你时,你正蜷缩在角落里,面色苍白。"刘禄曾看着伯特纳说,"我摸了摸你的额头,滚烫得吓人。那不是装病,你是真的发高烧了。" 刘禄曾立即找来了志愿军军医为伯特纳看病。在随后的战俘转移中,她特意为他安排了车辆,免去了长途跋涉之苦。这在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人道关怀。 "还记得那个总是想刮你鼻子的小战士吗?"刘禄曾问道。 伯特纳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那个十几岁的小战士,总喜欢捉弄我们这些俘虏。" "他还小,不懂事。"刘禄曾解释道,"当我看到他刮你的鼻子时,我告诉他即使是善意的举动,也要尊重俘虏的人格。战争中我们是敌人,但人性不应该被战争摧毁。" 志愿军一直秉持着优待俘虏的政策。即使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尽力保障战俘的基本生活需求,甚至组织文艺活动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刘禄曾作为翻译,亲眼见证并参与了这一过程。 "那时候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从未想过会被人记得这么久。"刘禄曾感慨道。 伯特纳深情地看着眼前这位已有些花白头发的女性,"在战场上,善良比子弹更有力量。您的举动让我看到了战争之外的人性光辉。回到美国后,我常常讲起在中国军队中遇到的这位翻译官,她的名字我一直记得——刘禄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