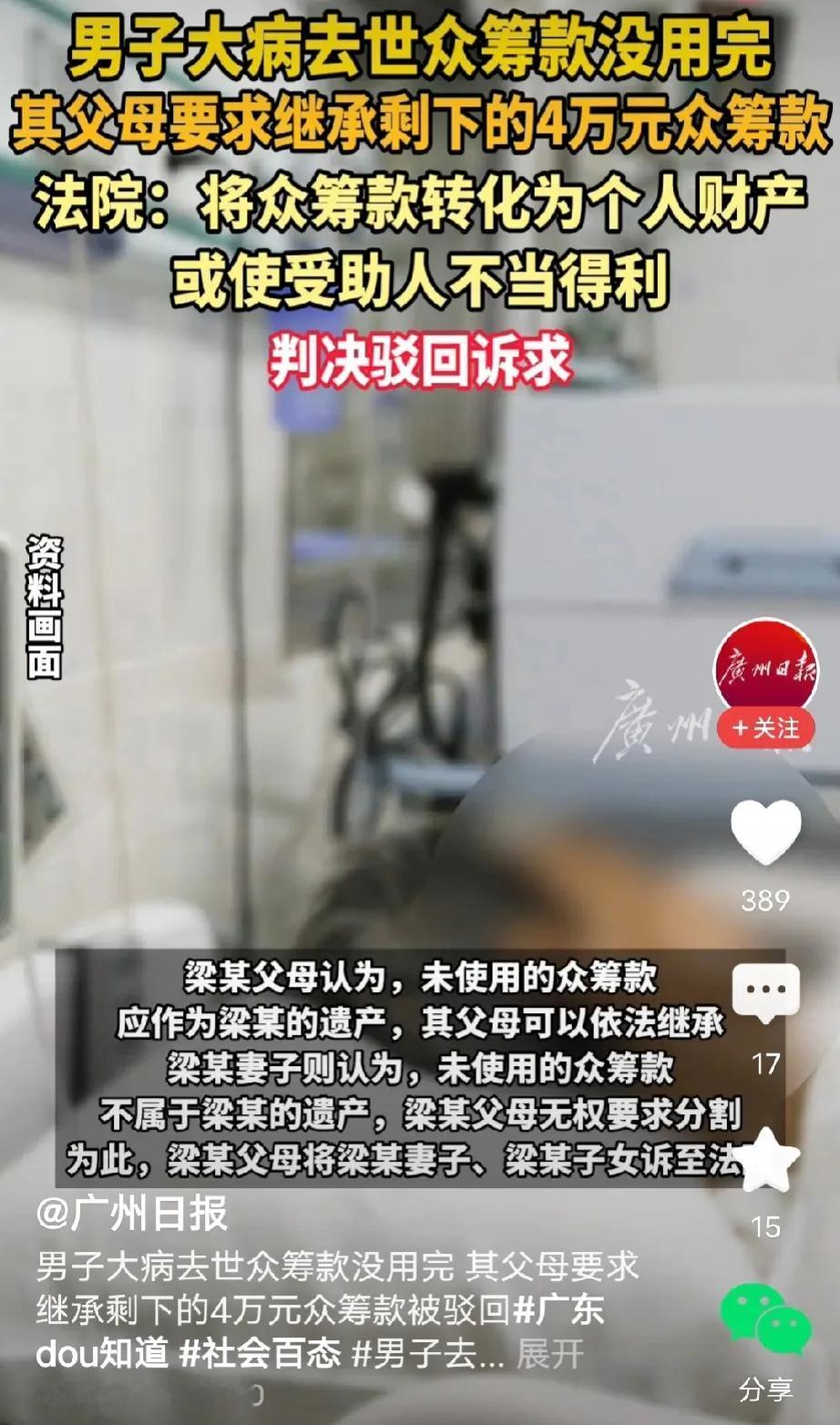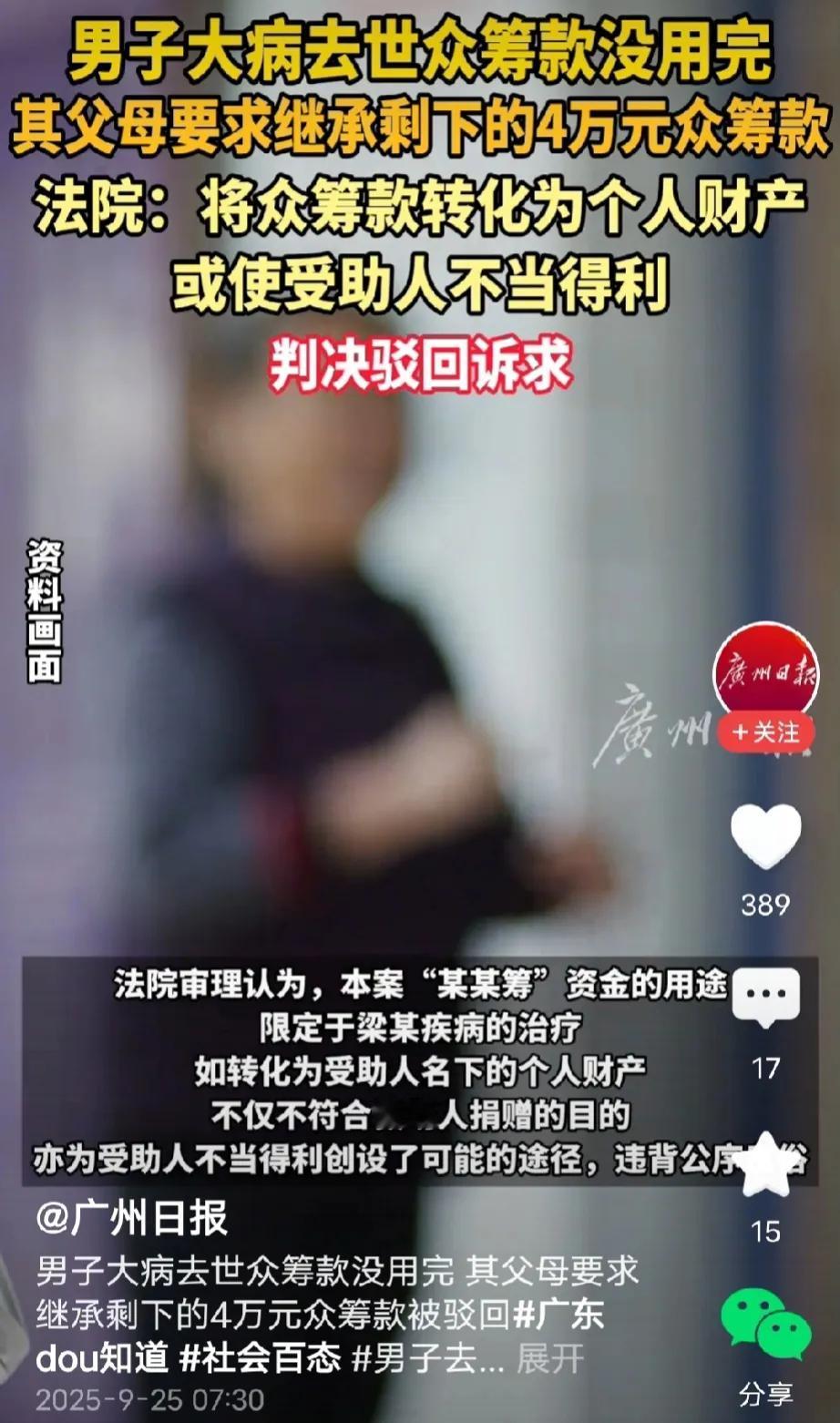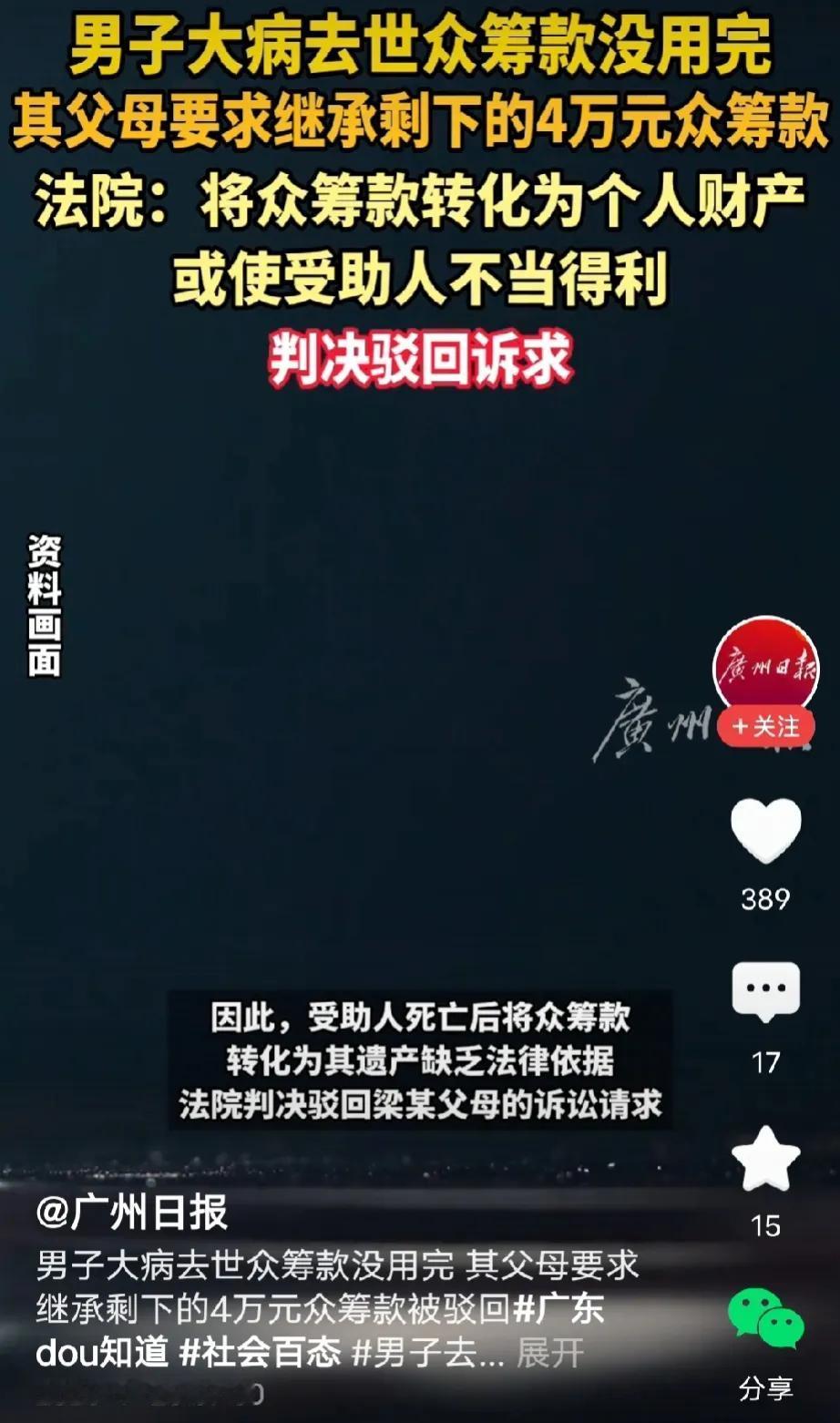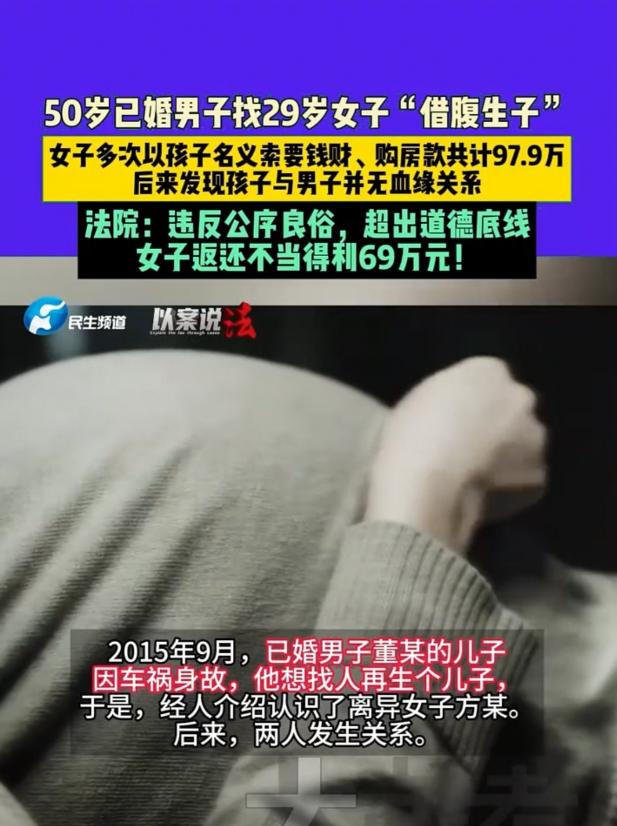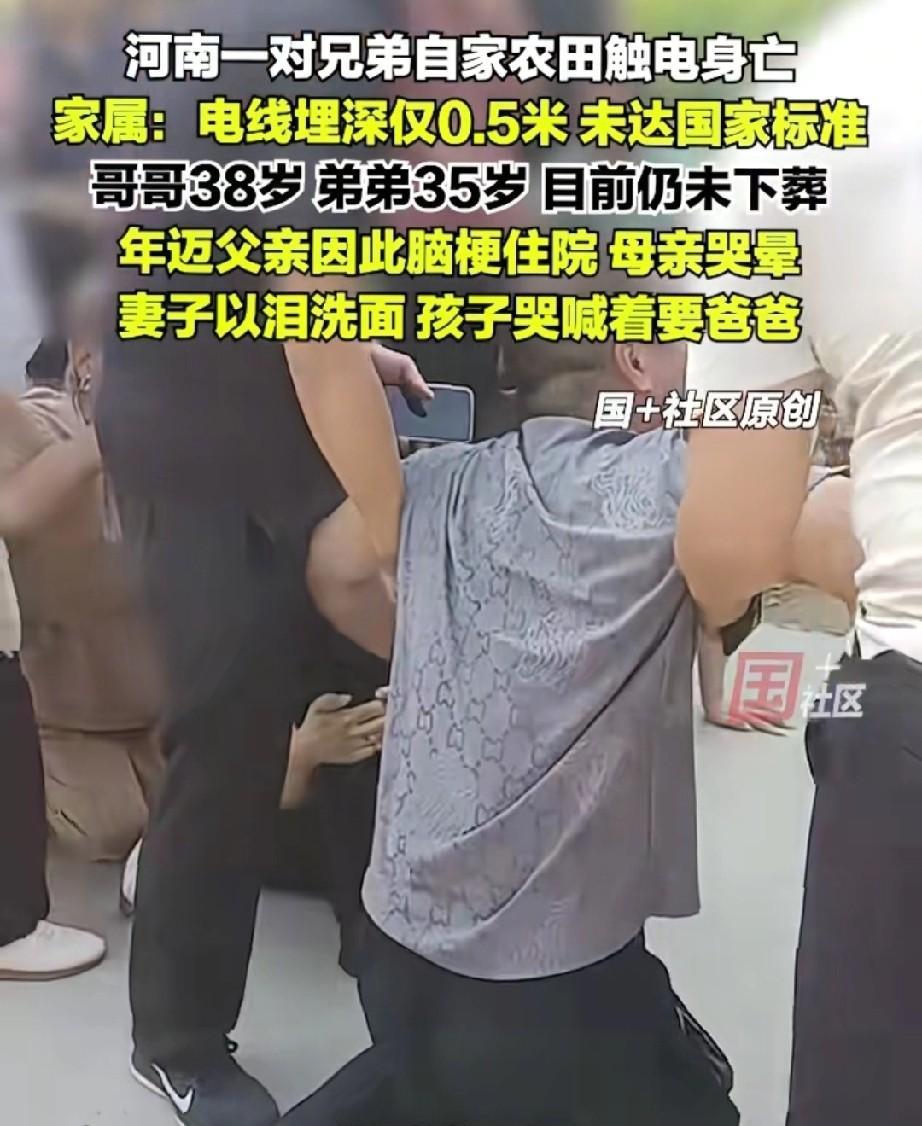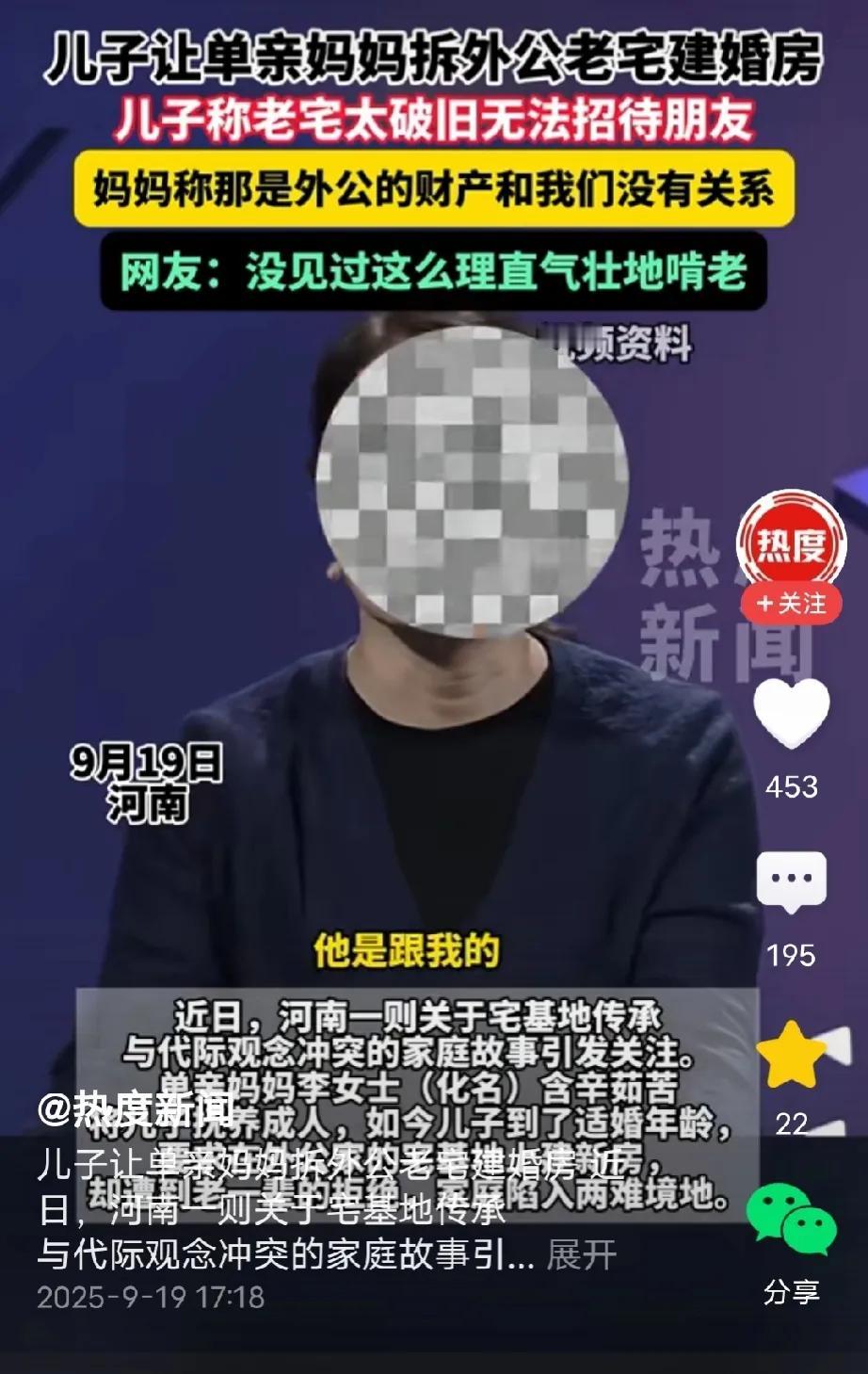广东德庆,男子不幸查出重病,家里条件不好,付不起高昂的医药费,于是他妻子发起了众筹,没想到,才没治疗多久男子突然病逝,众凑款还剩下4万元,男子父母认为这4万是男子的遗产,要求平分,男子妻子不同意,两老一气之下把儿媳和孙子孙女告上法庭,要求继承这4万元,法院判决亮了。 2021年的一天,梁某身体不舒服,之后到处去看医生,但是没有一点效果。 实在扛不住后,梁某到大医院检查,结果晴天霹雳,他竟然得了不治之症。 梁某看着检查单,愁得一夜之间白了头,他上有年迈的双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这一倒下他们怎么办? 面对高昂的医药费,梁某真想一走了之,给孩子们省点钱,可一想到他的孩子还那么小,他又舍不得,妻子也鼓励他,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哪怕砸锅卖铁都给他治。 看到妻子坚定的眼神,梁某咬牙坚持着,可每天面对高昂的费用还是让他们家陷入很难的境地。 他家里条件不好,存款也几乎用光了,迫不得已,梁某的妻子在网上发起了众筹。 朋友们知道梁先生的遭遇,个个自发帮他转发,帮他捐款,爱心人士很多,都希望梁先生顶过这一难关。 可病魔无情,梁先生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还是不舍离去了。 梁先生离世最伤心的是他的妻子、孩子,从此他们没了爱的依靠,没有坚强的顶梁柱。 梁先生的妻子怀着悲痛的心情给他办理好后事后,不久她处理众筹事宜。 她发现,众筹款还剩4万元,她也没多想,之前丈夫生病欠了不少债,她以为这一点钱,勉强能帮她抹点外债。 没想到,梁先生的父母知道众筹款还有4万元,他们竟然打起了这笔款项的主意。 梁先生的父母认为这也算是梁先生的一部分遗产,他们希望儿媳妇能把这些钱拿出来跟他们平分。 但梁先生妻子却说这部分钱不算遗产,不该拿出来分。 梁老多次跟儿媳沟通都没有效果,十分生气,于是把儿媳妇和孙子孙女告上法庭,要求平分这4万块钱。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某某筹”是公益平台,上面的众筹款是大家捐给特定病人治病的,不是送给病人当个人财产的。 这笔钱只能用在病人梁某的治疗上,如果变成梁某的个人财产,既违背了捐款人的初衷,还可能让他不当得利,不符合公序良俗。 有人说这两老太坏了,如果他们不去法院告,说不定人家不懂,儿媳妇还能用这点钱去还债,真是害人害己。 有网友说,众筹款如果用不完是会原路返回的,我之前也给别人众筹捐款,那个人把没用完的退了一部分钱回来。 那么,众筹款如果用不完到底怎么处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民法典》第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本案中梁某父母主张分割剩余4万元众筹款的核心依据是“遗产继承”,但该主张不符合此条规定。 遗产的核心要件是“个人合法财产”,即财产需明确归属于被继承人个人。 而案中众筹款是不特定多数爱心人士基于“帮助梁某治疗疾病”的特定目的捐赠的,并非无条件赠与梁某个人。 梁某及家人仅享有按用途使用款项的权利,并未取得该款项的完整所有权,其性质不属于梁某的个人财产。 因此,该笔剩余款项不符合遗产的法定构成要件,梁某父母的继承主张缺乏法律基础。 《民法典》第661条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网络众筹捐赠本质上属于“附义务的赠与”,捐赠人通过平台捐款时,已隐含“款项用于受助人治病”的义务约定。 本案中,“某某筹”平台明确众筹款用途限定于梁某的疾病治疗,这构成了赠与的核心义务。 梁某去世后,治疗义务已无法履行,剩余款项自然不能转化为受赠人的个人财产。 若支持梁某父母分割款项的诉求,不仅违背了捐赠人的附随义务,也使公益捐赠的特定目的落空,因此该主张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慈善法》第57条规定,慈善项目终止后捐赠财产有剩余的,按照募捐方案或者捐赠协议处理。 募捐方案未规定或者捐赠协议未约定的,慈善组织应当将剩余财产用于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项目,并向社会公开。 法院明确案中众筹款属于特殊网络慈善众筹范围,应参照《慈善法》处理 。 梁某去世导致“疾病治疗”这一慈善目的无法实现,众筹项目终止,剩余4万元需按法定规则处置。 由于本案未明确约定余款处理方式,该款项应用于与“大病救助”目的相同或相近的慈善项目,而非作为遗产分割。 最后,我想说,这场纠纷里,最让人心寒的不是众筹余款的归属争议,而是至亲在悲痛未消时为钱对簿公堂。 梁某父母将公益捐款视作遗产,既违背了捐赠人的善意,也无视了儿媳带着孩子还债的困境。 法院的判决守住了公益底线,可亲情的裂痕难弥。 众筹本是善意的传递,若被私利裹挟,伤的不仅是当事人,更是社会大众对公益的信任,实在不值。 关注@猫眼学法 品读案例故事,学习法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