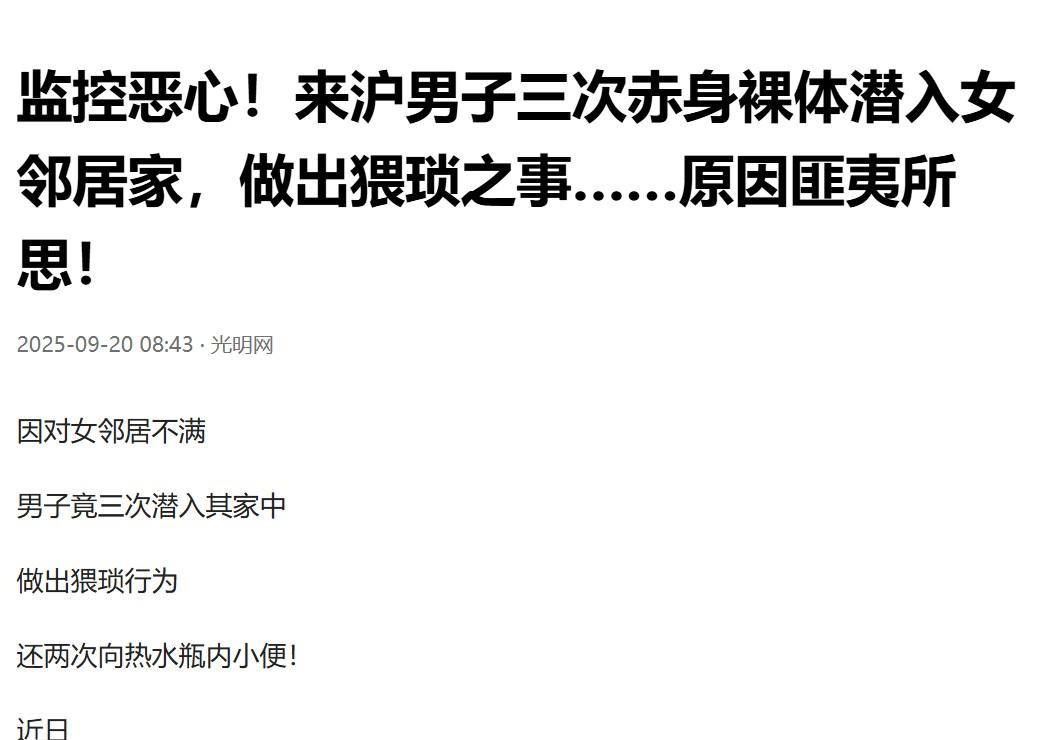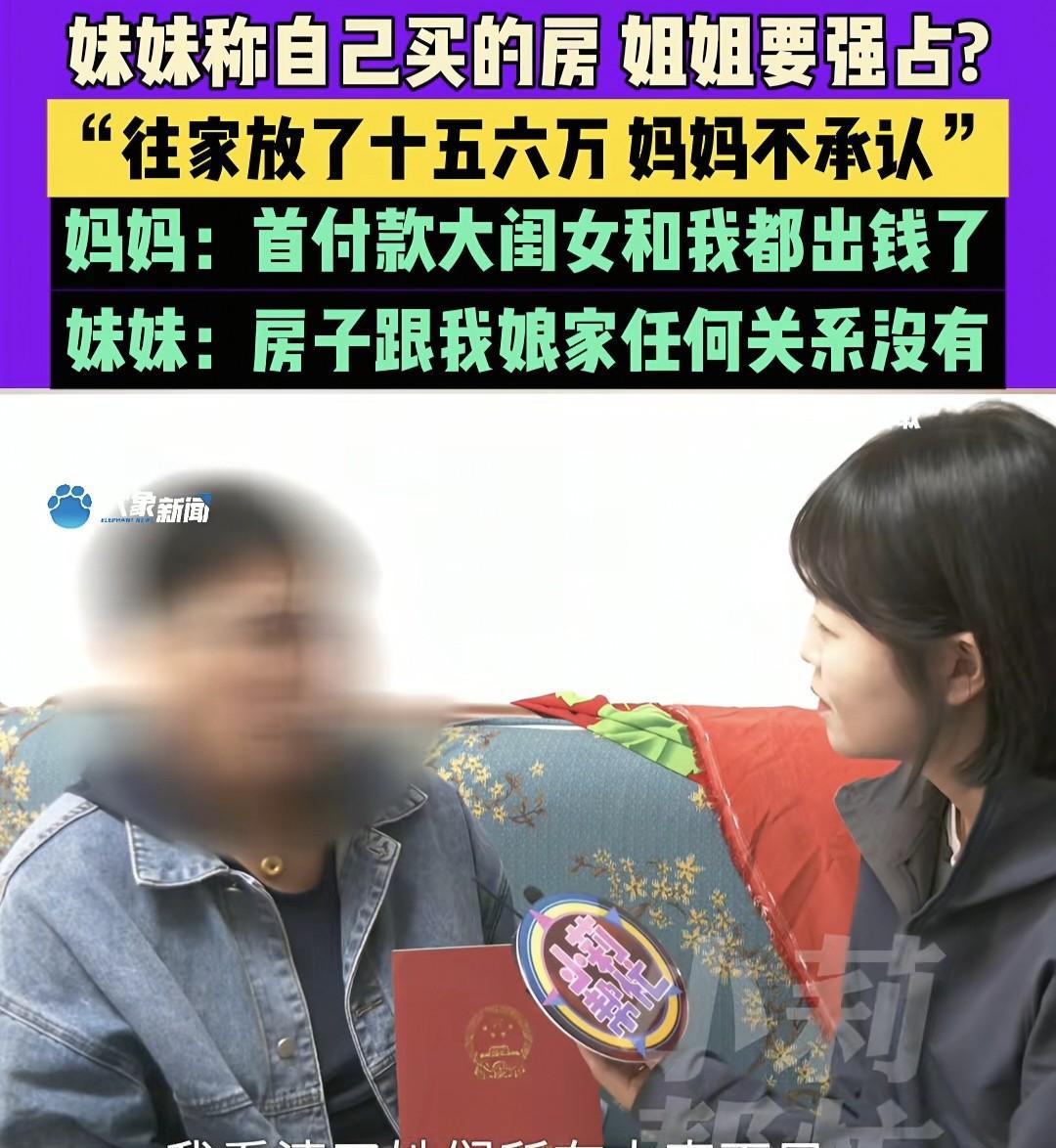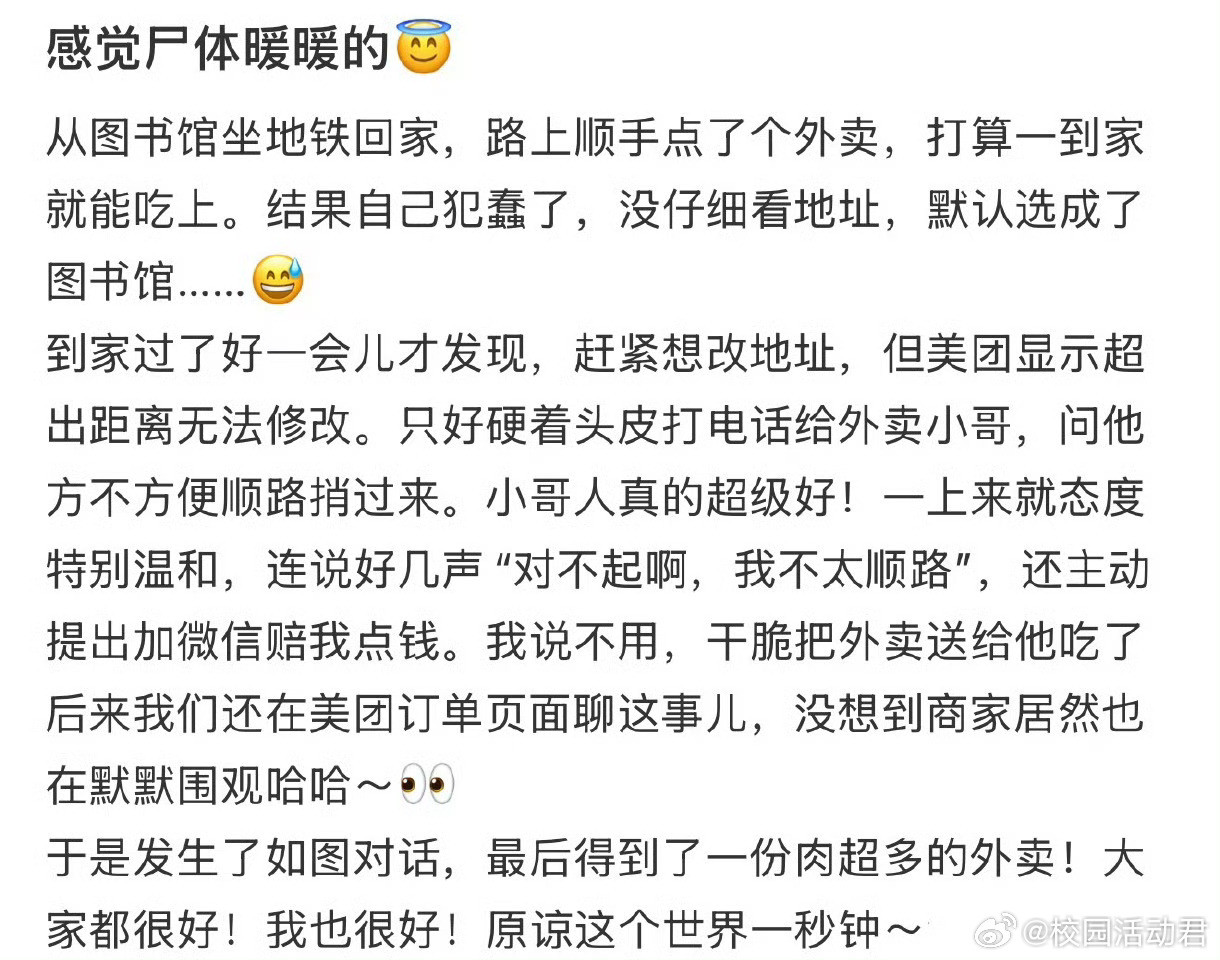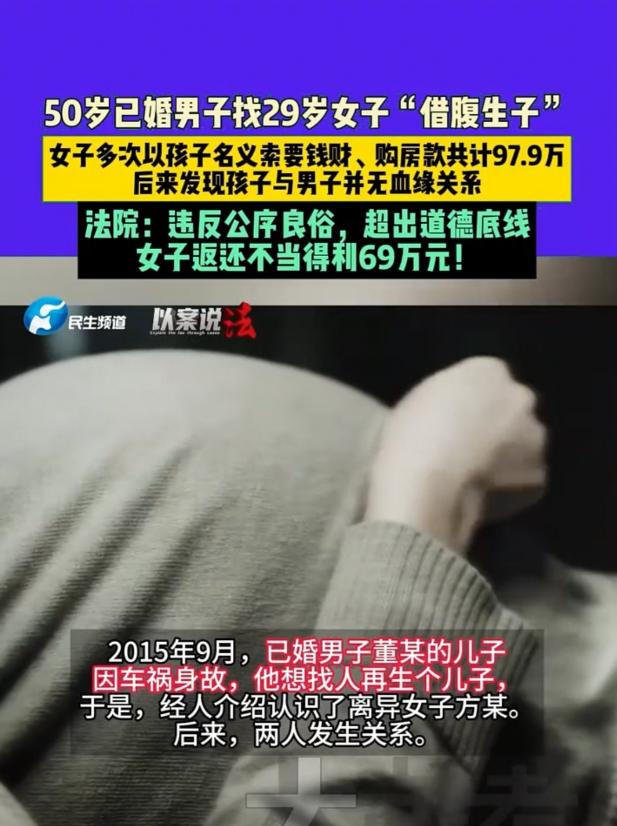郑州,男子请三名邻居去厂里干活,一名邻居从房顶上摔下来,下身没知觉,大小便也失禁。前期的医药费是这名男子支付的,可后续他家也很困难,就承诺会尽力找钱治疗那名邻居。但两个月了,对方电话不接,人也见不到。邻居家现在乱成了一锅粥,三个老人要赡养,孩子要读书,女儿考上大学没钱,还一直呆在家里。 周女士的丈夫两个月前去帮赵先生厂里干活,一天200元。去的时候还有另外两个人,大家其实都是邻居,平时有什么事,喊到了都不会推辞。 当天要做房顶上的修缮工作,周女士的丈夫稍微年轻一点,就承担了上房顶的活儿,其他两位邻居就在下面帮他递东西。 赵先生是喊他们来干活的,虽然是厂里的事,但只是临时修一下,不可能还签个合同或者协议之类的,就只反复叮嘱他们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几个人还笑嘻嘻地说:“你就放心吧,这些活我们都是熟能生巧的,不会出意外。” 赵先生这时就去忙自己的事了,毕竟他还有个厂子要管。所以叮嘱他们小心一点后,就转身离开去干别的了。 没过一会儿,有一位邻居急匆匆地跑到他办公室,说:“不好了!周女士的丈夫摔下来了,你赶紧去看看!” 赵先生刚端起来的茶杯都来不及喝一口,直接扔下就朝外面跑。来到房子下面,才发现周女士的丈夫躺在地上呻吟。 后来赶紧拨打120,把周女士的丈夫送到医院治疗。 传来的不好消息是,周女士的丈夫下半身没有知觉,大小便还失禁。 赵先生也很自责,心里想:千不该万不该,怎么就没在旁边一直盯着呢?明明反复说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他也赶紧去交了医药费,让医生竭尽全力救治周女士的丈夫。 前期治疗后,还需要后期康复,这得是个漫长的过程。赵先生也挺有担当,说:“你们只管治,医药费我们来垫付。” 有了这份承诺,周女士和她丈夫心里也稍微安稳了一点。虽然心里还是后悔,真不该那天去帮工,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可那毕竟是每天200元的收入啊。 后来,赵先生的经济也吃紧了,照这样垫付下去,他也没办法支撑,所以就跟周女士说了实情,但也表态会尽量多挣钱,来支付她丈夫的康复费用。 可说了这话后,赵先生他们就再也没出现过。周女士去他们家找,也没人;打电话,对方也不接。 眼看着要开学了,家里没钱,周女士的大女儿考上大学也没能去,一直呆在家里。 家里还有小的要读书、要生活费,还有三个老人要赡养,医院里还躺着她丈夫,需要康复费用。周女士急得焦头烂额。 可赵先生他们却当起了甩手掌柜。其实他们也确实是拿不出钱了,虽说有个厂子,但这几年的经营情况大家都清楚,可能也就只能维持正常生活,一旦发生点意外,真的是扛不住。 周女士找不到赵先生,就找来了媒体,希望赵先生能出面协调,谈谈赔偿的事——她现在太需要这笔钱来维持家里的生活,还有给丈夫做康复治疗了。 记者来到赵先生家,没见到人,就去找了当天一起去帮忙的另一个工人。 对方说这都是事实,当时周女士的丈夫在房顶上,他在下面递东西,也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就掉下来了。 记者问他当时签没签合同,对方说:“就干几天活,哪有什么合同啊,连协议都没有。一般在农村干活都这样,喊着去帮忙就去帮,最后结算钱就行,谁能想到中途会出这么麻烦的事。” 最后记者又找到村里的干部,对方表示村里有法律咨询的地方,可以帮周女士的丈夫申请法律援助。 事情已经过去两个月了,急需尽快解决。最后,记者没能联系上赵先生,就建议周女士走法律程序维权——只有这样,对方才可能坐下来和她协商这件事。 在这件事情里,没有签合同,只是临时喊来做工,结果出了意外,这就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到底该赵先生这个东家付钱,还是该临时工自己承担费用呢? 根据《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 在这个案例中,周女士的丈夫是赵先生临时喊来厂里干活的,双方形成了劳务关系。 赵先生作为接受劳务的一方,有责任为提供劳务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必要的安全指导。 虽然赵先生叮嘱过要小心,但在工人作业时,他并未在旁监督,在安全管理上存在一定疏忽,是有过错的。 周女士的丈夫作为提供劳务者,从事房顶修缮工作本身就有一定危险性,虽然他自称对这类活熟能生巧,但工作时不慎摔落,自身或许也存在操作不够谨慎等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过错。 所以按照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分析,双方可能都需要承担一定责任,具体的责任比例,可能要通过法律程序,由法院根据更多细节和证据来判定。 对于这件事,大家又是如何看待的呢?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素材来源于都市报道9月20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