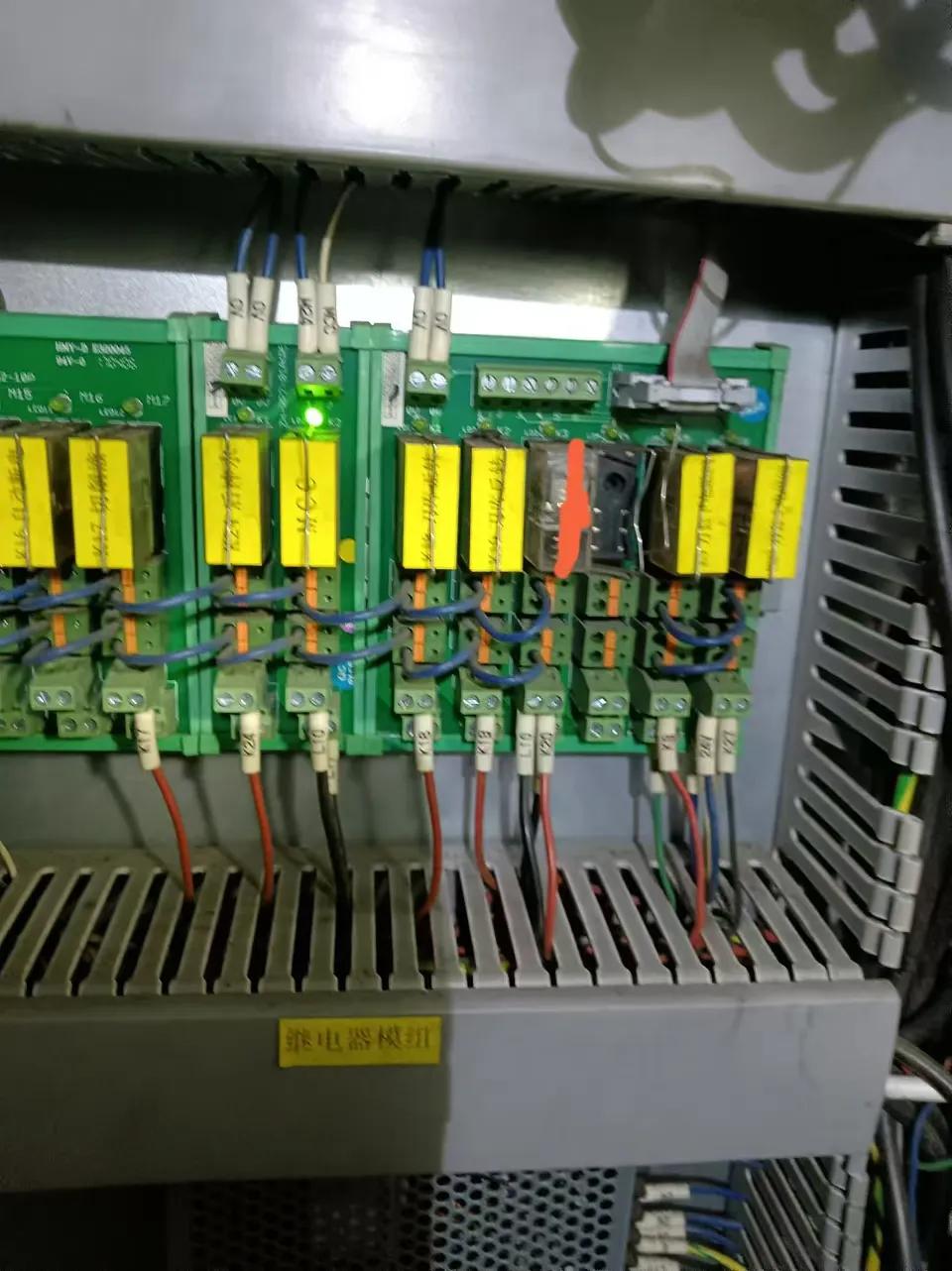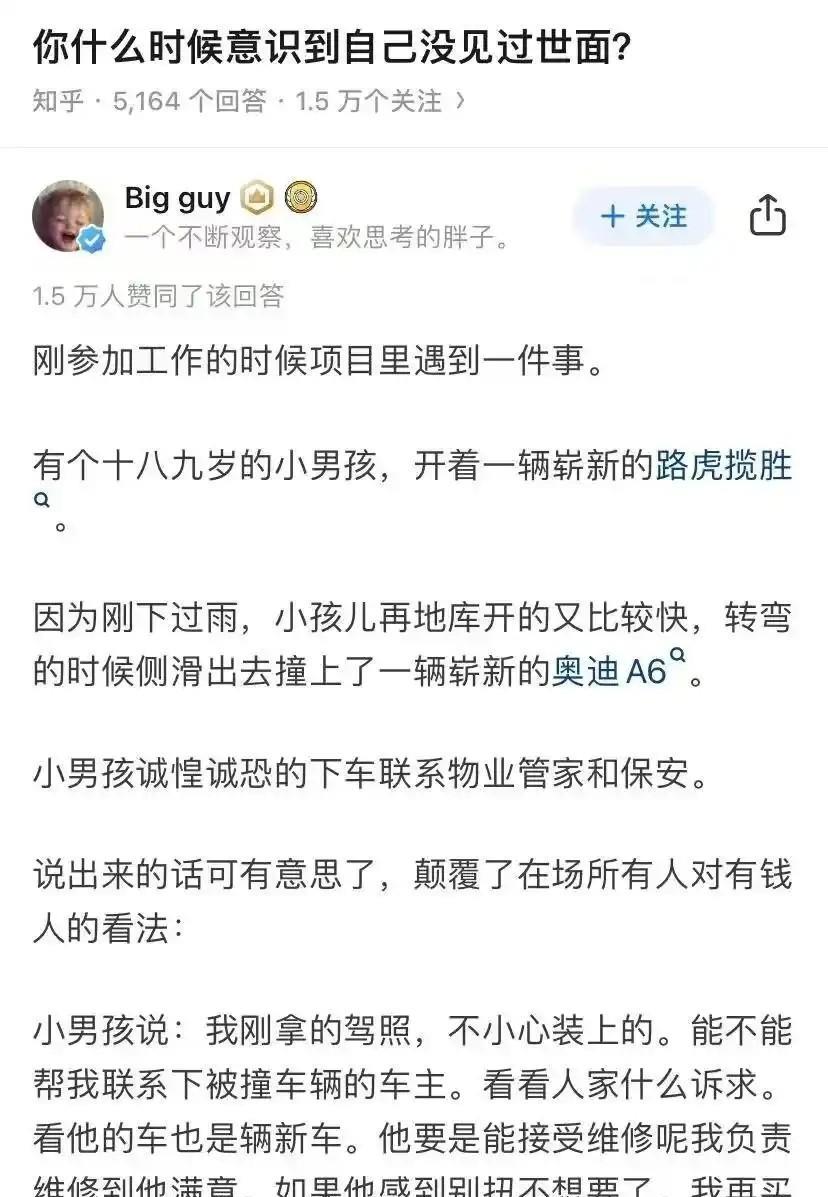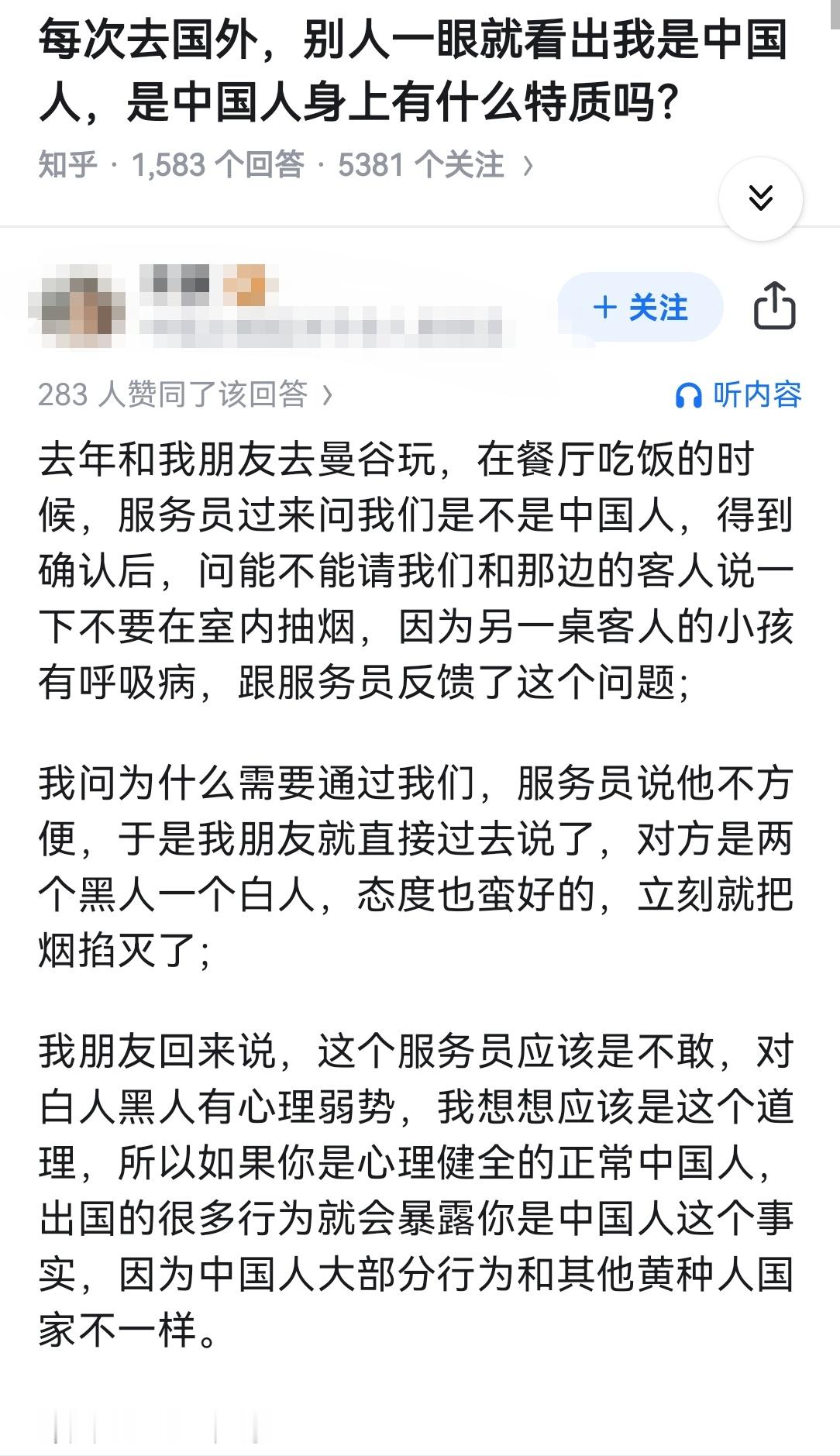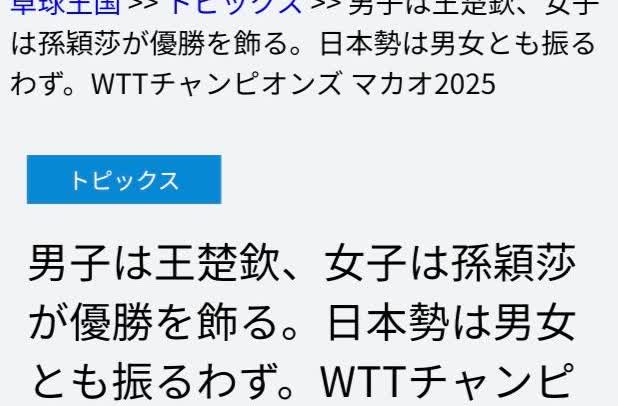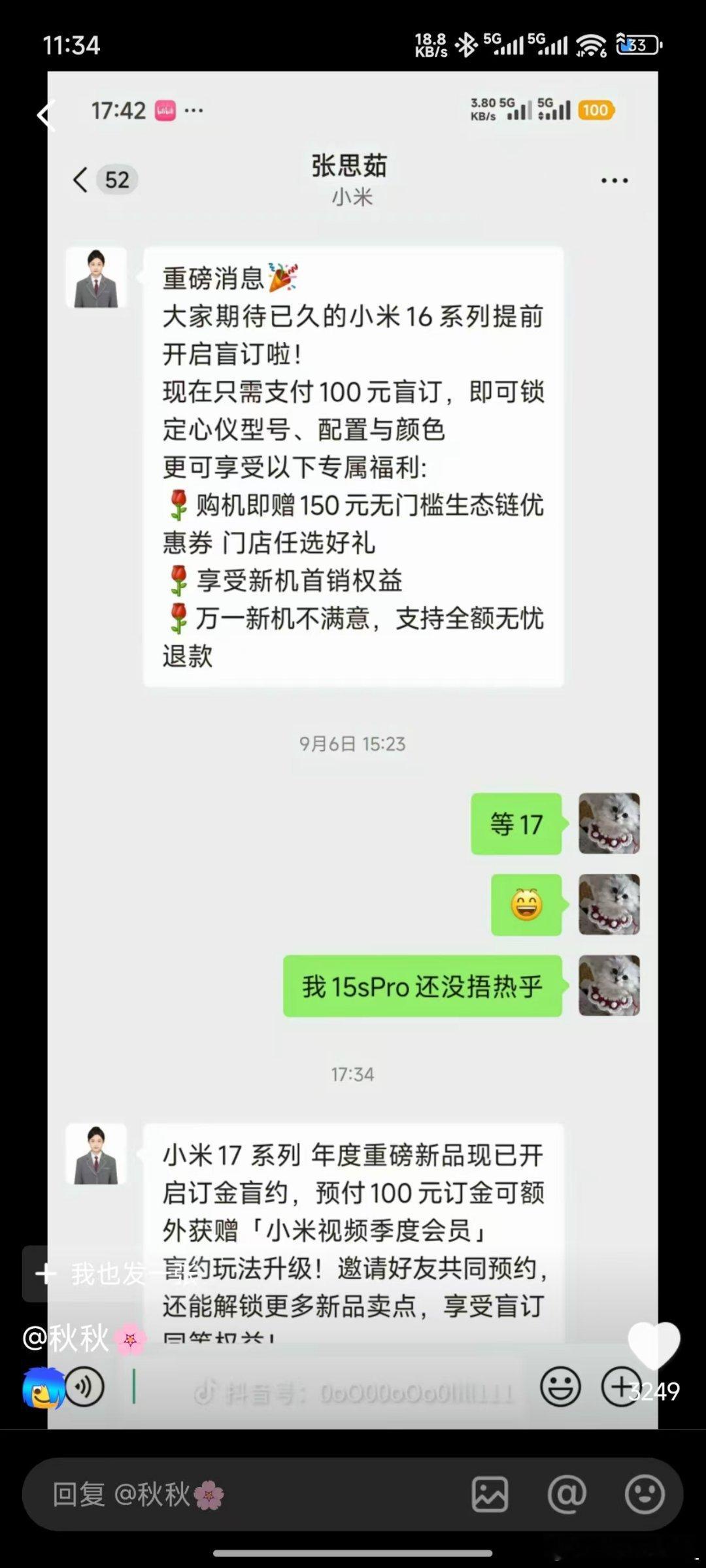1915年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日本的鬼工球竟然比中国多出五层,眼看就要夺得金奖,却在翁昭手中的一杯热水面前瞬间转变。 咱们平时聊老祖宗的手艺,总离不开剪纸、泥塑这些常见的,可还有一样宝贝,能让外国人拿在手里舍不得放下,那就是鬼工球。 别听这名字挺玄乎劲,其实就是用象牙一点点雕出来的套球,最绝的地方在于里面一层套一层,每层都能单独转,转起来还不卡壳,看着就跟有魔力似的。 明代有本专门讲古董的书,叫《格古要论》,书里就写过这鬼工球:“中直通一窍,内车数重,皆可转动”,意思就是球中间有个孔,里面雕了好几层,每层都能转。 要说这鬼工球的手艺,哪儿最厉害?那得数广州,不是说别的地方不行,是广州的气候太适合做这个了。 南方沿海不像北方那么干,空气里总有点湿气,象牙在这儿不容易裂。 雕这球得一层一层往里镂,要是象牙太干,雕个三四层就可能碎了,可在广州,匠人敢往十好几层里雕,就是因为气候给了底气。 而且广州的匠人不光敢雕,还雕得细,宋元时候就琢磨出了镂空通雕的法子,到了清代更是到了顶峰。 老辈人都传一句“苏州样,广州匠”,意思就是苏州人会设计好看的样子,但真要把这些样子做成精品,还得靠广州的匠人。 就连当年英国来中国的使团,里面有个叫约翰·巴罗的人,在他写的《中国行纪》里都夸广州的象牙雕刻,说“达到最完美程度,没有匹敌”。 当年外国人见多识广,能让他们这么夸,说明广州的鬼工球是真的走出了国门,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手艺的厉害。 真正让鬼工球“一战成名”的,是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那时候咱们中国刚推翻清朝没几年,就想借着这个博览会,让世界看看中国的好东西。 广州牙雕行里的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推选了联盛号的翁昭、梁雄几位老手艺人做的25层象牙球去参展。 这几位师傅平时就专做象牙球,做了几十年,这25层的球,光是分层就花了小半年,是当时广州牙雕的顶尖水平了。 可到了博览会现场,麻烦来了,日本也送了个象牙球,还是30层的。 俩球放在一块儿,看着都跟拳头大小差不多,表面都雕了缠枝莲,里面的透雕花纹也都是细活儿,评委们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左看右看都没主意。 按层数算吧,日本的多5层;可光看工艺精细度,俩球又差不太多,评委们甚至私下说“说不定日本的手艺更厉害”。 这时候翁昭师傅站出来了,他拿着咱们的25层球说: “各位评委,鬼工球不是看层数多就厉害,它的根儿在‘整根象牙雕出来’,不是用碎料拼的。要是拼的,别说30层,50层也能做出来,但那不是真手艺。” 接着他就提了个主意:“咱们把俩球放进沸水里煮煮,真的假的一煮就知道。” 评委们一听觉得有道理,就找了口大锅烧开水,把俩球都放了进去。 没一会儿,日本的那球就开始“散架”了,一层一层的壳往下掉,原来它是把象牙切成半球壳,先雕好每层的花纹,再用化学胶水粘起来,一遇热胶水就化了。 而咱们那25层球,在沸水里煮了半天,拿出来还是好好的,转起来照样灵活。 这一下,所有评委都服了,当场就把特等奖颁给了中国的鬼工球。 其实这鬼工球的手艺,难就难在“慢”和“细”。 第一步选料就不容易,象牙本来就少,还得挑大的、没裂纹的,有时候找一根合适的料,得等好几个月。 选好料之后,先得锯开象牙的中部,只留中间实心的部分,空心的地方没法雕,浪费就浪费了,手艺人行里有句话“宁丢十斤料,不做一件差活”。 接着是磨圆,用的是老木头做的转盘,匠人得一手扶着牙料,一手拿着细砂纸,慢慢磨。 磨的时候还得不停转着牙料看,哪儿有点扁就多磨两下,直到球变得圆溜溜的,拿在手里转着不晃,才算合格。 然后是钻孔,得对着球心钻,不然后面分层就歪了。 匠人没有仪器,全凭经验找中心点,钻的时候还得控制力气,太轻钻不透,太重又怕把球钻裂了,每个孔都得钻成外宽内窄的样子,方便后面伸刀进去。 最考验功夫的是“分层”,也就是把球里面镂成一层一层的。 匠人用的刀都是自己打的,刀头细得像针,刀杆还得弯点儿,才能伸进孔里横着切。 眼睛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全靠手上的感觉,耳朵还得听切割的声音,脆生生的声音就是切得对,要是声音发哑,说不定就快碰到别的层了。 最后每层都得雕成2毫米左右厚,最里面的小珠比绿豆还小,这么细的活儿,稍微手抖一下就废了,没有几十年的功夫,根本不敢碰这一步。 清代有个叫陈祖章的广州匠人,就是靠这手艺进了皇宫。 现在不一样了,大象都成了保护动物,2018年起咱们国家就不让用象牙做这个了。 但老手艺没断,匠人们改用象骨、骆驼骨接着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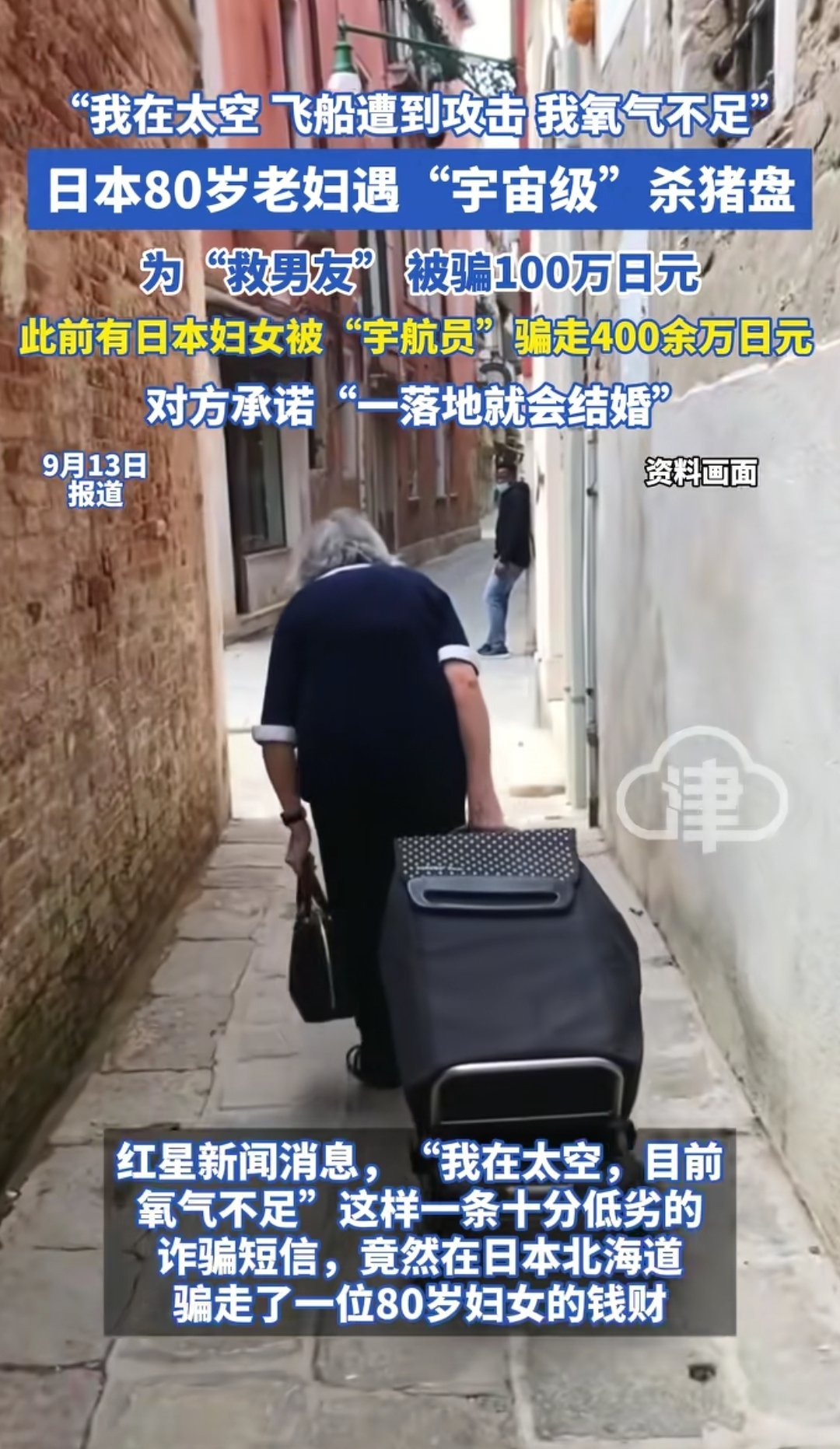
![自己脱不下来?[哭哭][哭哭][哭哭]](http://image.uczzd.cn/1713703912841471405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