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沈阳东华门原日本宪兵队本部地下发掘出的部分遗骨里,有一对拷在一起的男女尸骨。正值光复八十周年之际,向先烈致敬!这些尸骨现陈列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恒温展柜前,总有人驻足良久,玻璃罩里,两具遗骨手腕被锈迹斑斑的手铐锁在一起,骨缝间还嵌着当年的铁屑,女骨领口那片褪色的红布里,半粒干瘪的高粱米静静躺着。 这对遗骨能从地下走到展柜,能被后人叫出名字,背后藏着跨越25年的考证与铭记,更藏着一段不该被遗忘的抗联往事。 2022年,当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研究报告上写下“赵一楠、张兰”两个名字时,距离这对遗骨重见天日已过去25年。这份考证结果不是凭空而来; 工作人员比对了抗联十军的战史资料,翻查了1943年日军“冬季肃正”行动的档案,还找到了当年曾在宪兵队打杂、现已年过九旬的证人。 据证人回忆,1943年冬,曾有两名抗联战士被押进宪兵队,“男的腿被打断了,女的脖子上有绳子印,鬼子审了三天,没问出一句话”——这些细节,恰好与遗骨上的伤痕完全对应。 赵一楠是抗联十军的老战士,这支由汪雅臣组建的队伍,常年在五常、舒兰一带打游击,主要任务是破坏日军的铁路运输线,同时传递情报。 张兰则是他的交通员搭档,两人常乔装成商贩,把日军的兵力部署、物资动向写成密信,藏在柴火或粮食里送出。 1943年12月,他们在传递一份关于日军“进山清剿”的紧急情报时,因叛徒告密被捕。 档案记载,日军对两人使用了“老虎凳”“烙铁烫”等酷刑,赵一楠的左腿就是在刑讯中被钝器砸裂,张兰的肩胛骨则因被铁链反复拉扯而错位,后颈的勒痕,是鬼子用麻绳吊绑她时留下的。 即便如此,两人始终没吐露半个字,最后被日军活埋在宪兵队后院,埋之前,有人看见他们的手被铐在一起,“像故意拧了一下锁,怕分开”。 为什么他们的遗骨会出现在东华门?这得从这片土地的历史说起。1933年到1945年,这里是日本宪兵队本部,是当时沈阳最大的“政治犯”关押地。 据馆藏史料统计,这12年间,有两千多名抗联战士、地下党员、爱国学生被关押于此,绝大多数人没熬过酷刑,或被处决、或被活埋。 当年附近的居民回忆,夜里常能听见宪兵队里传出惨叫声,“有时候是鞭子抽的响,有时候是人的哭喊,听着心都揪紧”——而赵一楠和张兰,只是这两千多人中的两个缩影。 1997年冬天,东华门工地的发掘现场,是这段历史被唤醒的起点。当时工人们挖地基时,铁锹撞上硬物的闷响打破了寂静,扒开冻土后,那副手铐成了最震撼的发现。 文物局工作人员赶到后,用软毛刷清理遗骨时,陆续发现了更多关键线索:男骨左腿骨缝里的铁屑,经后来检测确认是日军刑具常用的铸铁材质; 女骨领口的红布,是当时东北农村常见的土布,里面包着的半粒高粱米,推测是她被捕前藏在身上的最后一点口粮; 男骨裤腰上的铜纽扣,上面模糊的“中”字,与东北军制服纽扣的制式完全一致,这些细节,一步步拼凑出他们的身份轮廓,也印证了日军的暴行。 如今,这对遗骨被安置在温度18-22℃、湿度50-60%的恒温恒湿展柜里,博物馆工作人员会定期对遗骨进行检测,防止骨头上的铁屑和痕迹因环境变化受损。 展柜旁,除了手铐的复原模型和标有当年刑讯室位置的老地图,还摆放着抗联十军的战史展板,上面详细介绍了赵一楠和张兰的事迹。 每到抗战纪念日,展柜前都会摆满观众送来的白菊和百合,烛光映着手铐上的锈迹,像是在替后人向先烈传递温暖。 博物馆还专门开展了“走近抗联先烈”研学活动,常有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站在展柜前,听讲解员讲述赵一楠和张兰传递情报、坚守气节的故事。 有次活动中,一个小学生指着那半粒高粱米问:“阿姨,他们是不是很饿啊?”讲解员回答:“他们饿,但更怕情报送不出去,怕战友们有危险。” 这样的对话,成了历史传承的一种方式。同时,博物馆官网至今还挂着征集线索的公告,希望能找到赵一楠、张兰的亲属或更多相关史料,让这段故事更完整。 馆外的东华门,如今是车水马龙的繁华地段,地铁口的人流、商场里的奶茶香、孩子们追逐的笑声,构成了和平年代的日常。 而馆内的展柜里,赵一楠和张兰的遗骨静静躺着,他们虽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但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和平,正以最鲜活的样子展现在眼前。 这对遗骨的现状,不仅是一段历史的陈列,更是一种提醒:那些为了民族独立牺牲的先烈,从未被遗忘,他们的精神,会随着每一次驻足、每一次讲述,永远传承下去。 信息来源: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日本侵华罪证展》《九一八历史陈列》

![因为一部扑了直接把所有武侠一杆子打死了[汗]](http://image.uczzd.cn/3534350195140232686.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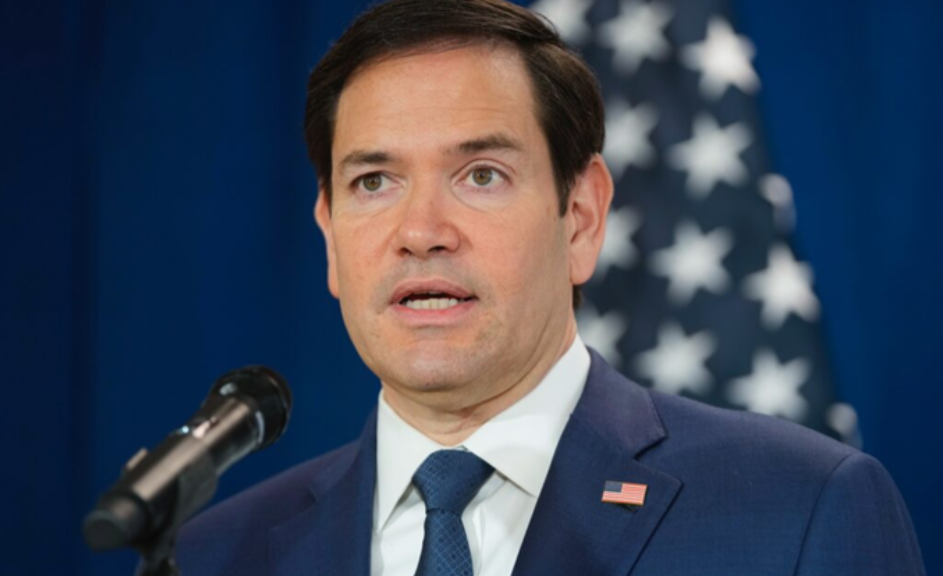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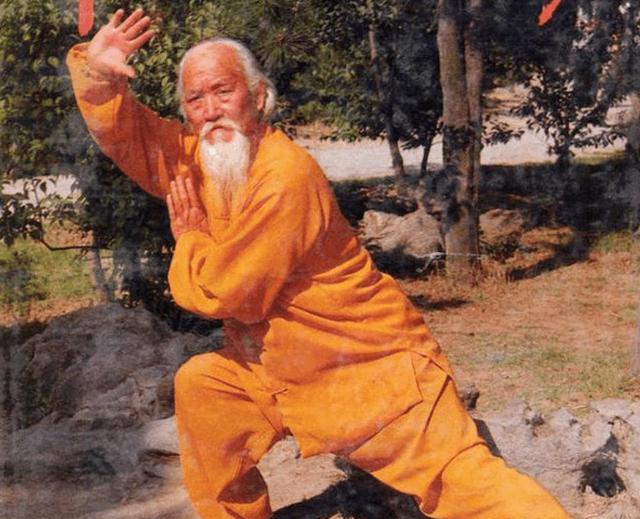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