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女子在某鱼平台看中一台标明“个人闲置”的iPhone15 Pro,与卖家约了线下见面交易,女子仔细查验了外观和序列号,确认无误后支付了6400元。不料,回家传输资料时,屏幕突然弹出“物主锁”界面无法使用。女子联系卖家要密码,却被告知手机实为公司配发的工作机,无法提供解锁所需的原始凭证,而苹果专卖店也证实无凭证则无法解锁。事后,女子要求退货,卖家先是拒绝,后又提出无法实现的退货条件并拖延。女子报警未果后,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法院却有不同观点。 据上海法治报9月2日报道,刘梅女士(化名)是一名精打细算的都市小白领,她时常在某鱼App上浏览,希望能淘到性价比高的二手商品。 2024年11月,她看到卖家潘哲先生(化名)发布的一则商品信息:一台几乎全新的iPnone15 pro,512G,白色,标题和描述都赫然写着“个人自用闲置,在保,几乎全新”。 刘梅恰好想入手一个苹果手机,而这个二手手机各方面正符合刘梅的需求,经过平台内的几轮沟通,双方最终以6400元的价格成交。 相较于动辄八千多的新机,这个价格颇具吸引力,潘哲强调手机是自用闲置,没有任何问题,并爽快地答应了刘梅线下验机的要求。 几天后,两人在地铁站见面,潘哲递上手机,刘梅仔细检查了外观,确认没有任何划痕,又进入设置查看了序列号和保修截止日期,一切似乎都完美无瑕。 出于对“个人闲置”描述的信任以及现场检查的顺利,刘梅通过某鱼平台完成了6400元的支付,双方钱货两清。 然而,当刘梅满心期待地开始将自己的资料导入新手机时,屏幕突然弹出一个她从未见过的“物主锁”界面提示,要求输入原所有者的Apple ID和密码才能激活使用。 她尝试了各种方法,都无法绕过这个界面,刚才还光鲜亮丽的手机,瞬间变成了一块昂贵的“板砖”。 刘梅立刻通过某鱼联系潘哲,语气焦急地询问原因,这时,潘哲才吞吞吐吐地告知实情,这部手机并非他个人购买,而是他所在公司配发的工作手机,他对这个“物主锁”的出现表示“完全不知情”,并称可能是公司远程激活的。 这个消息对刘梅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她要求退货退款,但潘哲起初以“交易已完成,当场验货无误”为由拒绝。 接下来的几天,情况更糟糕了,手机彻底无法开机,被完全锁死。 潘哲的态度有所松动,曾表示可以退货,但要求刘梅将手机“恢复原状”,但这个要求对于一块“砖头”来说显然无法实现。 之后便再无下文,所谓的“询问公司同事”也成了空头支票。 刘梅尝试找专卖店解决,但专卖店也明确必须提供该手机的原始购买发票、包装盒等凭证,证明机主身份。 刘梅再次联系潘哲索要凭证,对方则表示“无法提供”。 在采取报警等方式均无效果后,刘梅一纸诉状将潘哲告上了法院,要求返还货款6400元,赔偿三倍价款即19200元,并承担诉讼费等损失3000元。 法院会怎么判决呢? 《民法典》第617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据本法第五百八十二条至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请求承担违约责任。 法院指出,刘梅与潘哲之间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二手手机买卖合同,潘哲作为出卖人,负有保证其所出售的手机符合约定质量要求和正常使用功能的法定义务,这在法律上称为“瑕疵担保责任”。 潘哲在商品描述中明确标注“个人自用闲置”,这本身即构成了一种质量承诺,暗示该手机权属清晰、无任何使用障碍。 然而,事实是该手机是公司财产,并设有“物主锁”,这一锁定的存在,导致刘梅作为买受人根本无法正常使用手机,致使合同根本目的无法实现。 该瑕疵在交易当时通过常规验机无法立即发现,属于“隐蔽瑕疵”,无论潘哲对此锁是否“知情”,其已然构成违约。 法院认为,刘梅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货退款。 但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潘哲将“公司工作机”谎称为“个人自用闲置”,确实隐瞒了重要事实,这种行为具有欺骗性。 不过,“经营者”通常指以营利为目的、持续从事商品销售等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法院在审理中,特别审查了潘哲的交易记录,发现其并非专门从事出售二手手机人员,现有证据难以证明其具有明显的以盈利为目的的持续性对外出售商品的主观意图。 因此,潘哲在这次交易中,属于是一次性处置自有闲置物品的个人卖家,而非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 基于以上理由,法院未支持刘梅主张的三倍赔偿金。 最终,法院判决潘哲退还刘梅货款6400元,而刘梅将涉案手机返还给潘哲。 对此,您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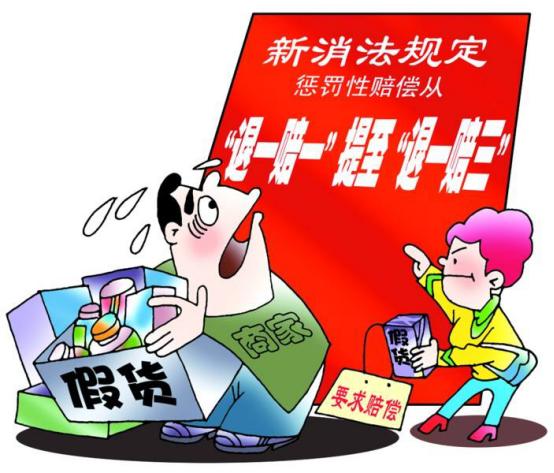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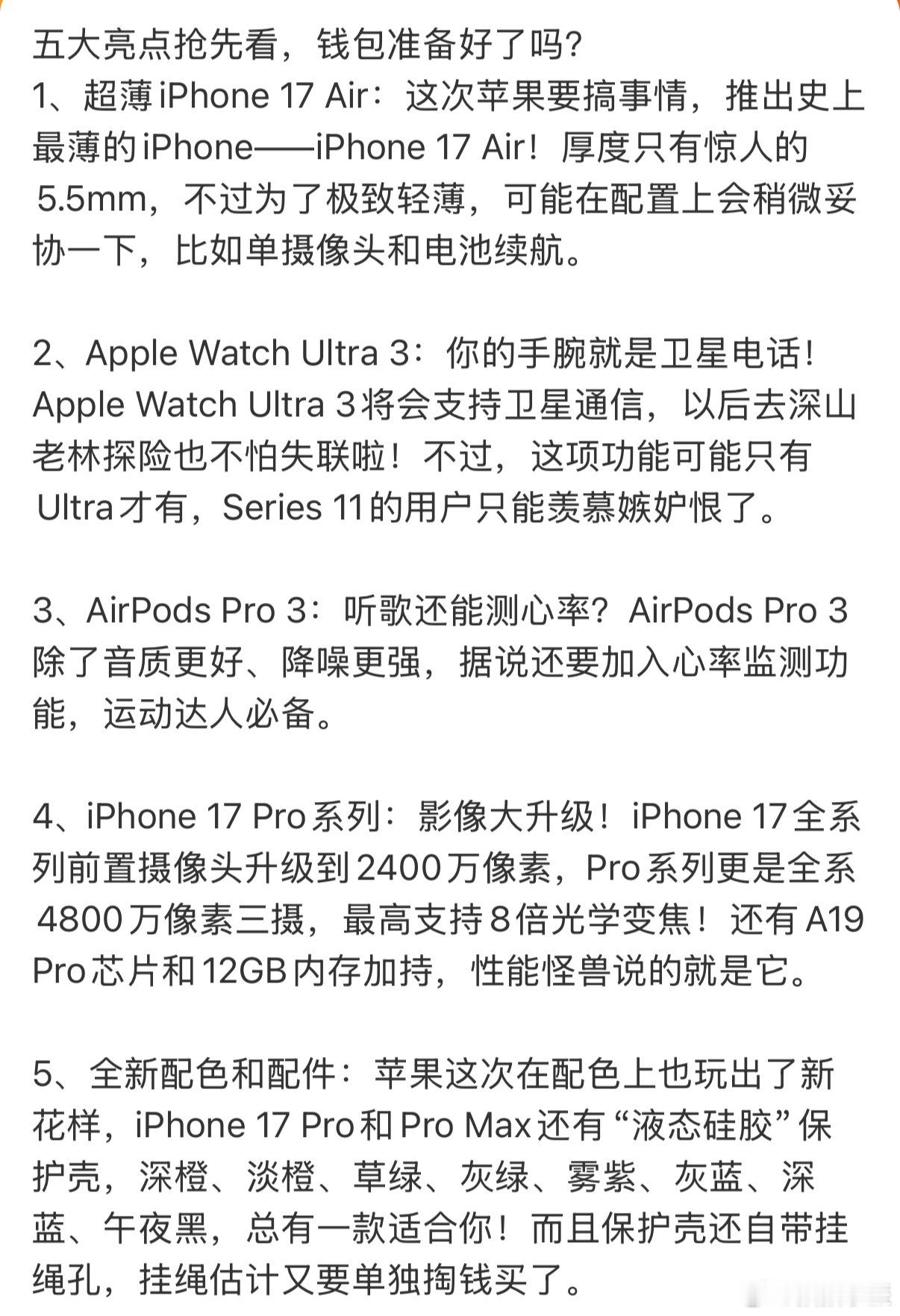

![有一说一,iPhone手机内部还真的就比安卓工整很多[并不简单]你们觉得呢?](http://image.uczzd.cn/5357295427848230667.jpg?id=0)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