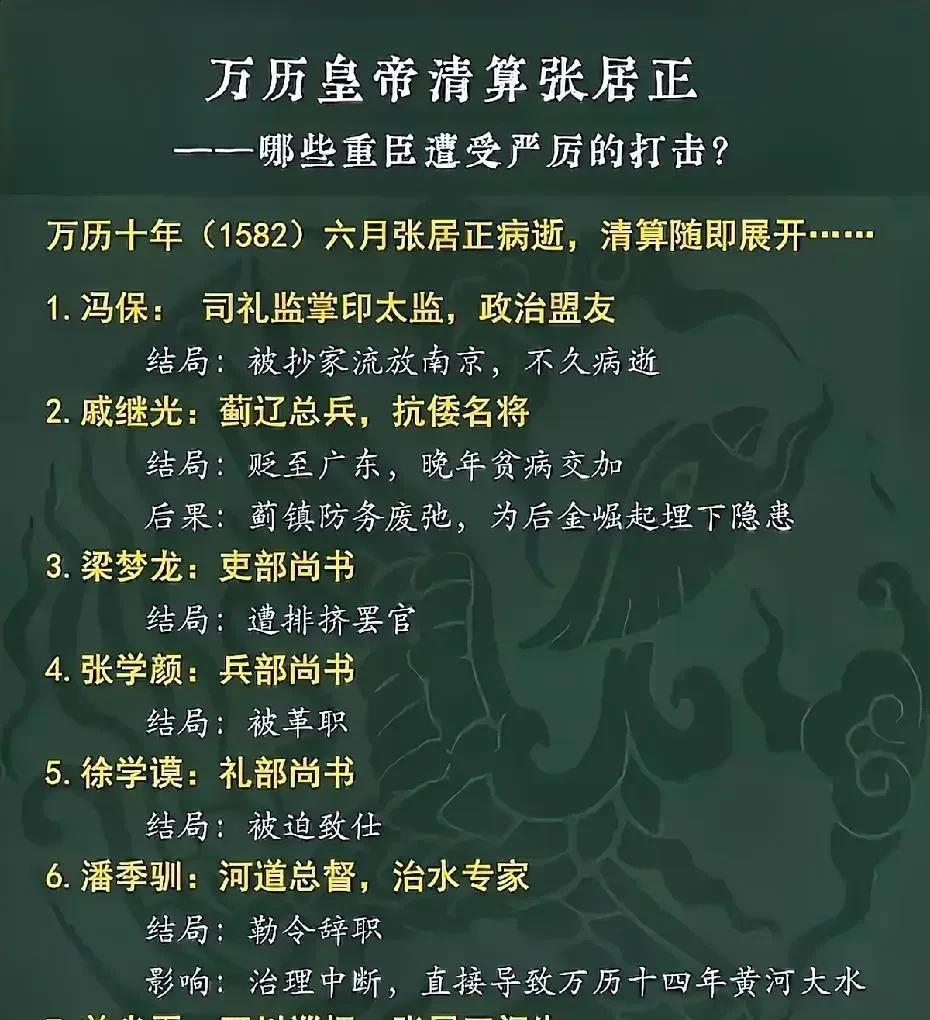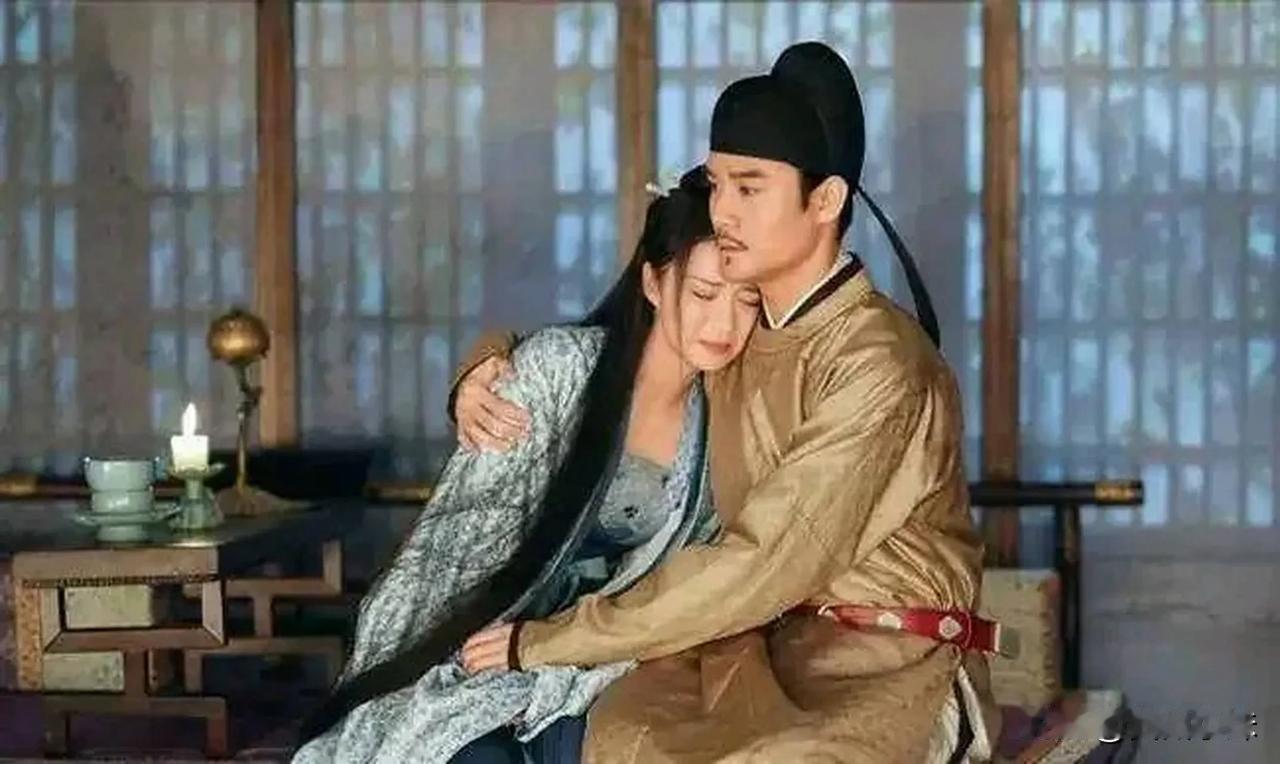万历元年,礼部六品主事童立本,不堪忍受家人饿死,竟然悬梁自尽了。礼部同僚闻讯仓皇赶去。推门而入,只见童立本悬于梁下,面容枯槁,身形瘦削如柴。
身上穿着旧官服,足下摆着家中唯一尚算完好的矮凳。屋内四壁萧然,桌案空空,唯墙角瓦罐中尚存些许豆豉。
这东西便宜,贫困人家经常用以充饥果腹,环顾家中,竟真无半粒米粮可寻。 而童立本的死亡现场成为大明官场的照妖镜。
当同僚撞开吱呀作响的木门时,那悬梁的官服下摆还沾着前日跪拜太庙时的香灰。
在书案上的绝命书墨迹未干,俸禄积欠四月,家里的粮食和钱啥也没有。
这句像刀子般扎进在场官员心里。
然而更触目惊心的是他枕下的账本。
上面记述着,腊月借西城米铺二钱银子,三分利滚到还不起。
妻子最后的银簪当了五十文,最近三天的伙食记录只有“豆豉半勺”。
然而这种赤贫在万历初年并非个例。
按《大明会典》记载,六品官年俸该有90石米,但经过“折色”剥削,七成俸禄被换成贬值百倍的宝钞和滞销胡椒,最终实际到手不足5石。
当巡城御史王家屏掀开童家米缸时,缸底裂缝里钻出的老鼠比这家人吃得还饱。
而在童立本死前一个月,曾抱着户部发放的苏木跑遍崇文门商铺。
这种曾价比黄金的香料,因张居正新政被大量抛售,太仓库积压的几万斤胡椒苏木冲抵俸禄,瞬间压垮市场。
当商人捏着鼻子告诉他,宫里流出来的货太多,这些连半价也卖不动了。
然而这场危机实为政治博弈的副产品。
那时候张居正推行实物折俸,表面是为清理财政积弊,实则剑指政敌高拱余党。
当吏部侍郎王希烈在童家灵堂哭喊“新政杀人”时,东厂番子已混在人群中泼洒火油。
第二天《邸报》记载“吊唁者焚纸引发火灾”,反对派领袖就此葬身火海。
童立本出殡那日,半城官员“突发风寒”告假。
只有礼部侍郎马自强脱下貂裘盖在尸体上说的那句“六品京官饿死,我辈岂能独活”。
这句话像寒风般卷过衙门,但是却没人敢接话。
这种死寂源于更深层的恐惧,当顺天府仵作剖开童立本的胃,里面未消化的豆渣让所有清官自危,更让贪官胆寒。
今日饿死的是不懂捞钱的傻子,明日屠刀会不会砍向“会来事”的自己?
在此刻官场潜规则在此刻暴露无遗。
京官们主要收入来自地方官的“冰敬”“炭敬”简单来说就是受贿,但童立本的书信匣里只有拒收礼金的记录。
他的同僚王显爵悲叹着前日还听他说“尚有豆豉可支应”,却无人知晓这位老实人已典当最后一件冬衣。
当万历皇帝得知死讯时,正为龙袍少绣朵云纹摔碎茶盏。
作为一个皇帝他手下的官员被活活饿死这只能证明这个皇帝的无能。
再一个官员都被饿死了,那百姓就更别提了。
但是司礼监冯保轻描淡写禀报“穷官想不开”,之后小皇帝转头就问新贡的暹罗胡椒能否多留几箱赏玩。
而在文渊阁,张居正朱笔划过《清丈田亩疏》,那些被豪强兼并的官田本可养活千万个童立本,此刻奏章却被“待议”的墨迹覆盖。
更荒诞的转折发生在停灵第七日。
京城米价突然回落,原来张居正召集商人高价回购胡椒,每斤补贴三钱银子。
当官员们喜笑颜开领钱时,此时童家院里的豆豉瓦罐被野猫撞翻,黑豆滚进雪泥,像凝固的血珠。
制度性腐朽终将清官逼成祭品。
童立本穿着官服赴死,用最体面的方式揭露最不堪的真相。
当折色制度让正一品月俸不足5石米,当潜规则成了官员生存必备技能,那件绣着云雁的官袍不过是华丽的裹尸布。
多年后黄山出土的万历粮价碑显示,当时1两银仅购米0.25石,也就是说童立本欠的四个月俸禄,折合白银不过6两,尚不够紫禁城半根蜡烛的开销。
童家废墟上后来建起关帝庙,香客们不知神龛下埋着半罐发霉的豆豉。
那黑黢黢的豆子像极了这个王朝的底色—,系统性腐败中,保持清白的代价是血肉,而制度杀人的证据,最终都成了老鼠的食粮。
一个诺大的皇朝,竟容不下一个只想靠俸禄养活家人的老实官员。
说来也是可笑,但是这也说明了那个时代,贪官腐败的严重,不管走到哪,只要有利可图都会有这帮人的出现,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