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新墙河阵地,机枪手曹锡发现离自己200公尺,一架重机枪歪在尸体旁,他爬过去架起重机枪,100多日军以为阵地无活人,蜂拥而来。 1939年9月23日清晨,新墙河南岸阵地陷入地动山摇的震动里。 日军八十多门重炮持续轰击三个小时,第十五集团军的战壕被掀翻在漫天尘土中。
守卫此处的第二师官兵多数被震得耳鼻冒血,只有机枪手曹锡从土堆里挣扎着爬出,用袖子抹掉枪管上的泥浆。
这个陕西汉子当时刚满二十九岁,参军不过两年光景。
此刻他守着全营最后一挺重机枪,眼见河面上密密麻麻的木筏逼近。
这批日军隶属第十一军精锐第六师团,半年前参与过南京暴行,刺刀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他们以为对岸守军尽灭,排成散兵线大步冲滩,皮靴踩碎岸边芦苇的声响清晰可辨。
当领头日军距阵地不足二十米时,曹锡突然拽动脚边麻绳。
提前埋设的十二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将滩头化作火海。
他随即架起轻机枪扫射,二十发弹匣点射五次,五名日军应声倒地。
其他幸存的战友也从各处开火,压得日军退到河堤后面。
日军官佐举着望远镜在木筏上跳脚,马上呼叫新轮炮火覆盖。
更致命的威胁来自空中滋滋作响的特种炮弹。
黄色烟雾在战壕蔓延时,朱班长嘶吼着让大伙拿湿布捂脸,可炮声掩盖了警告。
看着战友们抽搐着倒下,曹锡把衣襟撕碎浸在血水里捂住口鼻。
重机枪连最后四十余人,片刻间只剩曹锡和朱姓班长还在射击。
两挺轻机枪交叉火力暂时遏制了攻势,但日军很快发现这个火力点。
数枚掷弹筒炮弹尖啸着落下,朱班长被弹片削去半边脸颊时,手指还紧扣在扳机上。
曹锡拖着机枪撤到备用阵地,掀开盖在重机枪上的战友遗体。
马克沁水冷机枪开始嘶吼,打红枪管的子弹将日军整排撕裂。
此时营部传令兵猫腰奔来传达撤退令,却看到阵地上仅存的活人正在给卡壳的轻机枪换撞针。
二人交替掩护撤往二线阵地,半路遭遇日军斥候队。
传令兵中弹扑倒的瞬间,曹锡攀上被炸塌的祠堂阁楼,用单发点射解决三十三名追兵。
当他带着满身火硝味回到营部,营长亲自掀开帐门。
前线早传开这名机枪手单日歼敌五百的奇迹。
两天后师长赵公武召见他,将上等兵肩章换成中士衔,三十法币奖金足抵当时七百多斤猪肉钱。
这战报被印成号外传遍全国,连重庆统帅部都送来“民族英雄”匾额。
谁曾想新墙河战役竟成曹锡军旅生涯绝唱。
部队转进途中有人见他捂着腹部咳血,医务兵说那是连续被炮弹震伤的内伤。
也有士兵私下议论,说亲见他中弹栽进捞刀河。
更多人相信这个陕南汉子厌恶内战,拿奖金在汉中乡下买了三亩薄田。
军史档案里则记载着1940年部队重组时出现的花名册混乱,这解释却难抚平老百姓对英雄下落的追问。
陕西汉中的曹家老屋还留着民国二十八年的《扫荡报》,泛黄版面上登着授勋照片。
曹锡的弟弟八十岁时仍坐在门槛上念叨,说哥哥当年顶替自己参军时,把舍不得吃的半块麦饼塞进他怀里。
那时曹锡刚结束五年保安队生涯,本想着当兵能多挣军饷养家,没料到会在新墙河畔撞见南京刽子手部队。
他给家人最后一封家书里还夹着长沙城买的梨膏糖,信纸上歪扭的字迹写着“待杀尽倭寇当归”。
当时的第二师官兵都记得,这个沉默的新兵在训练场总比旁人晚走两时辰。
别人练百次据枪,他就练两百次。
马克沁重机枪分解组合蒙着眼能玩出花活,有老兵笑着说山西战场时这小子用捷克式打点射,五发子弹能掀三个鬼子天灵盖。
新墙河阵地布防前夜,他在煤油灯下给母亲纳的千层底缝了第二层牛皮底,说战壕碎石多省得磨破。
战后清理战场的老乡见过那挺马克沁机枪,护盾上密密麻麻的弹坑像筛子。
埋在河滩的手榴弹拉绳用的是裹腿带拧成麻花,炸出的弹坑最深能埋进半个人。
冈村宁次战后报告称遭遇“魔鬼阵地”,却没写明阻击者只有最后一人。
直到1983年修缮新墙河抗战遗址,施工队还挖出半块刻着“曹”字的铜水壶。
当地老人指着纪念馆里那挺斑驳的马克沁反复说:“那天枪声响到日头偏西,我们都当是关帝爷显灵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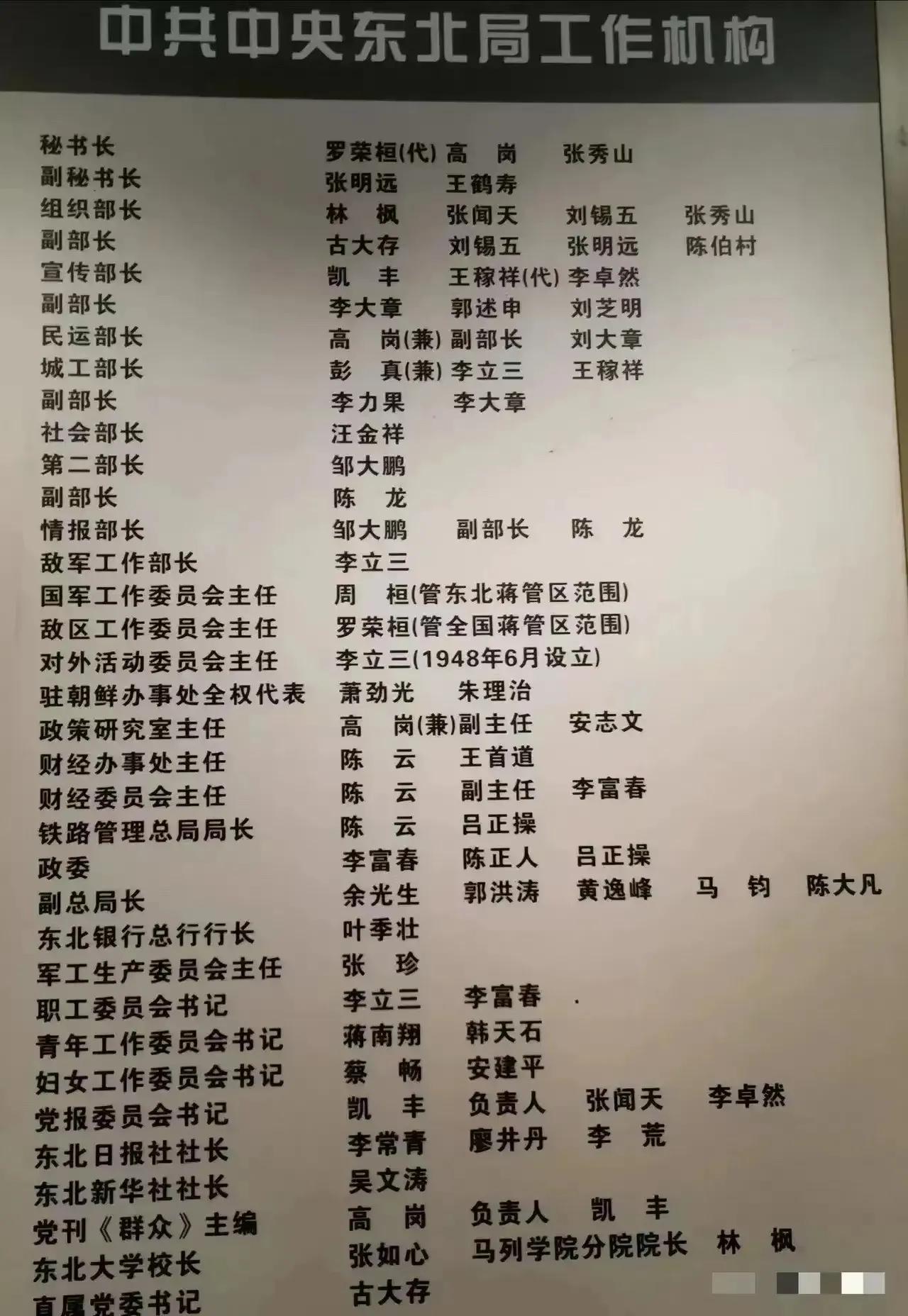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