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震怒,派曾国藩前去彻查。不料,曾国藩拖延数日才动身,审讯时也是一言不发。主审官员密报慈禧:要是再查大清就完了。 那年秋天,南京的贡院街还飘着桂花味,马新贻遇刺的总督府却已围上了三层兵丁。刺客张汶祥被按在地上时,手里还攥着沾血的短刀,仰头喊的那句“我为天下人除一恶贼”,让围观的百姓瞬间安静下来——两江总督是封疆大吏,在官署门口被人当众刺杀,这事儿在大清开国以来都没见过。 曾国藩接到谕旨时,正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府里翻《论语》。他盯着“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八个字看了半晌,让人把随行的行李收拾出来,却又吩咐:“先别装车,等我把这卷书看完。”幕僚们都知道,曾大人这是在琢磨——马新贻是慈禧亲手提拔的人,刚到两江就查了湘军旧部的粮饷账,如今突然遇刺,这背后的水太深了。 等曾国藩慢悠悠抵达南京时,距离案发已经过了二十天。主审的江宁将军魁玉早就熬红了眼,见了他就递上卷宗:“曾大人,张汶祥审了七次,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人所为,可他一个安徽来的小贩,怎么能混进总督府?怎么知道马大人那天要出门?” 曾国藩没接卷宗,先去了案发现场。总督府的青石板上,暗红色的血迹还没彻底洗净,被雨水浸成了暗褐色。他蹲下身,手指轻轻敲了敲石板边缘——那里有个新鲜的凹痕,像是被人用刀柄砸过。“案发当天,马大人是不是在这儿停过脚?”他忽然问旁边的差役。差役愣了愣,点头说:“是,马大人正要上轿,忽然想起忘了带公文,让随从回去取。” 第一次审讯时,所有人都盯着曾国藩。张汶祥被铁链锁着,脖子梗得笔直,见了曾国藩也不低头。魁玉刚要拍惊堂木,却被曾国藩用眼神拦住。他就坐在那里,端着茶杯慢慢喝,听魁玉问案情,听张汶祥翻来覆去说那套“私仇杀人”的供词,自始至终没开口。 散堂后,魁玉忍不住问:“曾大人怎么不发问?”曾国藩指着堂外的老槐树:“你看那树,风吹过来就动,雨打下来就摇,可根在土里,你不挖开,怎么知道它扎了多深?”魁玉这才明白,曾大人是在看——看张汶祥说话时手指是不是在抖,看他提到“湘军”二字时眼神有没有飘,看旁边记录的书吏握笔的力度够不够稳。 到了第七次审讯,张汶祥忽然改了口,说自己曾在湘军里当过兵,马新贻当年镇压捻军时,杀过他的同乡。这话刚说完,曾国藩手里的茶杯“当啷”一声磕在案上。他抬眼看向张汶祥,那眼神像结了冰的湖面:“你在湘军哪个营?营官是谁?”张汶祥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夜里,魁玉揣着密信去见曾国藩。信是从湘军旧部的商号里搜出来的,上面没写名字,只画了个十字——那是湘军当年约定的记号,意思是“此人该除”。“曾大人,再查下去,就得动湘军了。”魁玉的声音发颤,“江南的厘金局、盐运司,多少人是湘军出来的?真要把他们逼急了,南京城怕是要乱。” 曾国藩望着窗外的月光,半天没说话。他比谁都清楚,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裁军时留了太多隐患——旧部们拿着遣散费在江南买田开店,马新贻一来就严查偷税漏税,还抓了几个倒卖军械的湘军将领,这哪是查案,分明是在动别人的饭碗。 没过几天,曾国藩给慈禧递了份奏折。上面写着“张汶祥因私仇刺杀总督,依律凌迟处死”,没提湘军,没说幕后主使,连张汶祥供词里的破绽都没提。魁玉看着奏折,忽然懂了——曾大人这是在保大清的体面。两江是赋税重地,湘军旧部盘根错节,真要撕开了口子,不光江南要乱,朝堂上的湘军大佬们怕是也要反,到时候谁来收拾残局? 慈禧收到奏折时,正在给光绪缝小棉袄。她把奏折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叹口气,在上面批了个“准”字。旁边的李莲英想说话,被她瞪了回去:“曾国藩老了,可他心里有数。这案子再查,查出来的就不是刺客,是人心了。” 后来张汶祥被处决那天,南京城的百姓挤着去看。有人说他是义士,有人说他是棋子,可没人知道,他被押走前,曾国藩让人给了他一碗酒。“你若说实话,我保你家人平安。”曾国藩当时这样说。张汶祥喝完酒,只说了句“大人心里明白就好”。 这案子就这么结了,成了大清的一桩悬案。可江南的商人们都发现,自那以后,湘军旧部的商号规矩了不少,马新贻没查完的账,没人敢再糊弄。曾国藩在南京待了半年,没再提案子的事,只忙着修河堤、办书局,临走时给魁玉留了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但也不能让鱼把水搅浑了。” 其实曾国藩心里跟明镜似的——有些案子查到底,不是为了真相,是为了让活着的人知道边界。他拖延动身,是在给各方留缓冲的时间;审讯时沉默,是在观察谁在怕、谁在等;最后草草结案,是在告诉所有人:可以停手了,再闹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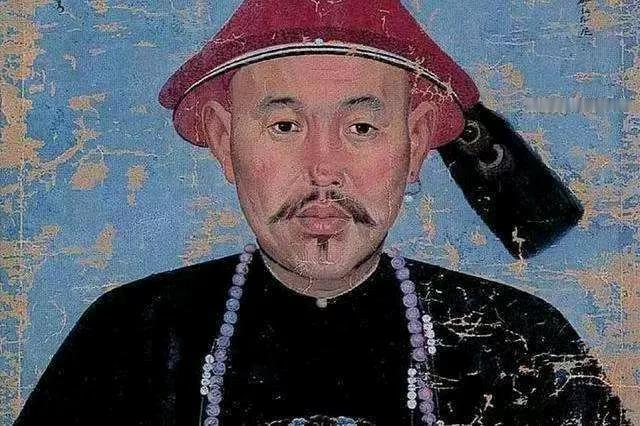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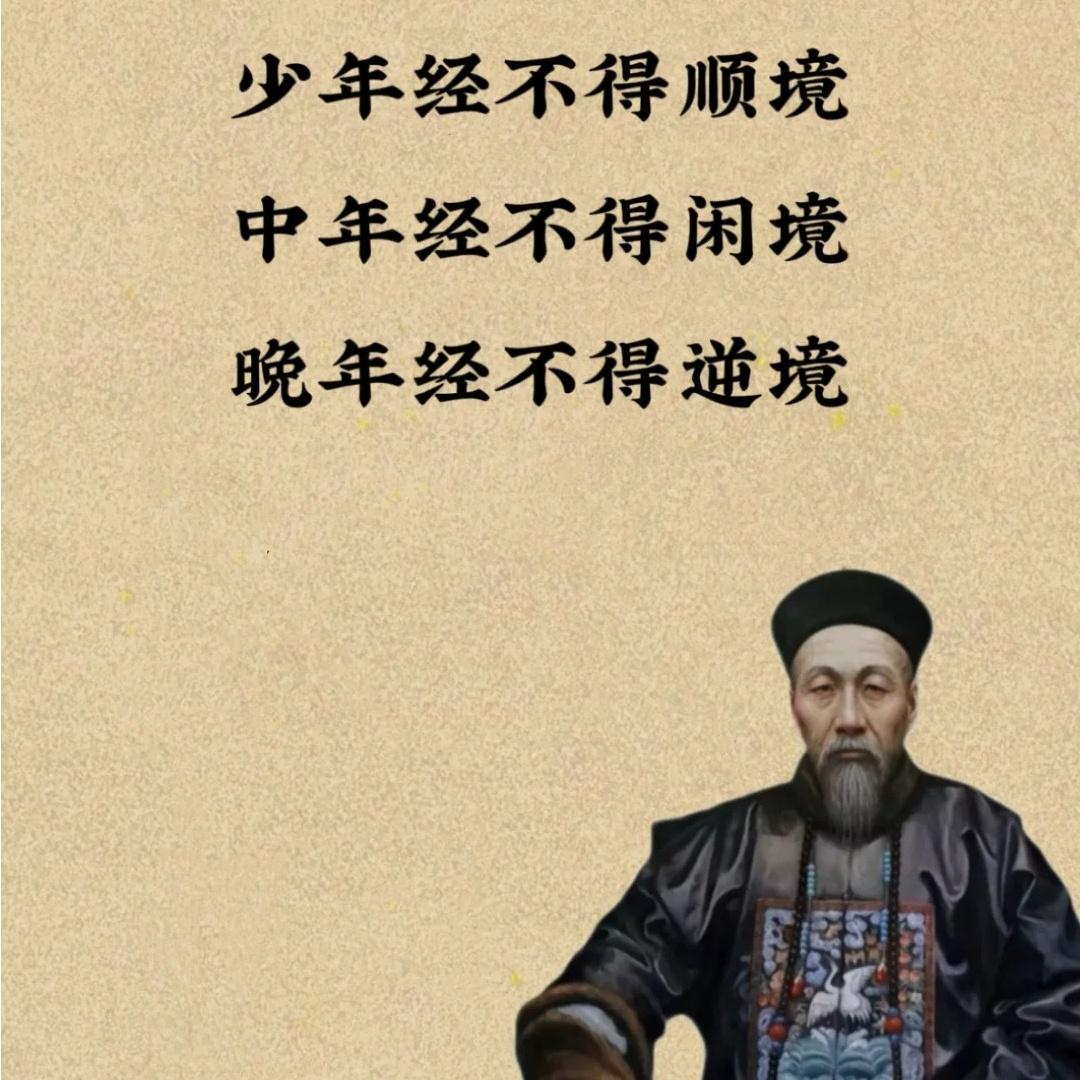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