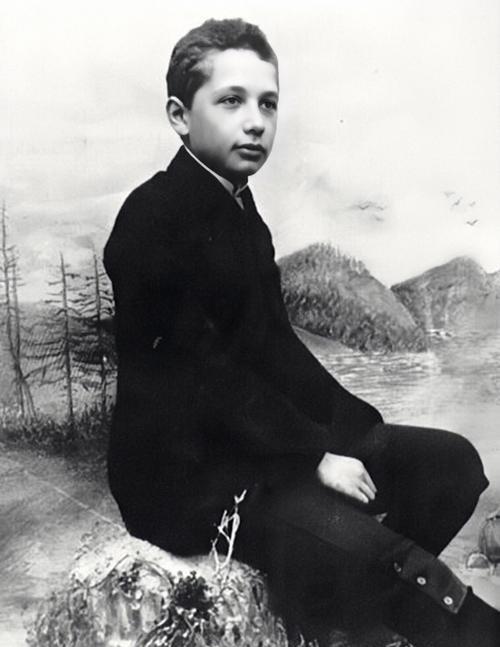婴儿是感觉不到疼的!”1985年,美国在给一婴儿做开胸手术时,全程没用麻药,面对孩子母亲的质疑,医生的回答,让人目瞪口呆。看着保温箱里浑身插满管子、呼吸微弱的儿子,吉尔的心像被揪成一团。她强忍着产后的虚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下名字,唯一的期盼就是医生能让儿子平安挺过难关。可术前沟通时,一个细节让她瞬间僵住——当她询问医生“手术会用哪种麻药,会不会对孩子大脑有影响”时,主刀医生理查德却轻描淡写地回答:“不用准备麻药,婴儿是感觉不到疼的,麻药反而会增加手术风险。”这句话让吉尔如遭雷击。她虽不是医学专业人士,却清晰记得自己每次抽血时的疼痛感,刚出生的婴儿难道真的对疼痛毫无感知?她试图反驳,可理查德医生却以“这是医学界共识”为由,拒绝了她的质疑。更让她无力的是,其他医护人员也纷纷附和,说“婴儿神经系统没发育完全,疼痛信号传不到大脑”“过去几十年的婴儿手术都是这么做的”。在“救子心切”与“医学权威”的拉扯中,吉尔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儿子被推进手术室,而她不知道的是,这场没有麻药的开胸手术,会成为母子俩一生难以磨灭的创伤。手术进行了整整5个小时。当吉尔再次见到杰弗里时,孩子浑身裹着纱布,小小的身体还在不受控制地颤抖,哭声微弱得像小猫叫,连吸吮母乳的力气都没有。护士解释说“这是术后正常反应”,可吉尔却注意到,每当医护人员触碰杰弗里的手术伤口附近时,孩子都会突然绷紧身体,哭声变得尖锐,眼神里满是她从未见过的恐惧。术后几天,吉尔开始疯狂查阅医学资料,试图找到“婴儿是否能感知疼痛”的答案。她泡在医院图书馆,翻阅了上百篇论文,发现当时美国医学界确实普遍存在一种错误认知:婴儿的大脑皮层和神经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无法像成人一样感知疼痛,甚至有权威医学期刊在1980年发表论文称“新生儿对疼痛的反应只是无意识的肌肉抽搐,而非真正的疼痛感知”。可吉尔在资料里也发现了不同的声音。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曾在1983年发表研究,通过监测婴儿抽血时的心率、血压和皮质醇水平(压力激素)发现,婴儿面对疼痛刺激时,生理指标的波动幅度与成人相当,只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只能通过哭闹、肢体僵硬等方式传递痛苦。杰弗里的术后恢复远比预期艰难。他不仅反复出现肺部感染,还变得极度抗拒与人接触——只要有人靠近保温箱,他就会立刻哭闹不止,即使是吉尔喂奶,也必须等他完全平静后才能靠近。这种“创伤后应激反应”,让吉尔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她联系了当地的母婴权益组织,将杰弗里的遭遇公之于众,很快引发了舆论哗然。越来越多有过类似经历的父母站出来发声:有人说自己孩子做疝气手术时,没打麻药,术后连续三天哭闹不止;有人说孩子割包皮时,医生只用了局部麻醉,孩子的哭声差点震破产房;还有儿科护士匿名透露,每次给婴儿做穿刺、缝合等有创操作时,看到孩子痛苦的反应,自己都心如刀绞,可医生却总说“别心软,他们不懂疼”。舆论压力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不得不成立专项调查组,重新评估婴儿疼痛感知与手术麻醉的关系。调查组调取了1980-1985年间全美婴儿手术的医疗记录,发现超过80%的新生儿手术未使用麻药或仅用微量镇静剂,其中有30%的婴儿术后出现长期哭闹、睡眠障碍、喂养困难等问题,这些症状与成人创伤后应激障碍高度相似。更关键的研究来自神经影像学检查。调查组用当时最先进的脑部扫描技术,监测婴儿面对疼痛刺激时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婴儿的大脑岛叶、前扣带回皮层等与疼痛感知相关的区域,会出现明显的神经兴奋信号,这与成人感知疼痛时的大脑反应模式完全一致。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婴儿感觉不到疼”的错误认知——婴儿不仅能感知疼痛,而且由于神经系统发育尚未成熟,对疼痛的敏感度可能比成人更高。1987年,美国儿科协会(AAP)正式发布《婴儿疼痛管理指南》,明确要求“所有新生儿及婴儿手术必须使用合适的麻醉药物,且需监测疼痛程度并及时调整用药”。而杰弗里的案例,被列为推动这一指南出台的“标志性事件”。遗憾的是,杰弗里虽然挺过了手术,却始终受术后创伤的影响。他童年时期极度胆小,害怕医院、医生,甚至看到穿白大褂的人就会浑身发抖;成年后虽逐渐走出阴影,却仍有睡眠障碍,需要靠药物辅助入睡。吉尔则成了婴儿疼痛权益的倡导者,她常年奔走于医院和议会,呼吁社会关注婴儿的疼痛感知,“孩子不会说话,但他们的哭声、他们的肢体语言,都是在向我们求救,我们不能因为‘权威认知’,就对他们的痛苦视而不见”。1985年的这场无麻药手术,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医学发展中“权威惯性”的盲区。当时的医生并非有意虐待婴儿,而是被长期以来的错误认知所束缚,将“经验”等同于“真理”,忽略了个体生命最真实的痛苦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