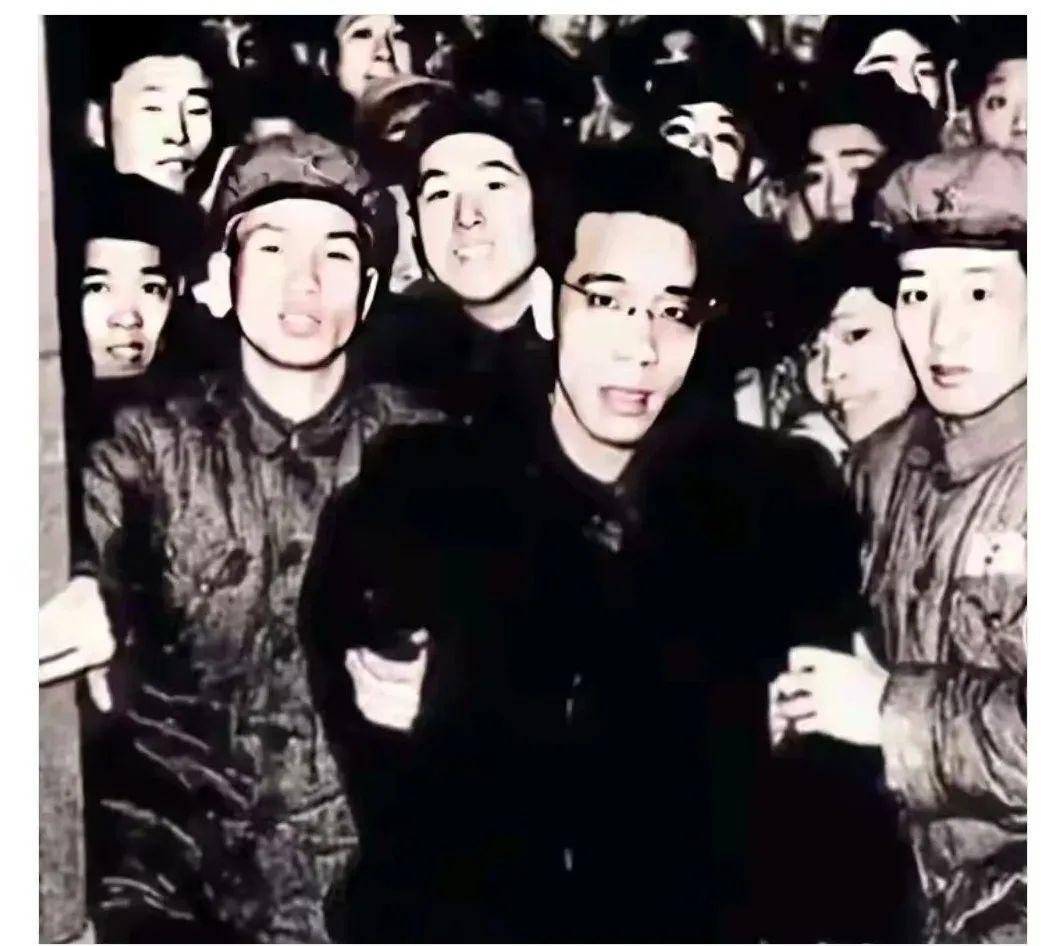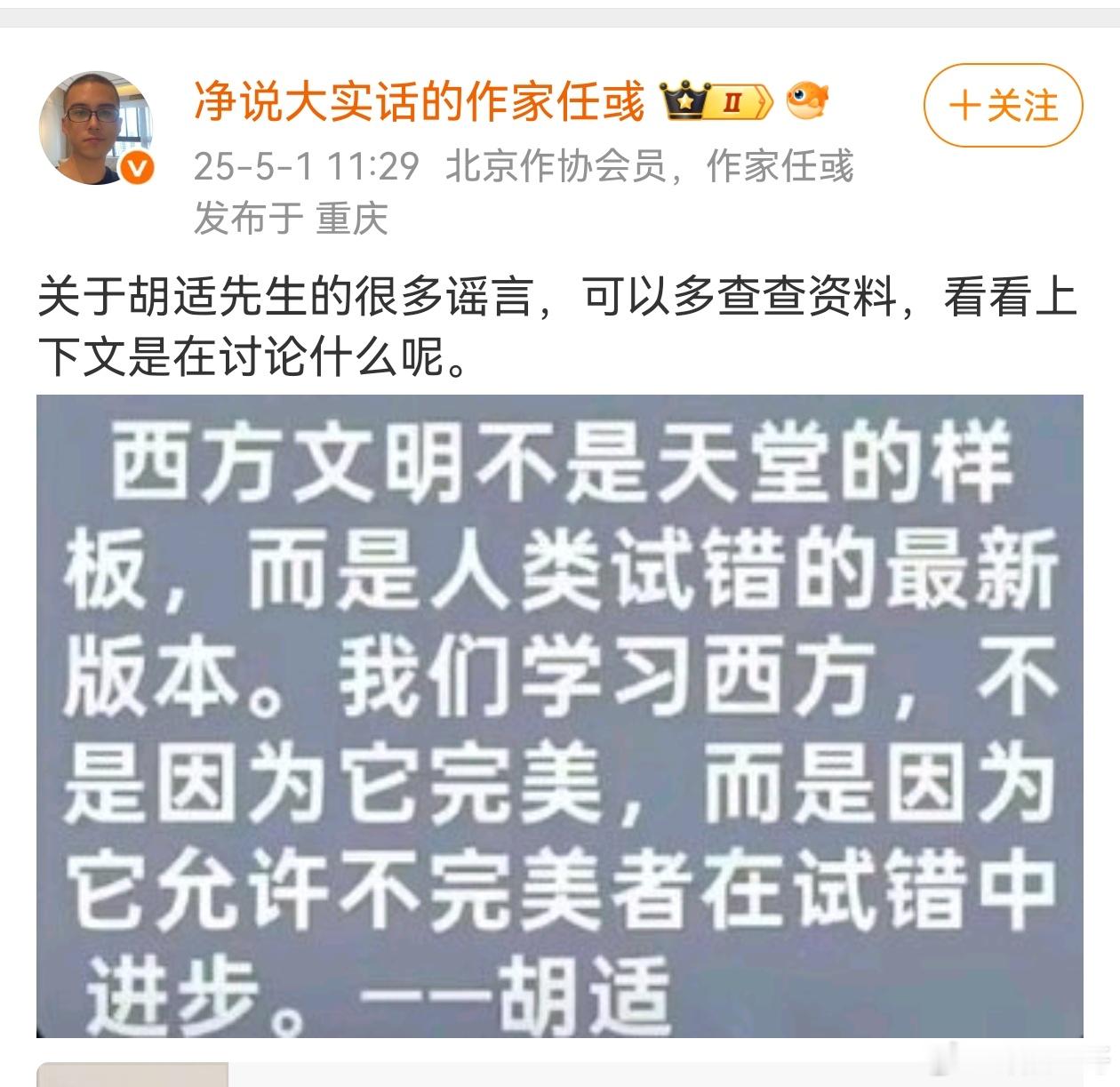在1951年的春末,中南海的菊香书屋里,毛主席正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这时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件被秘书递到他的手中。信件的内容看似平常——一位老朋友求助于他,希望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毛主席读到信尾签名时,眉头的紧锁逐渐舒展开来。为何这封信让毛主席破例,而来信人又是何方神圣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883年刘策成出生在湖南新邵县,自幼钻研《庄子》,被其思想深深吸引,尤其是对其“嫉恶如仇”的态度。日本留学期间,刘策成扩展了自己的知识视野,还加入了旨在推翻封建帝制的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等重要革命人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归国后刘策成在广西优级师范、湖南第一师范和湖南工业学校等多个教育机构担任教师,后来更是历任邵阳驻省中学校长以及浏阳、衡山、衡阳几个县的县长,其间也曾担任过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国大代表等政治职务。

1914年春,作为邵阳驻省中学校长的刘策成,联同国文教员李洞天、学生匡互生,秘密储藏武器弹药,旨在反抗袁世凯的统治并推动革命。不久后他们被湖南督军汤芗铭发现并逮捕。得知此消息的蔡锷立刻向袁世凯和汤芗铭斡旋,请求宽免,最终刘策成虽然受尽折磨,但免于死刑,并于1915年被释放。
释放当日,门外迎接他的除了家人,还有十余位曾受其影响的学生和同道。蔡锷对刘策成赞赏有加,曾评价他说:“身陷囹圄,心却与天地同阔,终日思考反帝的大业,具有坚不可摧的爱国情操。”

湖南第一师范
释放后刘策成重返教育界,在邵阳驻省中学复职,并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历史,毛主席便是他的学生之一。他的教学深入浅出,能将复杂的历史事件简明扼要地讲解,深得学生爱戴,被誉为“活历史”。
在1918年的湖南,毛主席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包括萧子升和蔡和森,共同成立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这标志着毛主席革命活动的一个新起点。那一年毛主席完成了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业,并搬到北京,开始了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工作。
北京之行为毛主席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有幸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革命先驱交流,深受其思想影响。在那里毛主席广泛阅读,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毛主席
1920年返回湖南后的毛主席发起并组织了本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此外他还启动了一个旨在教育和启蒙当地青年的文化书社,由他的同学易礼容担任经理。文化书社的创建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最初的资金,来自湘雅医科学校的赵运文,他借出了20元,这成为了文化书社的种子资金。毛主席随后与新民学会的成员以及当地教育界人士进行协商,通过集资的方式,最终筹集了519元,这为书社的启动提供了坚实的财务基础。
文化书社的初期藏书量有限,仅有不到200种书目和几十种杂志、报纸,但这些都是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工具。为了进一步扩大书籍资源,毛主席想到了自己的恩师刘策成,他给刘策成写信,表达了当前的困难和对书社未来的期望。

蒋介石
刘策成对于支持这样一项有益于社会和青年的事业毫不犹豫。他捐出了300元银洋作为资金支持,还积极鼓励毛主席继续这项伟大的事业。在刘策成的帮助下,文化书社的业务迅速扩展,到了1921年,书社已与省内外六七十个书报销售点建立了业务联系。
刘策成也在政治舞台上有了新的角色,在辞去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职后,他投身政治,担任过浏阳、衡山两地的县长。在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刘策成以其清廉、务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人民的广泛尊敬和爱戴。
在任期间刘策成撰写了《如何做好一位模范县长》一文,强调改革官场,提倡清廉,严惩贪腐。在衡山离任时,民众甚至创作了赞歌:“刘县长清如水,衡山青更深。”这反映了刘策成在民间的高度声望和人们对他工作的认可。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主席
1923年的一天刘策成作为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突然接到紧急通知:毛主席由于其犀利的文章直接挑战了军阀赵恒惕的权威,使得赵恒惕极为愤怒,决定铲除这一刺激。毛主席的文字锋利无比,直指赵恒惕的压迫和腐败,让其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赵恒惕因长期的反革命行为而恶名昭著,这一次他决定亲自下令给刘策成,要求迅速动用警力,实施对长沙的全面封锁,并将毛主席捕获,以此发泄他的私愤。面对来自上级的严命,刘策成虽身处其系统,却仍保留着对革命的忠诚与同情。
他迅速召集自己信任的副手王建屏,密谈对策。刘策成给出的第一条指令是表面遵从赵恒惕的命令,即组织警力对长沙进行严密封锁,表面上展示他的忠诚与执行力。然而,他的第二个指令是秘密行动,即在实际行动开始前,由王建屏暗中派信到毛主席,通知他立即离开长沙,从而在赵恒惕的眼皮底下将毛主席安全转移。

《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王建屏执行了刘策成的双重命令,一面按照赵恒惕的指示在城中设置检查点,加强巡逻,另一面则秘密派遣可靠的联络人前往毛主席的住处,以最高的机密级别传递逃离的消息。毛主席接到消息后得以利用这一窗口期,成功脱离险境,而王建屏也通过他的表面行动,有效地混淆了赵恒惕,使他无法怪罪刘策成处理不力。
刘策成不只一次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革命同志免受迫害。在赵恒惕的统治下,许多革命人士被捕入狱。在他们最为困难的时刻,刘策成利用自己在警察系统中的影响力,确保这些被关押的革命者不受到虐待。他还曾通过私下交涉,成功为那些未被严重指控的革命者争取到释放的机会。

周总理
1937年,当徐特立从延安回到湖南担任地区代表时,曾与刘策成有过一次深刻的交流。在那次会面中,徐特立背诵了毛主席专门为刘策成写的一封祝寿信,信中表达了深深的敬意,还回忆了他们在长沙共同经历的岁月。听完之后,刘策成被深深触动,情感澎湃。
到了1939年,国共两党在南岳山区共同组织了一次游击战术训练班,以增强抗日战争的实战能力。4月份,周总理作为高级领导干部,顺路对训练班进行了视察。得知这一消息后,刘策成特地前往南岳,以表达对周总理的敬意和支持。周总理在会面中转达了毛主席的问候与敬意,提到毛主席常忆及他们在长沙的日子,并嘱托刘策成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并关照其健康。

赵恒惕
在抗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国民政府试图利用刘策成在湖南的影响力,聘请他为国民大会代表,意图借他的声望为自己的政权加分。尽管接受了这一职位,刘策成并未完全臣服于蒋介石的命令。他不止一次地向蒋介石递交请愿书,催促其实行孙中山的民主和抗日的政策,并建议停止内战,与共产党合作。
由于反复的建议和请愿,刘策成逐渐失宠于蒋介石,多次请求会面均被拒绝。经历了这一系列政治挫折后,刘策成逐渐对国民政府表面的民主失望,最终决定回归学术,退回到湖南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在那里他投入大量时间研究并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书,淡出了政治舞台,专注于学术研究,直到晚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全国上下沉浸在空前的喜悦中。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此言一出,象征着国家新的起点。

开国大典之中的毛主席
然而对于刘策成来说,这一刻的兴奋背后夹杂着不小的忧虑。毕竟他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过高职,包括一段时间的厅长,这份履历让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经过深思熟虑,刘策成决定写信给毛主席,寻求指导。他在信中提到了两件事:一是询问如何处理自己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获得的财产;二是表达了自己希望能为新中国贡献余力的愿望,希望能在北京文史馆找到一个工作职位。尽管第一个问题对刘策成而言并不是非解不可的困扰,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是为了更好地引出第二个问题——一个关于他老年生活及贡献的问题。

文化书社旧址
毛主席收到刘策成的信后,心情复杂。虽然一向不鼓励通过私人关系求职,但考虑到刘策成的特殊背景和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他决定破例帮助。毛主席的回信简洁明了,既指示刘策成将所有家庭土地财产交给农会处理,也提到了关于工作的安排:“关于你要工作的问题,不需亲自来京,我已与湖南的同志们联系,你直接前往长沙与省长程潜联系即可。”
毛主席的回信中“不需来京找我”的表述,虽然在字面上看似疏远,实则是在规范和正常化官员聘用流程,确保一切按规矩办事,而不是走后门。刘策成接到回信后,感受到了毛主席对自己的关怀,同时也留下了一丝遗憾,因为他忘记了将自己新完成的学术著作《庄子集解内篇补正》一并寄出,以供毛主席审阅。
不过事情并未如刘策成所愿那般顺利发展。尽管他多次尝试联系长沙的文史馆,希望能尽快得到工作上的安排,但时间一拖再拖,回复迟迟未到。时间的流逝让刘策成感到焦虑,毕竟年岁已高,他感觉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可以等待。

毛主席
因此刘策成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亲自前往北京,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自己的情况,并争取一个明确的答复。
1951年5月,刘策成来到北京,当时他财产已尽,他无法承担昂贵的旅馆费用,只得选择在一间简陋的会馆暂居。到达北京不久,刘策成决定向毛主席发送了第三封信,表达了自己的困境:“我现在已抵京,若无工作,恐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
尽管毛主席曾明确告诉他无需前来北京,但在得知老师已到达北京的消息后,毛主席迅速采取行动安排对策。首先,他回复了刘策成的信件,并表示感谢对刘策成所著《齐物论集解补正》的贡献,同时告知已联系统一战线部的李维汉部长,帮助刘策成解决工作问题。

毛主席
此外毛主席安排人员将刘策成迎接至条件更佳的宾馆,并用自己的稿费支付所有费用,还特别送去了衣物和零用钱,确保刘策成在北京能有一个稳定舒适的生活环境。
毛主席还传话给刘策成:“刘老先生,您关于工作的问题我已了解,并指示周总理同志进行安排,请您放心住下。闲暇之余,不妨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周总理与李维汉讨论后,考虑到刘策成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文化背景,决定任命他为政务院文史研究馆馆员。一个月后的1951年6月1日,刘策成收到由周总理签发的聘书。
这份聘书对刘策成来说意义非凡,他潸然泪下。三次书信的往来并非寻求名利,刘策成从未公开提及曾帮助毛主席脱险的事迹。他对工作的追求,显然是出于对文化事业的热爱及个人学术的完成。

毛主席与周总理
刘策成后来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史研究和《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修订工作中,1953年该书终于出版,并被国家图书馆收藏。毛主席虽未直接评论该书,但他通过周世钊向出版社催促,确保书籍能快速排印并再版。1957年9月,刘策成在北京逝世,留下了对学术的深厚贡献和对师生情谊的珍贵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