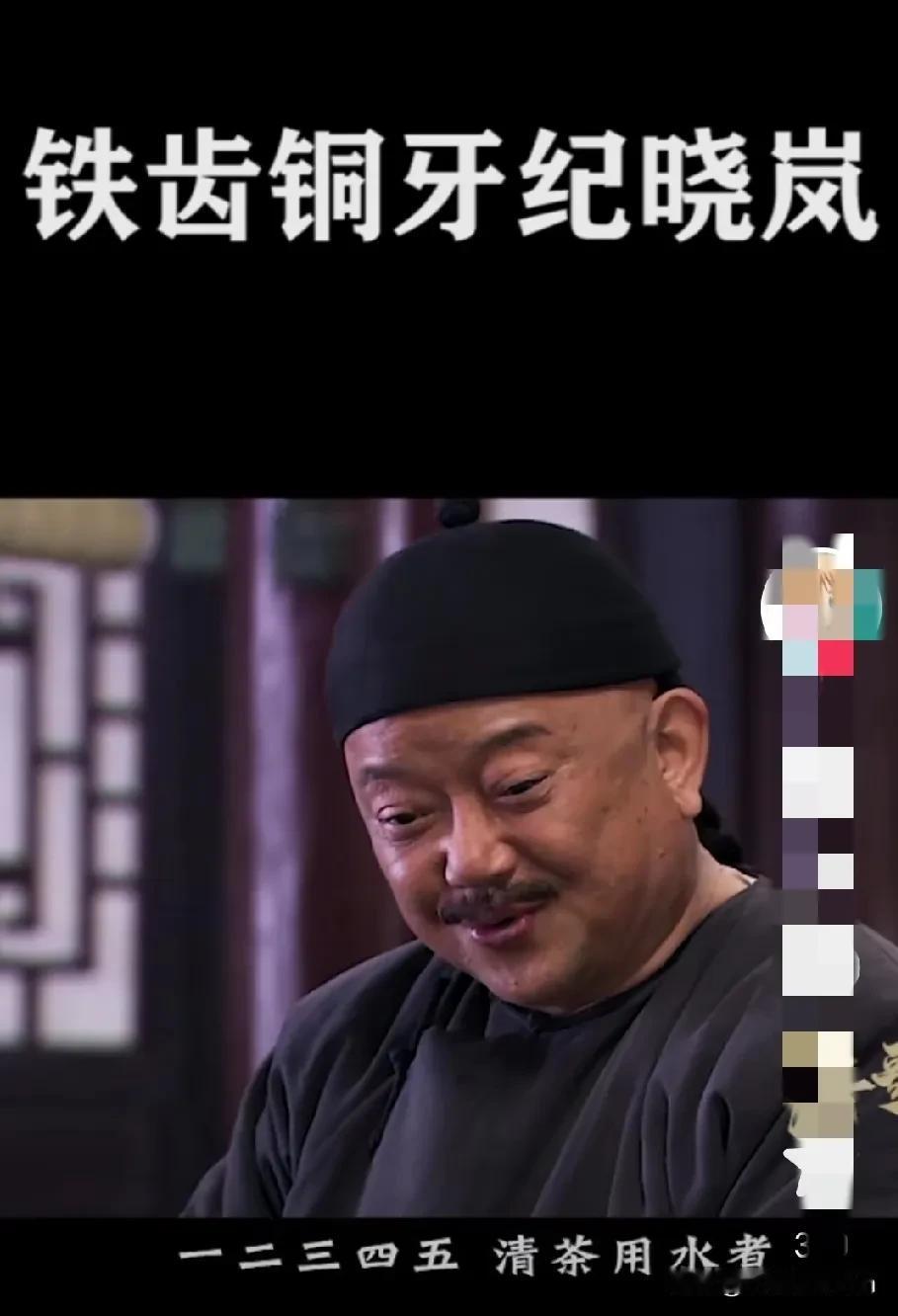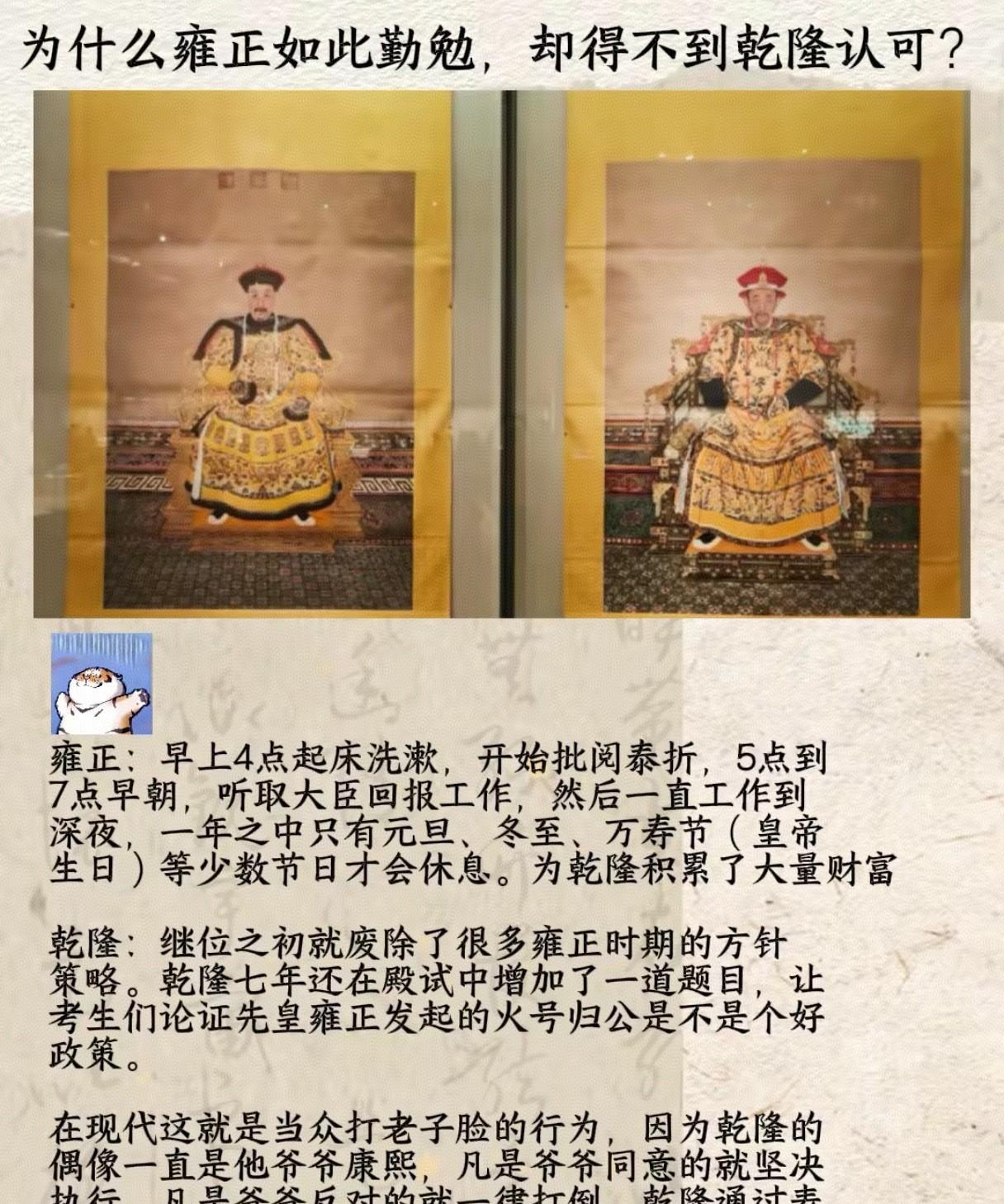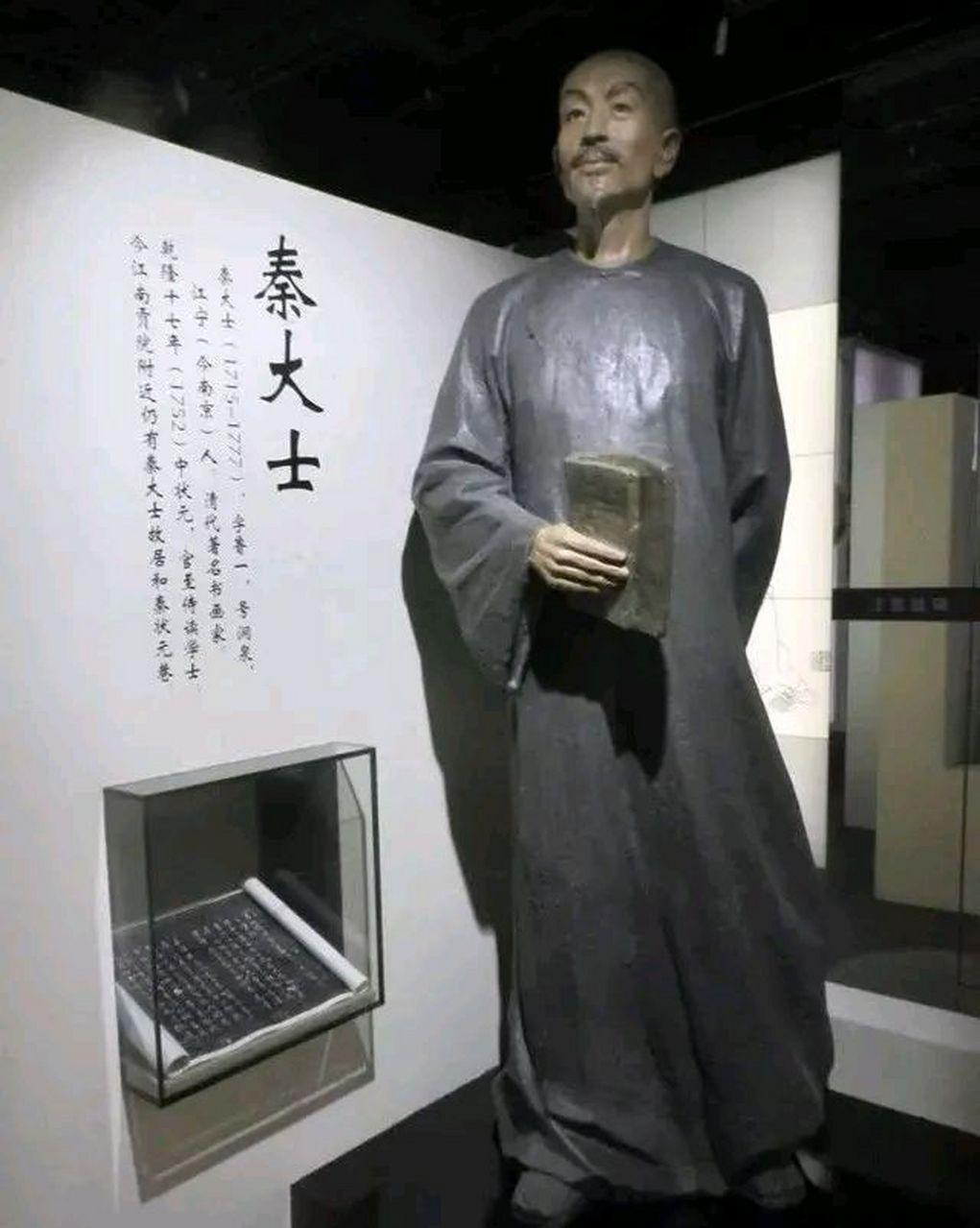乾隆茶馆闲坐,忽闻一老头骂:“皇上的诗,狗屁不通!”他刚要发火,老头下句话竟让天子当场想拜师! 乾隆三十年暮春时节,京城前门大街的“松月楼”茶馆里,一句“狗屁不通”的骂声,让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停住了脚步。 正是这声骂,反让当朝天子当场红了脸,生出拜师之念。 乾隆身边的侍卫已经按捺不住,手悄悄按在了腰间的佩刀上。这位天子自视甚高,尤其对自己的诗作颇为得意,执政三十年里写下的诗已近两万首,朝中大臣无不对他的“御制诗”交口称赞,哪曾有人敢如此当众辱骂。 他抬手按住侍卫,倒要看看这不知死活的老头能说出什么花样——毕竟刚在江南巡访时,他还因在竹炉山房即兴赋诗,被随行文人夸作“诗追唐宋”。 骂人的老头就坐在靠窗的桌旁,穿件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桌上摆着一壶冷茶,手里正攥着张抄诗的纸。听见周围突然安静,他头也没抬,手指戳着纸上的诗句又骂:“什么‘一朵两朵三四朵’,数数也叫作诗?堆砌些典故却连逻辑都不通,虚字填得再多也遮不住空洞!” 这话正好戳中乾隆的痛处。他的诗确实常犯这类毛病,为了凑数爱用“之”“而”“以”这类虚字,有时记琐事的诗句直白得像流水账。乾隆的脸瞬间热了,脚步不由自主挪了过去,侍卫紧随其后却被他用眼色喝退。 “老丈这话未免武断,御制诗自有其章法。”乾隆压着火气开口,语气里仍带着帝王的矜持。 老头这才抬头,浑浊的眼睛扫过乾隆一行人,倒没露出怯色,反而冷笑一声:“章法?老夫沈德潜当年在翰林院编书时,见过的好诗能堆成山,从没见过这样凑数的。” 这话一出,乾隆心里咯噔一下——沈德潜这个名字他熟,前朝翰林院编修,因编选《唐诗别裁集》闻名,后来因直言批评官场风气被罢官,传闻早已隐居,没想到竟在这里遇见。 沈德潜把抄诗纸推到乾隆面前,指尖点在“远看城墙齿锯锯,近看城墙锯锯齿”那句上:“这样的句子,街头孩童编顺口溜都比这有韵味。作诗讲究的是真情实感,不是记流水账,更不是靠‘御制’二字撑场面。”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皇上坐拥天下,本该写出关乎民生疾苦的好诗,可这些诗里,除了巡游琐事就是空洞感慨,百姓的温饱疾苦在哪儿?” 乾隆的脸彻底红透了,不是羞的,是被戳中要害后的震动。他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题画诗,确实多是“皇家盖章”般的敷衍,悼念皇后的诗也少了真情,反倒不如诗里偶尔提及的水利工程细节,后来还被史官拿去补证农业政策。沈德潜说的没错,四万首诗的数量,终究掩不住质量的贫瘠。 “那依老丈之见,作诗该如何?”乾隆的语气不自觉放软,甚至带了些请教的意味。 沈德潜没料到他会追问,倒也不含糊:“先学做人,再学作诗。心里装着百姓,笔下才有温度;读透百家典籍,遣词才见功力。不是每天写个一两首就能成大家,张若虚就一首《春江花月夜》,不也胜过万千平庸之作?” 这话让乾隆彻底服了。他掌权三十年,见多了阿谀奉承的臣子,却从没听过如此直白尖锐的批评。沈德潜的每句话都说到了点子上,比那些捧着诗集夸“圣明”的大臣有用百倍。他突然明白,眼前这老头才是真正懂诗的人,自己那些所谓的“御制诗”,在真正的学问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老丈学识渊博,朕……我愿拜您为师,请教作诗之道。”乾隆往前迈了半步,态度诚恳。周围的茶客和侍卫都惊得说不出话,谁也没料到这衣着华贵的客人竟是皇上,更没料到皇上会当众要拜一个老头为师。 沈德潜也愣了,随即摆了摆手:“老夫闲散惯了,教不了帝王。再说作诗的道理,老夫已经说完了,听不听得进去,全在皇上自己。”他收拾起抄诗纸,起身就要走,走到门口又回头,“若皇上真有心,不如多看看百姓的生活,比闷在宫里凑诗句强。” 乾隆站在原地,看着沈德潜的背影消失在茶馆外,手里还攥着那张抄诗纸。直到侍卫轻声提醒,他才回过神,吩咐人把沈德潜的住处记下,又让人把宫里的诗集都搬到御书房——他是真的想好好改改自己的诗了。 后来乾隆再作诗,虽仍改不了爱记事的习惯,却少了许多空洞堆砌的毛病,诗里渐渐多了些对农事、水利的切实关注。他始终没再强求沈德潜为师,却常对大臣说,真正的学问不在朝堂上的奉承里,而在民间的直言中。 那些敢说真话的人,才是藏在市井里的真先生。帝王的权力能让人闭嘴,却换不来真正的学识与尊重。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