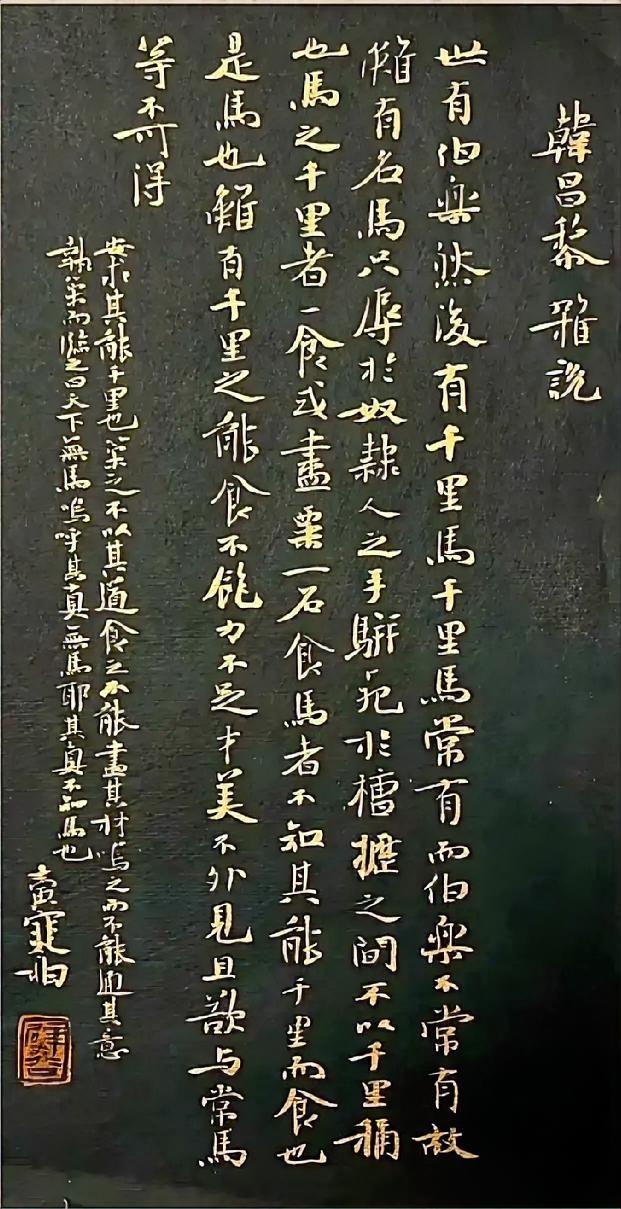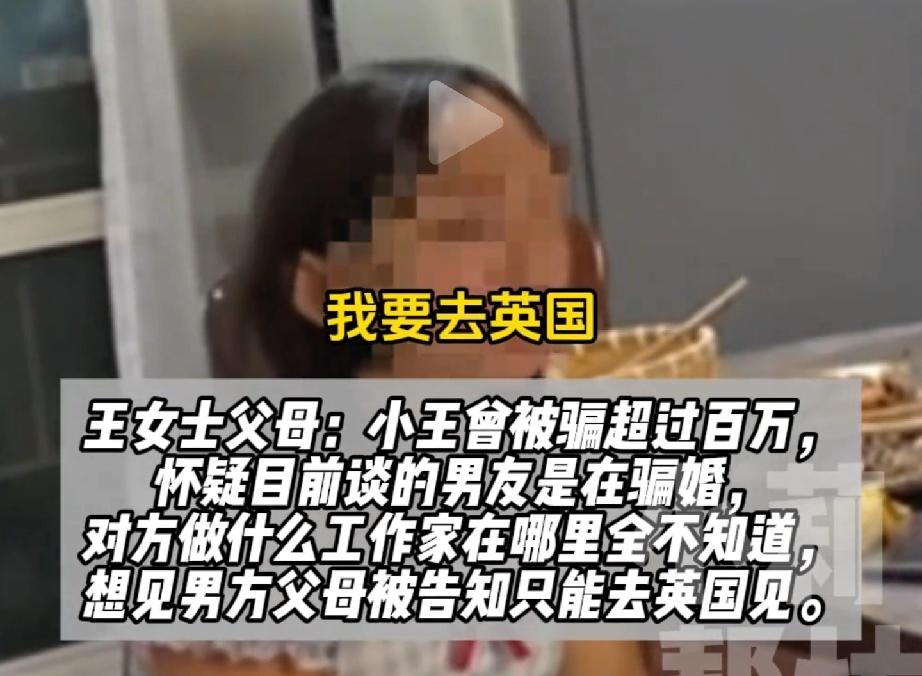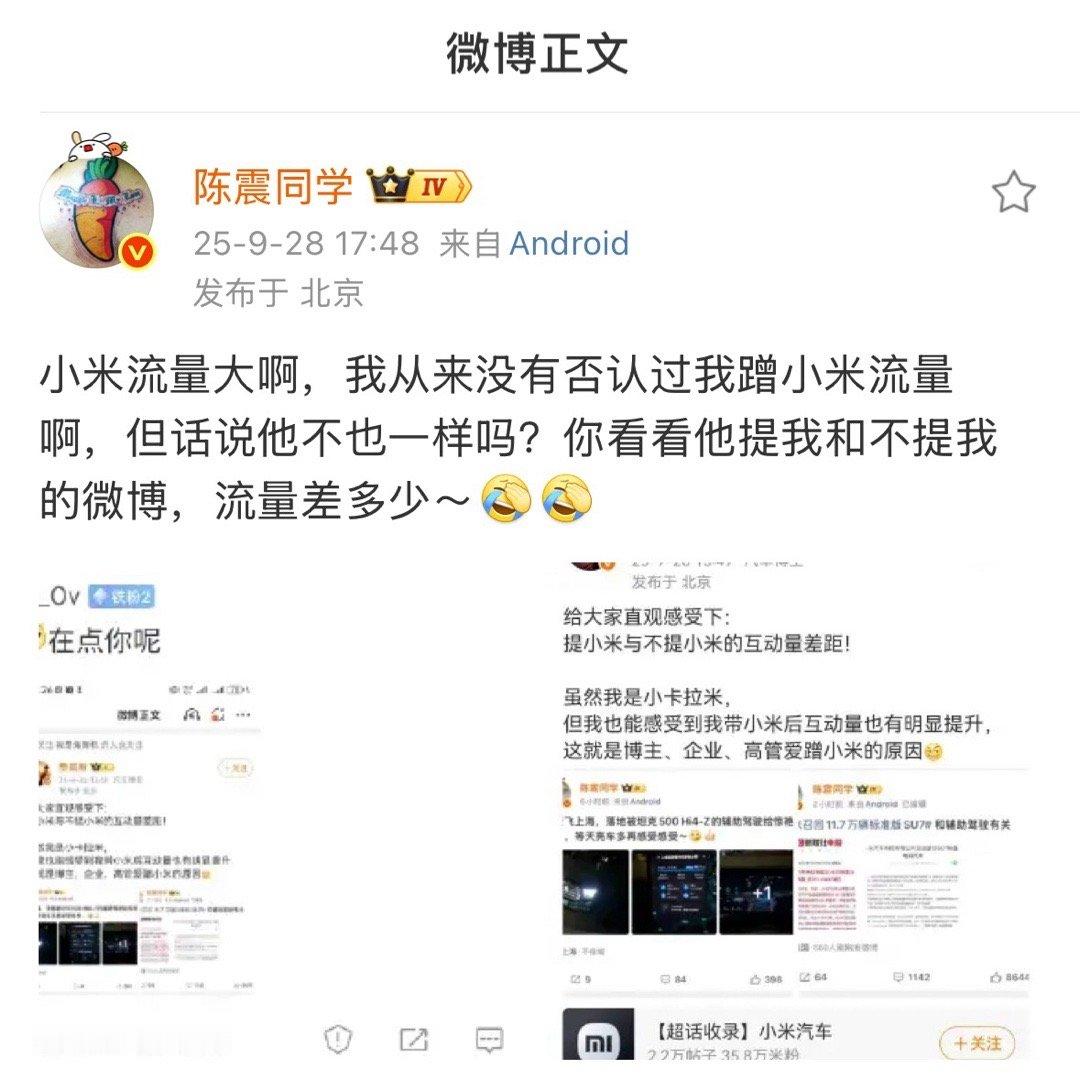1949年巴厘岛宗教仪式现场,一名妇女作为祭品被献祭,揭开神秘宗教仪式的一角! 1949年。那一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独立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整个国家都在从荷兰殖民的旧梦中醒来,摇摇晃晃地走向新生。那时候的巴厘岛,可不是现在这个挤满了网红和瑜伽馆的热带天堂。它是一座被时间遗忘的孤岛,岛上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由神明、祖先和恶灵共同组成的世界里。外界的炮火与变革,似乎都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结界。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外人看来诡异至极的仪式,正在某个村庄的寺庙前悄然准备。 这里说的“献祭”,跟想象中的血淋淋的场面,完全是两码事。在巴厘岛人的宇宙观里,人不是世界的主宰,而是维系宇宙平衡的一部分。当村庄里出现瘟疫、灾祸,或者收成不好时,他们相信,是宇宙的平衡被打破了,邪恶的力量正在作祟。 怎么办?得跟神灵“沟通”,请祂们出手,把这些捣乱的家伙赶走。可神灵高高在上,凡人怎么沟通?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媒介”了。 这个媒介,就是那位“祭品”。通常,她们是村里最纯洁的年轻女性,未经人事。在仪式开始前,她们要经过数日的斋戒和沐浴,用圣水净化身体。这不是为了让她们“体面”地死去,而是为了让她们的身体变得足够“干净”,干净到可以容纳神灵的降临。 仪式开始时,甘美兰音乐响起,那是一种叮叮咚咚、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金属敲击乐。祭司们焚香诵经,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香味。那位被选中的妇女,会在众人的注视下,慢慢进入一种非生非死、如梦似幻的状态。人类学家称之为“出神”,而当地人相信,在这一刻,她的灵魂已经暂时离开了身体,而某位神明或者圣兽的灵,已经“住”了进来。 这时候的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她可能会跳起一种凡人不可能完成的舞蹈,脚步激烈而精准;她可能会手持利刃刺向自己的胸膛,却毫发无伤。因为此刻,她的身体只是神灵的“偶”,一个在人间显圣的工具。 这才是“献祭”的真正含义——她献出的是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身体使用权,以此换取神灵的力量来庇护整个村庄。 这是一场神圣的交易,是她为族人做出的巨大奉献。对她个人和她的家族而言,这更是无上的荣耀。 这些仪式,本质上是一种集体的心理治疗。在那个缺乏现代医药和科学解释的年代,一场成功的仪式,能极大地抚慰人心的恐惧,重新凝聚社区的向心力。当那位“被献祭”的妇女从出神状态中苏醒,安然无恙地回到人群中时,人们相信,邪灵已被驱逐,神灵的庇佑已经降临。 那么,70多年过去了,到了现在,这些古老的仪式还在吗? 答案是:在,也不在。 在,是因为这些仪式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形态,依然存在于巴厘岛的文化血脉中。最典型的就是每年巴厘印度教新年“安宁日”前举行的游行。人们会制作巨大的、面目狰狞的恶魔雕像,在村庄里游行,最后付之一炬,象征着净化社区,驱逐邪灵。而在一些更传统的村庄里,小规模的出神仪式依然在特定的节庆日举行。 说“不在”,是因为随着全球化和旅游业的冲击,许多仪式已经或多或少地“表演化”了。你能在乌布的舞台上看到专门为游客的表演,舞者们同样会进入类似出神的状态,在火堆中穿行。但那种根植于村庄信仰、维系着整个社区存亡的紧迫感和神圣感,已经很难被复刻了。 根据印尼旅游和创意经济部2023年发布的数据,巴厘岛在疫情后迎来了强劲的旅游复苏,国际游客数量预计在2024年底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这意味着,巴厘岛的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观赏”和“消费”。这对当地经济是好事,但对这些脆弱的传统仪式来说,是保护还是打扰,没人能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所谓“一名妇女作为祭品被献祭”,背后隐藏的,不是野蛮的杀戮,而是一种深刻的、我们现代人或许难以完全理解的集体信仰和精神联结。 我们习惯于用自己的逻辑去评判世界,用“科学”和“迷信”给一切贴上标签。但巴厘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类的精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丰富。在那个小岛上,神明与凡人共舞,生与死的界限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