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能源部的大干部,离休了。 你以为他要去北京哪个干休所里养花弄鸟,安享晚年? 他却回家回到老家筹建电厂! 熟悉李廷魁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跟电结缘太深。 从年轻时在基层电站爬电线杆,到后来在能源部参与全国电力规划,办公室墙上的电网图换了一版又一版,可他总念叨老家新安的夜晚——电压不稳的灯泡忽明忽暗,冬天取暖靠煤炉,村里的小加工厂一到用电高峰就得停工。 离休前最后一次回乡调研,他看着路边堆着的玉米秸秆被村民一把火烧掉,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回来就跟老同事说:“新安不缺能源,缺的是把资源变成电的法子。” 决定建电厂的消息传开,村里炸开了锅。有人说老领导闲不住,也有人暗地里嘀咕:“北京来的干部懂啥农村事?建电厂要占好地,万一搞砸了咋办?”李廷魁不辩解,带着从部里带回来的旧地图和几本技术手册,天天往县发改委跑。 第一次去提交项目建议书时,工作人员看着这个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递过来的表格都带着迟疑:“李老,建电厂得先过可行性研究,光有想法不行。” 他听了这话,反倒来了劲。回家翻出当年参与国家生物质发电试点的资料,又联系上几个仍在岗位上的老部下,视频电话一开就是半宿。 一个月后再去发改委,手里的材料厚了三倍:从新安周边秸秆年产量测算,到附近变电站接入容量评估,连环保排放标准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他指着数据跟工作人员说:“咱这电厂烧的是秸秆,既解决污染问题,又能给农民添份收入,你算算这账。” 最难的还是筹钱。参考同类项目的投资规模,一个3万千瓦的生物质电厂总得两三亿资金。李廷魁揣着可行性报告,跑遍了省里的能源企业,对方一看是县级小项目,大多婉言谢绝。 有次碰了钉子,他在企业楼下的花坛边坐了俩小时,望着来往的年轻人,掏出手机给老战友打了个电话:“当年咱们搞西部电网攻坚,比这难十倍不也成了?新安的事,我放不下。” 这话传到一家央企负责人耳朵里,对方深受触动,最终答应以资本金入股的方式参与项目。 审批手续的繁琐超出想象。 光是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就得跑自然资源、环保、林业好几个部门。李廷魁不觉得麻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准备材料,有时为了一份盖章文件,能在部门办公室外等到下班。 有次环保评估会上,专家提出秸秆运输可能造成二次污染,他当场拍板:“咱们建秸秆收储点,统一打包运输,再给运输车辆装防尘布,绝不能让污染问题出在咱这环节。”这种较真的劲头,让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县领导也动了心,专门成立工作组帮他协调手续。 开工那天,李廷魁没剪彩没讲话,戴着安全帽在工地转了整整一天。看到推土机平整土地时,他突然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在手里攥了攥。施工队负责人过来打招呼,发现老领导眼眶有点红: “李老,您这是……” 他摆摆手:“没啥,就是想起年轻时修电站,也是这样一砖一瓦干起来的。” 建设期间,他每周都去工地,安全帽上的红漆被晒得褪了色,裤脚总沾着泥。有次暴雨冲坏了临时道路,他跟着工人一起扛沙袋,年轻人劝他休息,他说:“我这把老骨头,多活动活动才结实。” 一年半后,电厂汽轮机第一次转动起来。并网发电那天,李廷魁站在主控室里,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发电量数字,给远在北京的老同事打了个电话:“你听,这声音多踏实。” 投运第一个月,电厂就消耗秸秆8000多吨,附近村民拉着秸秆来卖,过磅时脸上的笑藏不住。曾经质疑的人也改了口:“没想到这电厂真能给咱带来实惠,李老这是给新安办了件大好事。” 如今电厂运行稳定,每年能发两亿多度电,不光解决了县里的用电缺口,还带动两百多个就业岗位。 周边乡镇的秸秆有了去处,每吨能卖三百多块,光这一项就给农民增加不少收入。冬天厂里搞起热电联产,附近的学校和养老院再也不用靠煤炉取暖。 有人给李廷魁算过账,按他的级别,在北京干休所能领不少补贴,跑来搞电厂纯属“亏本买卖”。他听了这话,只是笑笑:“人这辈子,总得干点让自己老了不后悔的事。” 从部委大院到田间地头,李廷魁用一座电厂诠释了什么叫离休不离岗。他用专业和坚持证明,真正的为民服务不在职位高低,而在心里装着多少百姓期盼。这样的坚守,或许比任何荣誉勋章都更有分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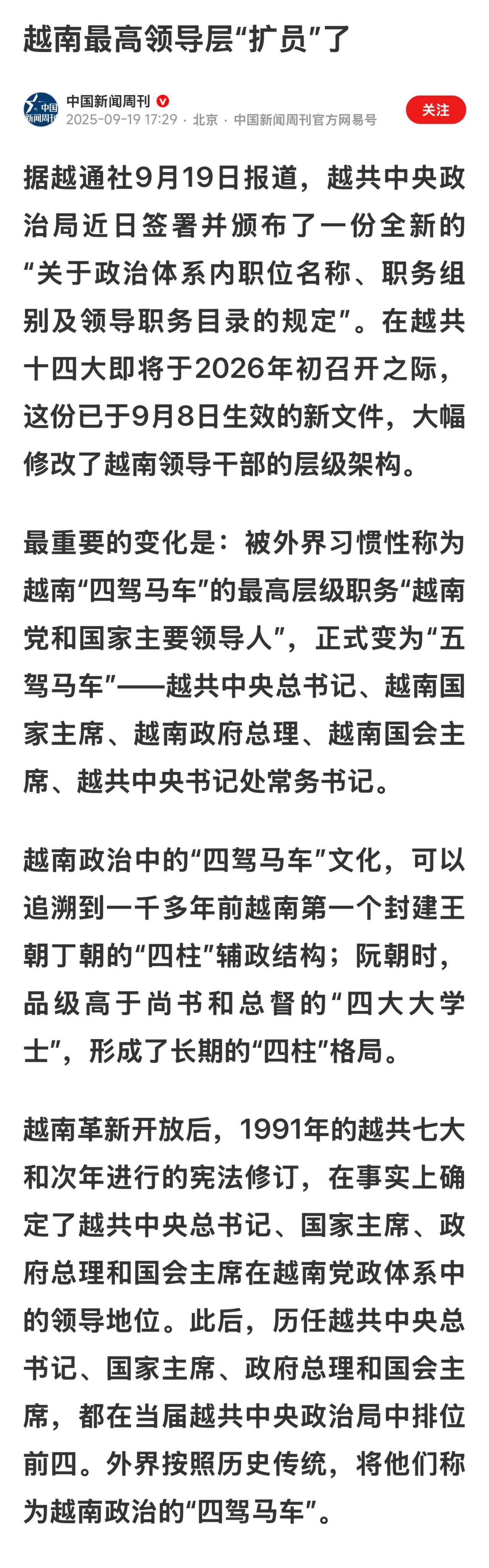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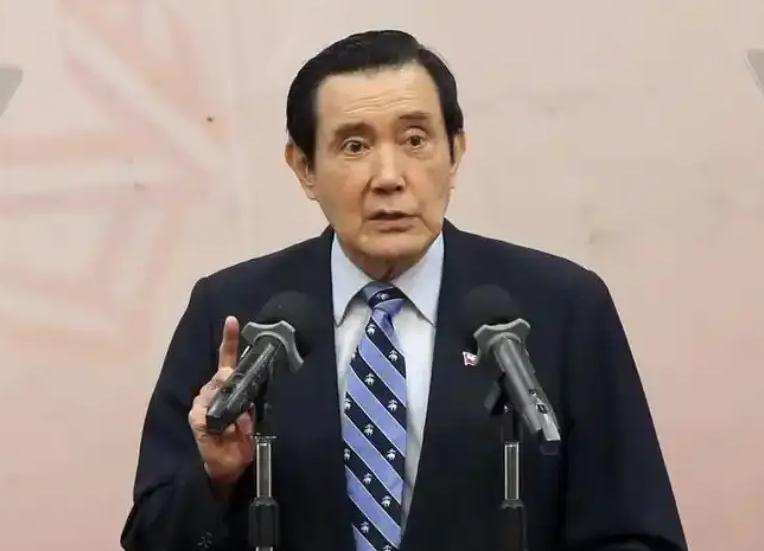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