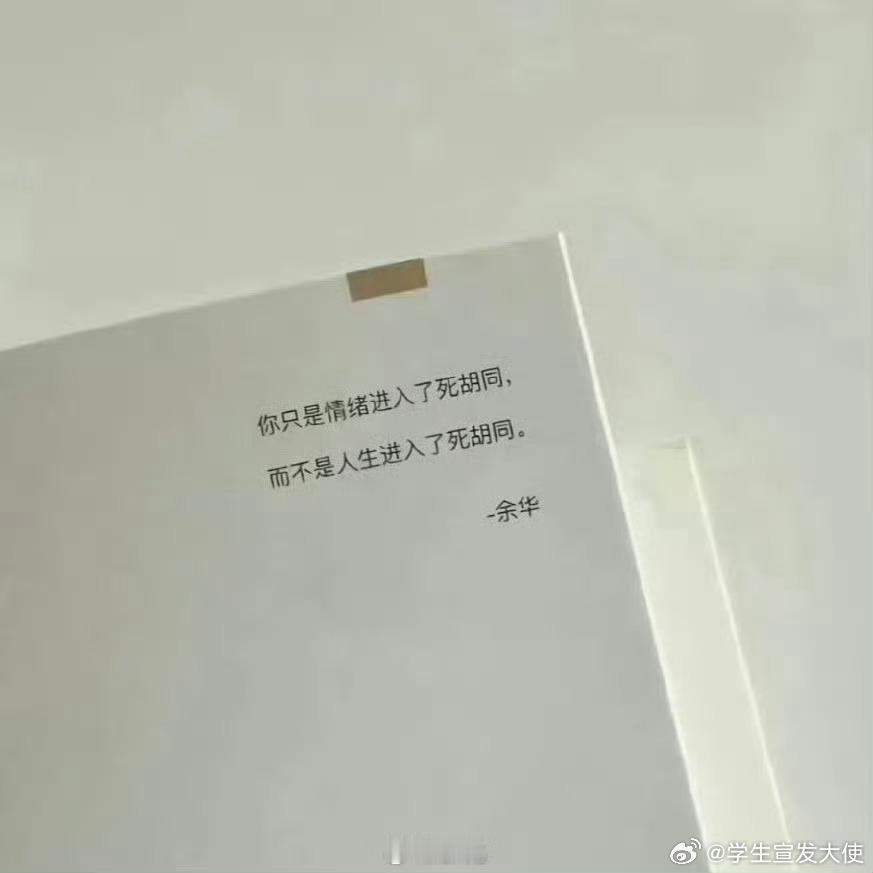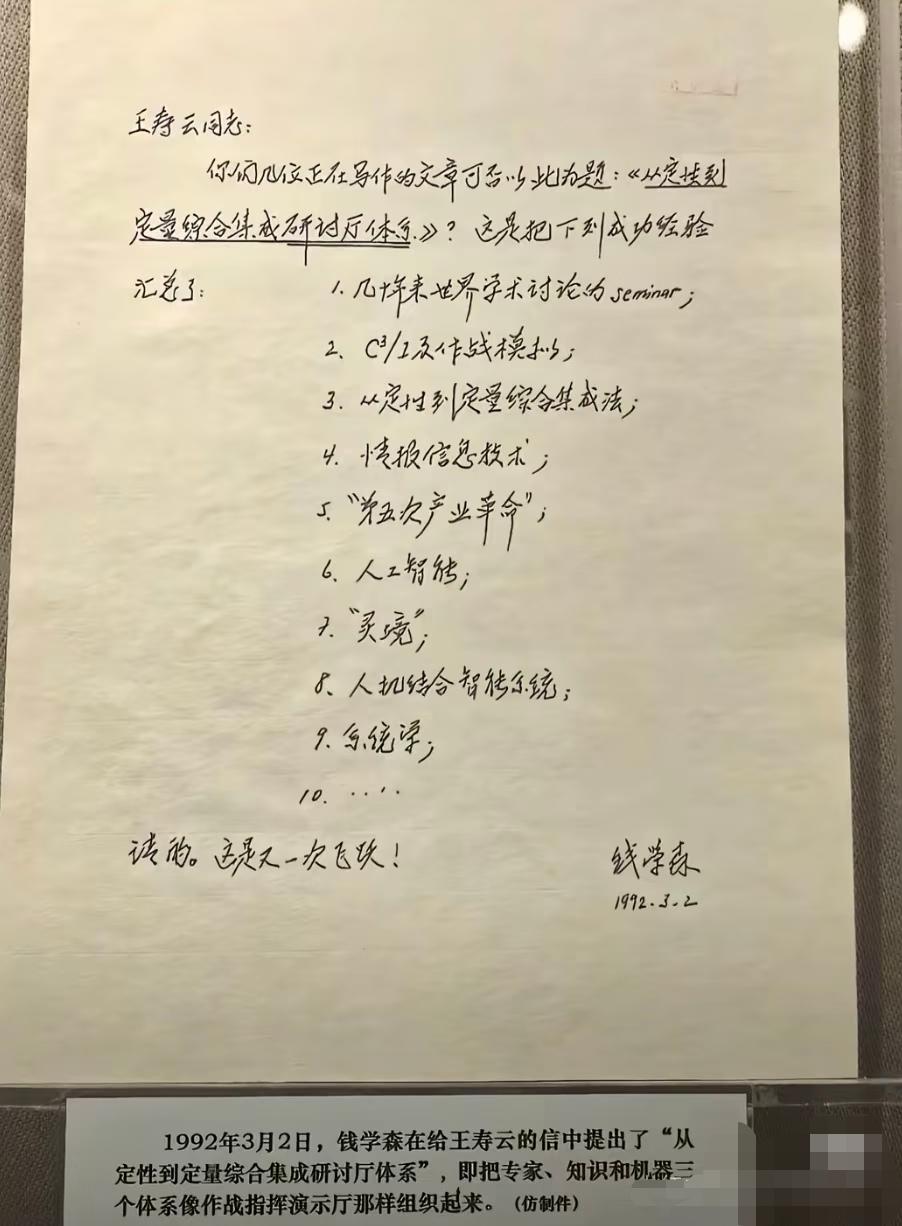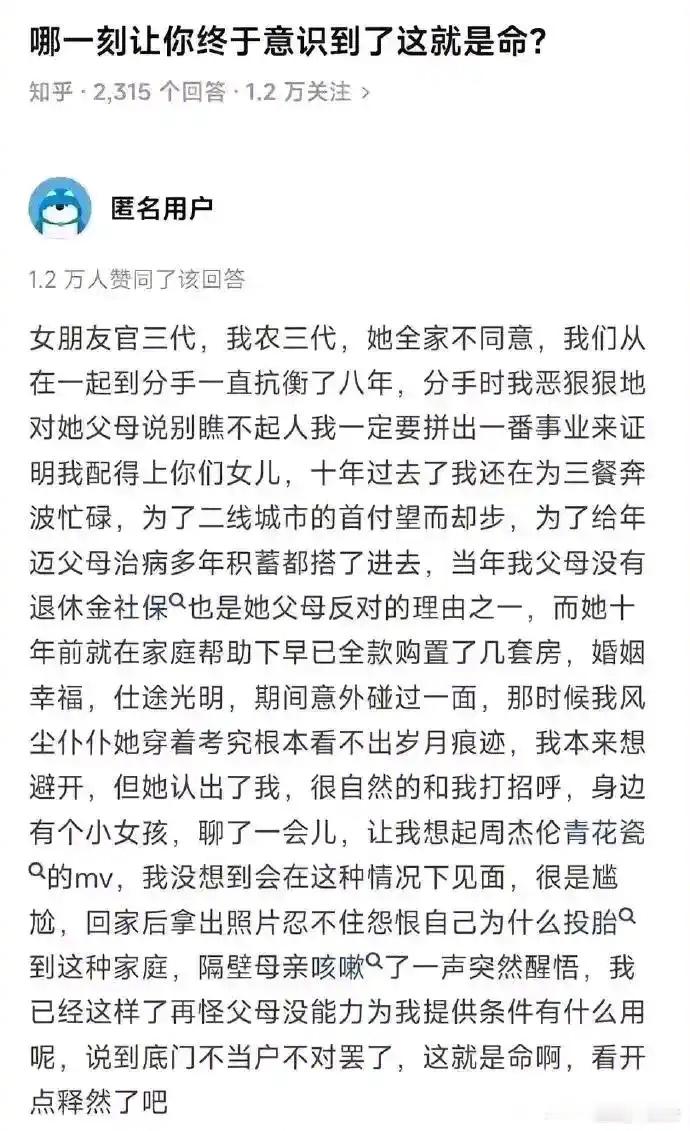1981年,阎连科拿着117元退伍费回家,团长追到车站将他召回提干 1981年12月下旬,济南火车站的站台冷得像把刀子。阎连科挤在候车的人群里,棉大衣口袋里塞着一张硬座车票和117元退伍费,那点钱被他包在报纸里,揣得紧紧的。就在列车即将进站时,一辆军绿色吉普车猛地刹在台阶下。车门被推开,团长探出身子,高声喊:“小阎,先别走,命令有变!”阎连科愣住,简短敬礼:“团长,我听命。”这句对话后来在战友间传了很久,像个突兀的尾音,把他的命运硬生生拽了个急转弯。 把时间拨回三年前。1978年春,河南嵩县的土路上扬着尘土,20岁的阎连科挑着行李去县武装部报到。之前,他写了30万字的小说手稿,母亲忧心“写字不当饭吃”,一把火烧了稿子。作品没了,贫困还在。为了挣口粮,也为了躲开那股被扼住嗓子的窒息,他决定参军。刚下连,他对枪械和队列一样生疏,但他对书却像着了魔:口袋里塞着《战争与和平》,铺位下藏着《悲惨世界》,连夜间站岗都捧着。连里射击考核他竟神乎其技打了“满环”,战友摇头:“这人,读书也行,打靶也行,邪门。” 1979年初,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济南军区没有直接参战,但内部也在紧张备战。就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挑出几个文笔好的兵去武汉军区参加小说写作培训。阎连科的名字排在最前头,一个月的培训,时间短,却像在他脑子里安了发条,他开始明白写作不只是宣泄,更是技艺。他试着写了3000字的小小说,《新兵夜话》,稿子寄出去不到半个月便刊发在军报副刊上,稿费8元——足够他全排请一顿饺子。从此他被调到营部当报道员,写连史、写简报、写典型材料,写得手起刀落。那两年他连拿两个三等功,又火线入党,射击名次却稳居前三,算得上“文武双全”。 1981年上半年,部队接到精简整编的硬指标:精兵简政,压员裁干。普通士兵提干名额所剩无几,文化兵又常被视为“可有可无”。年底评审,阎连科榜上无名,他索性打报告复员。退伍证、117块钱和一张铺面向西安的火车票——这就是当时的全部结局。谁也没想到,北京总政举办的全军文艺汇演里,他临别前写的独幕剧《二挂鞭》拿了头奖。组委会给总政打报告:“创作班底里有几个优秀战士,建议解决干部编制。”济南军区随即获批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写着“阎连科”。 于是站台上一幕出现。团长一句“命令有变”把他从退役线拉回军旅。部队允许他先回家一周。回到嵩县,父亲卧床咳喘,母亲的眼神比往年更浑浊。阎连科犹豫:留下务农、陪父亲,还是再穿回军装?姐夫在邮电局当工人,拎着半袋面粉赶来劝他:“穿军装的读书人成不了状元也饿不死,走吧,别死心眼。”阎连科第二天就买票返程,算是赌一次。 提干手续批得飞快,他从班长一跃成排职干部,分管宣传。待遇改善,婚事也随之落定:几个月后,他与医院工作的王梅喜结连理。1985年,他把苦熬多年的中篇《忧郁的蒲公英》寄给《解放军文艺》,稿费800元寄到连里,连长看着汇款单直嘬牙花:“这得相当于一个士官一年的补贴!”从那以后,他陆续推出《黄金洞》《年月日》等作品,风格晦涩,骨子里却透着兵味——那些战壕、哨卡、夜行军的灰尘全在字缝里。 2004年,多方原因,他选择转业。脱下军装后,他继续以小说针砭现实,文字锋利得像旧刺刀。有人说他的书“拧巴”,也有人喊“震撼”。2009年,《我与父辈》首发于同济大学,校长握书红了眼眶;几名高中生在采访里说,边看边哭,“才知道亏欠父母有多深”。文学圈评价更不吝溢美,刘震云言辞犀利:“莫言能拿诺奖,阎连科也行。”卡夫卡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接踵而至,可他的多部作品在国内曾被停印。有人替他抱不平,他简单一句:“写作就是发声,堵不住。” 对阎连科来说,117元退伍费不过一串早该花完的旧钞,可那辆在站台急停的吉普车,却像一个隐形支点,改变了他此后四十年的轨迹。硬朗的军旅生活给了他对秩序与苦难的双重感知,也给了他写作的无穷矿脉。若当年团长那声呼喊晚到五分钟,今天的文坛恐怕会少一位“兵味”作家,嵩县乡间也少一个远走高飞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