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欧美国家不吃动物内脏,而中国人吃动物内脏,一位海归朋友说:国外媒体暗讽我们就像未开化的野人。 因为吃法和处理动物内脏的诀窍不一样。 中国的屠户早有章法:猪肝要浸在清水里换三遍血,肥肠得用盐和面粉反复揉搓去黏液,鸡杂要分部位焯水 —— 这些代代相传的手艺,让原本带着腥气的内脏,能变成卤煮里的软糯、爆炒后的鲜嫩。 可在不少欧美国家,这样的场景却不多见。 有人觉得是他们没尝过饥饿的滋味,其实,这背后藏着的是屠宰技术、资源禀赋与时代变迁拧成的绳。 屠宰的精细程度,从来是吃内脏的前提。 宋徽宗年间,使者徐兢去高丽,见当地人为了招待他宰猪羊,竟是 “缚手足投烈火中,候其命绝毛落,以水灌之”,结果 “肠胃尽断,粪秽流注”,炖出来的肉臭不可闻。 不是高丽人不想吃好,是他们平时难得见牲畜,压根没练出利落的屠宰手艺。 反观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 “屠肆” 专门处理牲畜,《齐民要术》里甚至记载了 “净肠法”:用盐水反复冲洗,再以花椒去腥 —— 技术到位了,内脏才成了可利用的食材。 欧洲的情况更复杂些。 中世纪的庄园里,农奴们用着罗马浅犁,只能把土地犁出浅浅一层,小麦亩产最高不过 70 斤,连人吃的粮食都紧俏,哪有富余喂牲口? 牲畜少,屠宰就成了稀罕事。 偶尔宰头牛,农奴们能分到点边角肉就不错了,内脏要么因不会处理烂掉,要么被领主随手丢弃。 直到后来引进中国的深耕犁,粮食产量提上来,畜牧才慢慢多了,可处理内脏的手艺没传下来,也就难怪多数人对这东西犯怵。 但也不是所有欧洲人都不爱内脏。 法国的屠户们早就发现,鹅肝在特定喂养下会变得油润丰腴,于是琢磨出用管道定量灌食的法子,让鹅肝长到寻常的数倍大 —— 这道后来成了法餐招牌的鹅肝,本质就是把内脏吃出了讲究。 苏格兰人更直接,把羊肝、肺、心剁成馅,拌上板油和香料塞进羊肚,炖得软烂,起名 “哈吉斯”,成了国菜。 南欧的意大利人炒牛肝,用橄榄油爆香蒜片,火候拿捏得和咱炒猪肝如出一辙,可见只要有机会接触,内脏也能成美味。 美国人对内脏的态度,倒是跟着时代变了样。 19 世纪的食谱里,烤牛心、炖牛舌的做法密密麻麻,说明那会儿的人吃得香。 可到了 20 世纪,大牧场、大工厂成了主流,一天要处理上万头牲畜,分拣内脏太费人工,索性一刀切 —— 扔了更省事。 只有南方小镇还留着老习惯,比如把牛睾丸裹面油炸,叫 “洛基山牡蛎”,算是给内脏留了个念想。 这哪是不爱吃,分明是工业化效率掐断了念想。 再看咱们身边,挖野菜的竹篮、问 “吃了某” 的招呼,藏着的是对食物的敬畏。 1942 年的冬天,能找到的树皮、草根都成了救命粮,更别说动物内脏。 就是这种 “有啥吃啥” 的韧性,逼出了处理内脏的百般手艺:夫妻肺片要用二十多种香料卤制,九转大肠得经过九道工序去味,连不起眼的鸡杂,也能在泡椒的爆炒里变得酸辣开胃。 其实不止中国,资源紧俏的地方,总能把食材用到极致。 日本山地多,粮食少,就把鱼籽腌成明太子,鱼鳔熬成花胶,连鱼骨都要炖成高汤。 东南亚的小贩,能把鸡胗、鸭肠卤得咸香入味,用芭蕉叶一包,就是街头最俏的零食。 这些和咱吃内脏的道理一样:不是穷,是懂得珍惜每一份能入口的东西。 饮食这回事,从来不是非黑即白。 有人爱牛排的鲜嫩,有人恋卤肠的醇厚,背后是不同土地上长出的生存智慧。 刀工、火候、调料,不过是把日子过下去的法子 —— 至于哪种更好,吃的人心里最清楚。 有网友说,吃不吃内脏哪是饿不饿的事儿,全看会不会做。 咱能把猪大肠洗得比脸还干净,卤得香飘一条街,欧美那边没这手艺,自然觉得内脏腥。 也有人觉得是资源闹的,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啥都得物尽其用,内脏不浪费。 欧美早年畜牧业靠天吃饭,牲口少,哪有闲心研究内脏做法。 还有人抬杠,说法国鹅肝、苏格兰哈吉斯不也是内脏?说白了就是偏见,觉得自己吃的是高级料理,别人吃的就是 不值钱玩意儿。 更多人觉得没必要较真,饮食就是过日子的习惯,你爱啃牛排我爱吃卤煮,各有各的乐子,非要分个高低,纯属瞎操心。 那么你们怎么看呢?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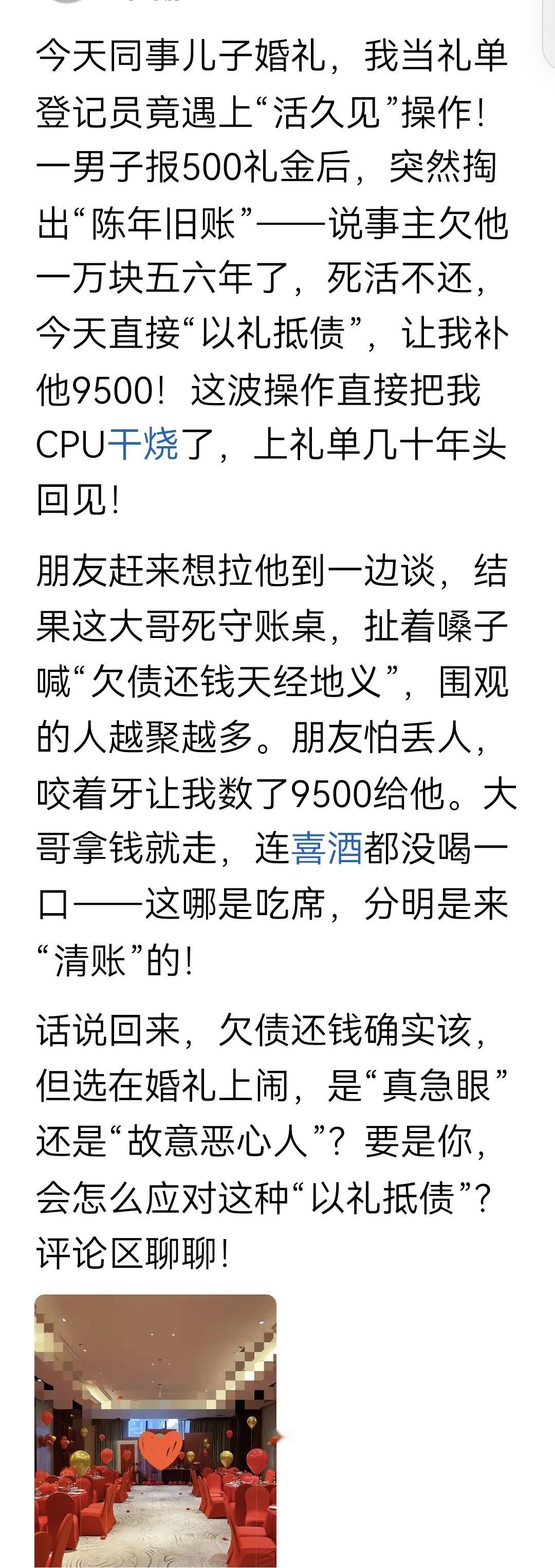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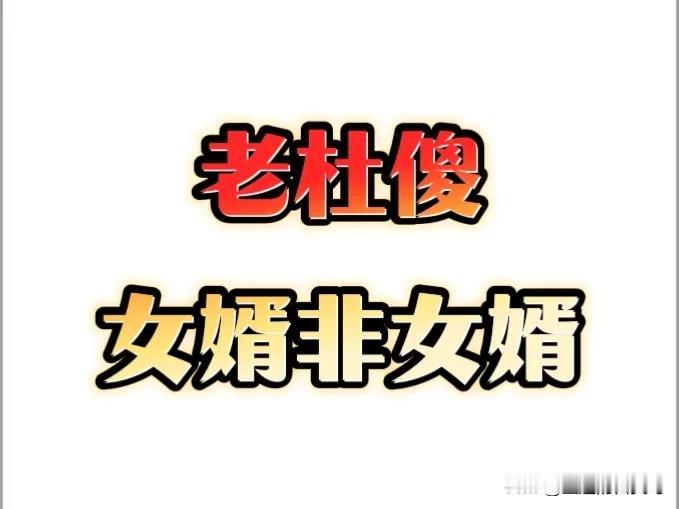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