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在山上休息的迫击炮手陈宝柳,忽然发现30多个日军和几个女人,正在不远处的榕树下,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悄悄架起迫击炮,打算给他来一发。
1943年2月,21岁的陈宝柳被当地当局拉去当壮丁,和村里其他八个年轻人一起出发。那个时候征兵可不讲道理,抓到就走。他一路从温州走到丽水,分配到西南部队第六营第二连第三排。部队的长官有总司令李墨庵、副师长关周同、连长丁银河什么的。那些同村的伙计分散到不同单位,到抗战结束,只有陈宝柳一个人活着回来,其他人都没了影。这一路上,部队没时间给他们正规训练,边走边练,勉强适应。刚入伍一个星期,他就领到一支轻机枪,直接扔到火线上去了。战场上枪炮声不断,他趴在壕沟里射击,看着日军从头顶跨过去,好几次捡回一条命。丽水松阳、衢州龙游那些地方都打过,来回拉锯战打了一年多,兰溪一仗败了,又退到江西遂昌。过程中,他的左脚踝被日军子弹削掉一块肉,血肉模糊的,简单包扎一下就继续上阵,没工夫细治。
后来,大概1945年,因为他身体结实,不容易被炮的后坐力震晕,部队把他调到第一百零八师炮兵连。那个连队只有两门迫击炮,每门炮配六个人,轮流负责开炮,其他人就抬炮弹。炮是意大利造的45毫米口径,老掉牙的东西,重六十斤,从江西赣州背到浙南山区,一路颠簸。他把这炮当成宝贝,其他人嫌累赘,他却天天琢磨。没有测距仪,他就抓把土扔空中看风向;没弹道表,就靠反复试射记规律。开炮的时候,后坐力大得很,很多人第一次就被震蒙,但他底子好,保持清醒。渐渐地,他的瞄准技术练出来了,百发百中,队友都佩服。卡壳了,他就用通条快速捅开,动作利索得像吃饭一样平常。
1945年,他所在的部队在浙南山区活动。他在山上歇息时,发现三百米外一棵大榕树下,有四十来个日军在休息,抽烟的抽烟,武器堆一边,还有几个当地妇女被绑着蜷在那儿。日军人数多,包括一个中队长。他觉得机会来了,悄悄组装迫击炮,第一发炮弹直接砸中人群,炸得他们乱成一锅粥。第二发点着了他们的弹药堆,引发大爆炸。第三发堵了下山的路,土石崩塌封住通道。三发炮弹下去,四十个日军全没了,包括那个中队长,那些妇女却没事。这事让他在部队里出了名,大家说他炮长了眼睛。日军后来悬赏捉他,但连长相都摸不清,只知道是个黑瘦高个,平时不爱吭声,打仗时变了样。
这之后,他继续在温州一带反击日军。他的炮火专挑巡逻队下手,打得日军不敢随便进山。有次夜里,借着月光,他一炮端掉四百米外的机枪阵地,队友看呆了。那门老炮射程有限,精度不高,但他玩得有灵性。转移时遇山洪,他把炮拆成零件,用油布包好顶头上游过河,上岸第一件事检查撞针有没有坏。总的来说,像他这样的兵不少,但能把土炮玩出花的真少见。抗战那几年,他算不清杀了多少日军,但榕树下那次印象最深。
日本投降了,部队在江西赣州抓到八个日军藏在祠堂,缴了枪送师部。后来单位移防金华,长官给选择:回家种地还是去舟山打仗。他选回家,因为觉得共产党是战友,不是敌人。退伍后,他回到永嘉老家,娶妻生子,继续务农。家里几个孩子都孝顺,两个儿子受他影响,也去当兵,把军人当成光荣的事。战争留下的后遗症不小,左脚伤没好全,走路有点跛,心脏因为炮震受损,得靠药维持,七八年前还做过手术。但他日子过得平静,偶尔喝点酒,跟人聊聊当年的事。
九十三岁那年,他拿到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举起时眼睛有点湿。这事后来写进军事教材,当成迫击炮战术案例。不是战术多牛,而是普通人靠热血和本领写传奇。我们现在用高科技打仗,GPS、激光什么的,但陈宝柳那套靠经验和直觉的办法,有时候更管用。那个时代的手艺人多,靠苦练出一身绝活,现在年轻人少有耐心花十几年琢磨一件事。想想看,他从农家小子到神炮手,全凭那股钻劲。战争残酷,日军干的坏事不少,但陈宝柳这样的兵,用行动回击了。历史就这样,一代人扛起责任,换来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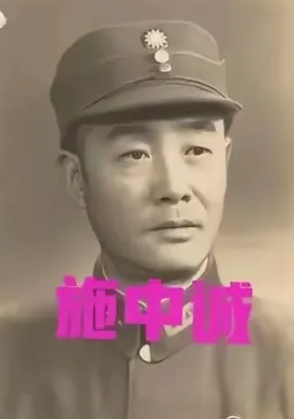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