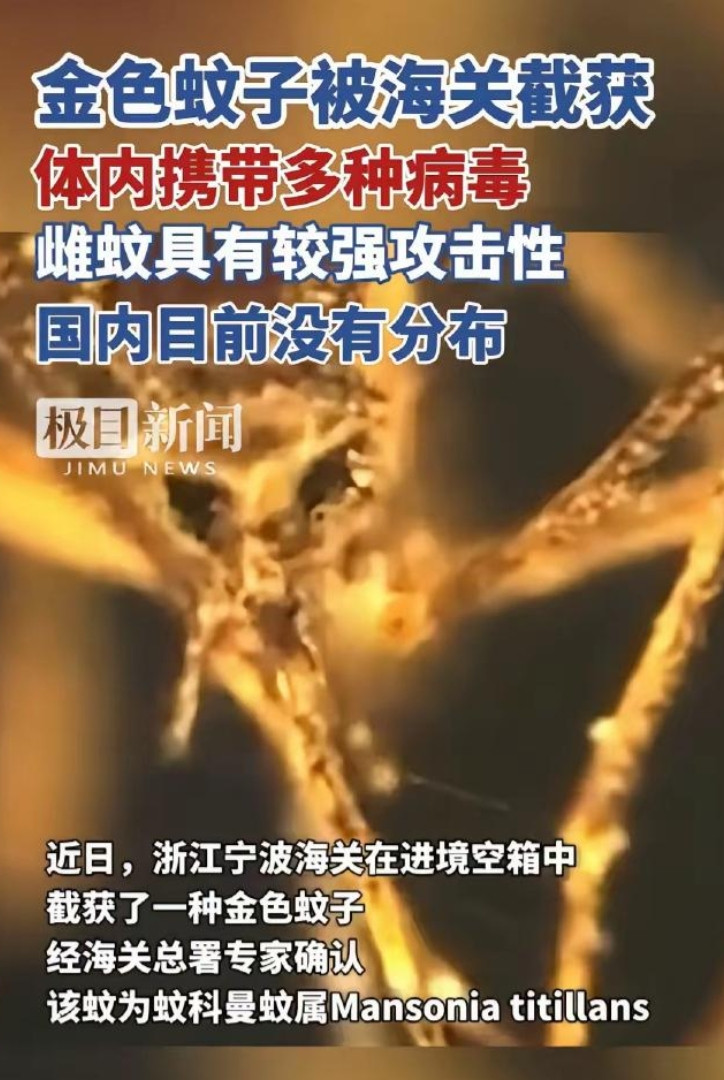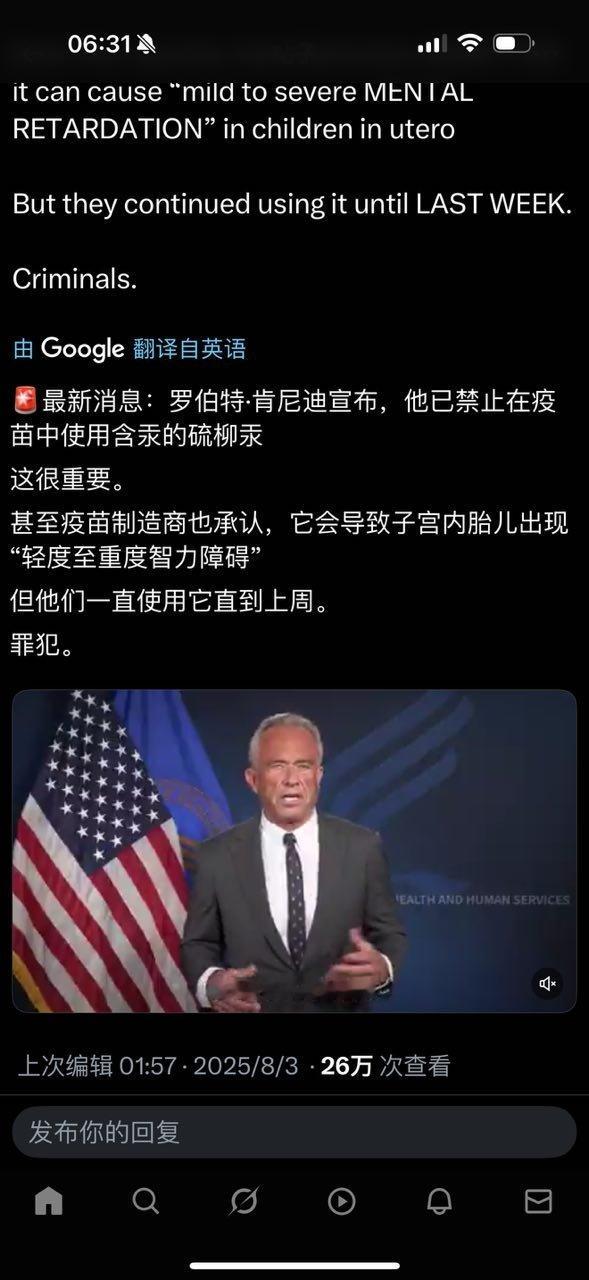为什么非洲人不怕艾滋病?因为在非洲所有的慢性病都排不上号,而像艾滋病这种小克拉米那就更是不值一提了。全世界都恐慌的艾滋病,为什么在非洲却排不上号?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艾滋病感染率曾高得吓人。 博茨瓦纳最严重时全国四成人带病毒,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患者。 但奇怪的是当地人不太怕这病,卡车司机奥德彪的说法很实在: "埃博拉两天要命,疟疾发烧一天就死,霍乱拉稀半天脱水成干尸。艾滋?医生说能活十年!" 他拍着方向盘大笑: "我这破车都开不了十年!" 华盛顿大学教授马丁娜·莫里斯的研究揭开关键。 她比较乌干达、美国和泰国发现,非洲人性伴侣数量不算最多,泰国65%男性有十个以上伴侣。 差别在于非洲人习惯长期维持多个性关系,泰国人找女人多是一夜情。 好比煮汤,泰国是冷水锅放肉片,烫一下就捞;非洲是文火慢炖,病毒有足够时间熬进骨汤里。 基因研究更揪心。 黑人CCR5基因变异率仅1.6%,白人10%,俄罗斯人12%。 这基因好比身体防盗门,变异了艾滋病毒就撬不开锁。 中国人更惨,1300人里只有3人有变异基因,比黑人还易感。 北京实验室的小刘做检测时手抖: "难怪我国感染者十年翻十倍。" 但非洲人淡定有原因。 刚果金某村庄,酋长掰着手指算:去年寨卡病毒带走七个壮劳力,今年麻疹收走五个娃。 艾滋? "那病走得慢,患者还能下地种木薯。" 最绝是南非贫民窟诊所,医生把抗艾药和止泻药放同个货架: "腹泻死得快,药摆前面。" 不过,近些年来,非洲国家也在为遏制艾滋的传播而努力。 乌干达政府把安全套广告印在香蕉上——香蕉是主食,每人每天必剥两三根。 卡车休息站配发夜光安全套,司机们当新奇玩具抢着用。 十年间感染率从30%降到6%。 首都坎帕拉的性工作者有句行话: "客人要'亮灯服务',得加钱。" 亮灯就是指用荧光套。 卢旺达的招数更硬核。 政府给每村配发检测仪,结婚登记前强制双检。 教堂婚礼新增环节:牧师捧圣经,新人举阴性报告。 有小伙检测阳性哭晕,未婚妻抽他耳光: "哭啥!领药去!" 现在当地抗病毒药覆盖率98%,比手机信号覆盖率还高。 非洲抗疫也有黑色幽默。 尼日利亚某部落发明"艾滋神判法":嫌疑人喝猴面包树汁,呕吐算有罪。 后来发现树汁含强催吐剂,艾滋病人免疫力低更易吐。 误打误撞倒揪出些患者。学 者哭笑不得: "这比检测仪便宜,但冤死几个疟疾病人。" 刚果河的驳船上有群特殊乘客。 每早六点,艾滋患者排队领药,药盒印着彩虹条纹。 老药师阿卜杜勒总唠叨: "红白胶囊早上吃,蓝黄药片晚饭后。" 有回暴雨断药三天,病人自己分药——重症让药给轻症,孕妇药量分给儿童。 船医发现时哭出声: "这群'等死的人'比政客懂团结!" 如今非洲抗艾有新难题。 欧美机构撤资后,肯尼亚改用国产药,药片大如指甲盖,患者戏称"吞瓦片"。 津巴布韦更绝,把药磨粉掺玉米粥里。 最无奈是南苏丹,战乱中断药品运输,医护人员教患者采草药: "虽然治不好病,但能止腹泻——别没被艾滋带走,先让痢疾送走!" 雨季的非洲村落常看奇景:老人坐门前剥抗艾药板,铝箔亮片挂满屋檐。 问就说"驱鸟"——其实是提醒子孙按时吃药。 阳光照射时,整个村子银光闪闪,像落下片片不会融化的雪花。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艾滋病在非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