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有10磅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因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无法成活!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27年4月,邓颖超刚从手术台上被转出不久,医院的走廊外便传来沉重的脚步声,孩子出生了,却未能活下来。 邓颖超的第一个孩子在出生不到半小时后停止了心跳,婴儿头部因助产器械造成严重损伤,医生确认抢救无效。 护士将裹好的婴儿悄悄带走,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个孩子连名字都没来得及拥有,便从人世间消失了,这次分娩是邓颖超与周总理共同人生中最沉重的一页。 当时的广州局势混乱,战争阴影笼罩城市,医疗资源极度短缺,医院内缺乏手术设备,医护人员经验有限,面对巨大儿的生产情况,医生无力安排剖腹产手术,只能选择使用产钳助产。 这种助产方式在当时被广泛使用,是在产程受阻时不得已的选择,医生本希望通过产钳协助分娩,尽快结束邓颖超长时间的宫缩,但因胎儿体重异常,达十磅以上,操作过程出现了难以控制的创伤。 孩子的头部在产钳夹持下遭到严重拉伤,颅骨错位,出生后呼吸微弱,几分钟内心跳消失,医生进行了基础急救,但根本无力回天。 在孩子去世后,医院立即为邓颖超进行产后检查,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之长时间高强度的子宫收缩和产道撕裂,使她的身体遭受重创。 检查结果显示,邓颖超的子宫肌层薄弱,部分血管失去弹性,医生判断再次怀孕将极具风险,可能造成大出血甚至威胁生命。 面对孩子夭折、妻子受伤的现实,周总理沉默不语,紧盯着医生的每一句话,确认邓颖超脱离生命危险之后,周总理开始安排静养并暂停了邓颖超原定的工作任务。 这一切并未向外界公开,除了个别亲属和身边最亲近的同志,几乎无人知晓邓颖超失去了孩子,也无人知道她从此失去了再次做母亲的可能。 几个月后,周家亲属陆续知情,在一次家族聚会后,有人向周总理提出,希望他和邓颖超可以过继一个侄子为养子。 理由很简单,家中其他孩子多,周总理夫妇一无子嗣,抚养一个亲戚的孩子既能继承香火,又能填补情感空缺。 邓颖超认真听完每一位亲属的提议,婉拒所有过继安排,她认为孩子不应成为他人悲伤的替代,那些孩子各有家庭,不该因为自己失去孩子而被迫更换生活轨迹。 每一个孩子都应留在原生家庭中成长,而不是为了满足成人的情感需要而成为“安排”,周总理也没有表示任何接受的意愿。 他在私下里向亲属明确说明,不会为家庭建立完整结构而领养孩子,在他看来这种行为对孩子并不公平,对其他未被选中的孩子也可能造成心理落差,他不想在家族内部制造对比和分裂。 于是,原本准备好的过继安排全部搁置,那些孩子继续在各自家庭中成长,而邓颖超与周总理则坚定地维持无子无女的家庭状态。 尽管如此,邓颖超并未与孩子们疏远,在延安时期,大量青年被派往各地培训或执行任务,留下的子女常年无人照料。 邓颖超在不担任要职期间,主动承担起照顾这些孩子的责任,她负责饮食起居、身体检查、教育辅导,甚至连衣物缝补都亲自操作。 这些孩子未曾叫她母亲,但与她的联系从未中断,邓颖超一视同仁地照顾每一个孩子,从不偏向,也从不居功,在她的安排下,许多孩子健康成长,后来分赴各地继续参与建设工作。 周总理亦在各项事务中,不忘为这些孩子安排教育、户籍和医疗,他和邓颖超把原本只属于一位孩子的关怀,扩展到几十位干部子女、家属后代,以及他们在延安时期领养过的难民孤儿。 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家庭私情干扰公事,也让每一位曾受到照顾的孩子都能保有尊严,周总理与邓颖超没有生育,却以行动建立起一个更广泛的“家庭”。 这个家庭不靠血缘维系,而靠责任与担当,多年以后,那些曾被提议过继的孩子长大成人,他们当中有人成为工程师,有人成为医生,有人成为学者。 每当谈起童年时光,他们都记得在北京、延安或者重庆曾短暂生活在“邓大姐”的身边,有人记得深夜发烧时被她抱着赶往卫生所,也有人记得冬天吃饭时她为大家加菜。 虽然没有正式过继,也没有亲生血缘,但他们始终将周总理和邓颖超视作亲人,邓颖超从未用母亲的身份标榜自己,却完成了超越家庭范围的“母职”。 而这一切正是从1927年那个未能存活的婴儿开始,缓慢却坚定地延展开来的,周总理与邓颖超选择了不再尝试、不再代替、不再填补,而是去创造。 他们没有孩子,却让无数人因他们的存在而受益,这种爱没有界限,也不依赖身份,它是一种选择,一种永不动摇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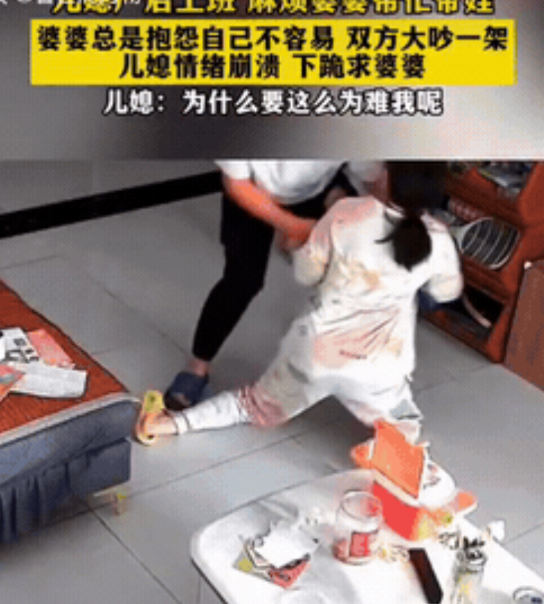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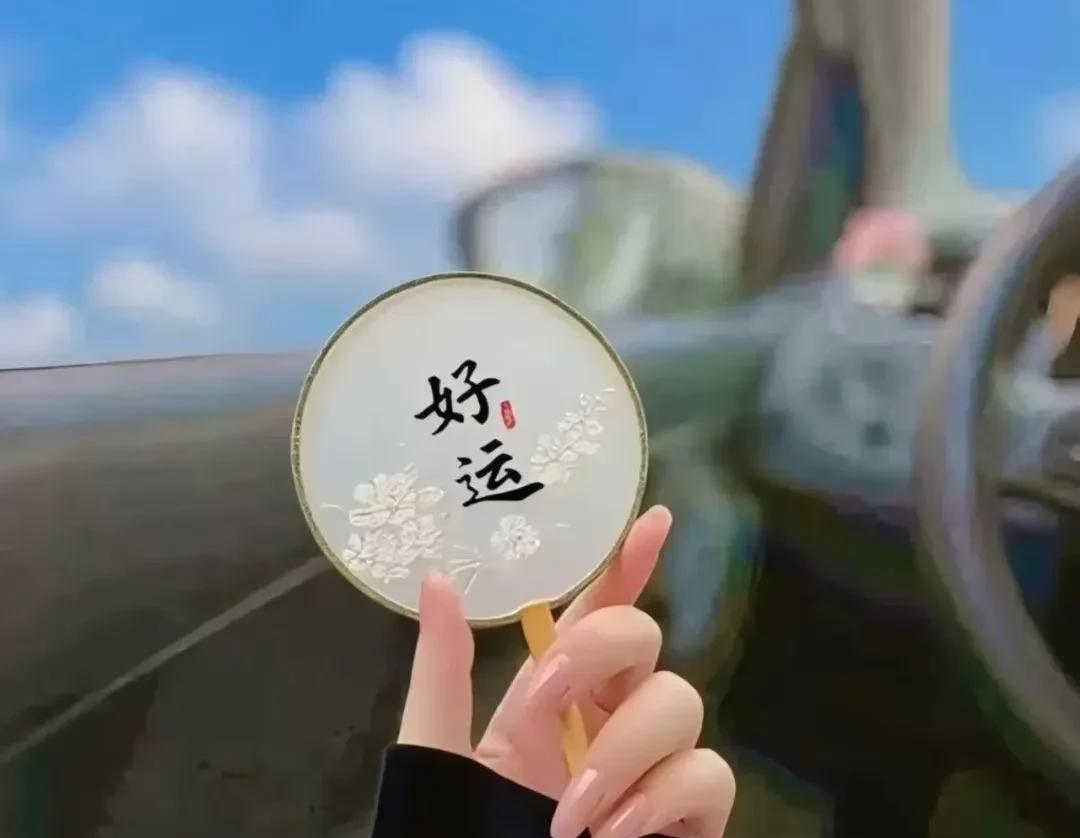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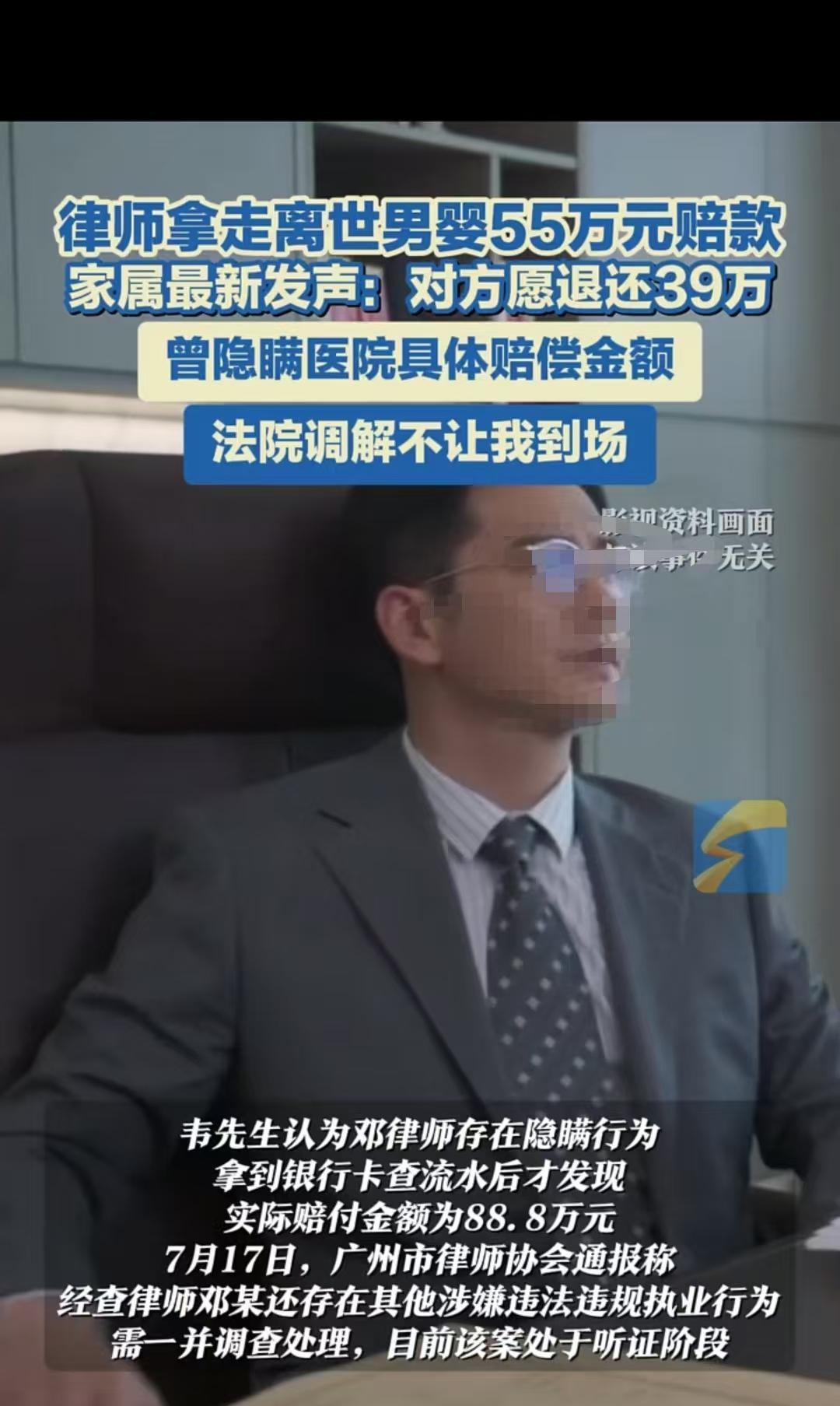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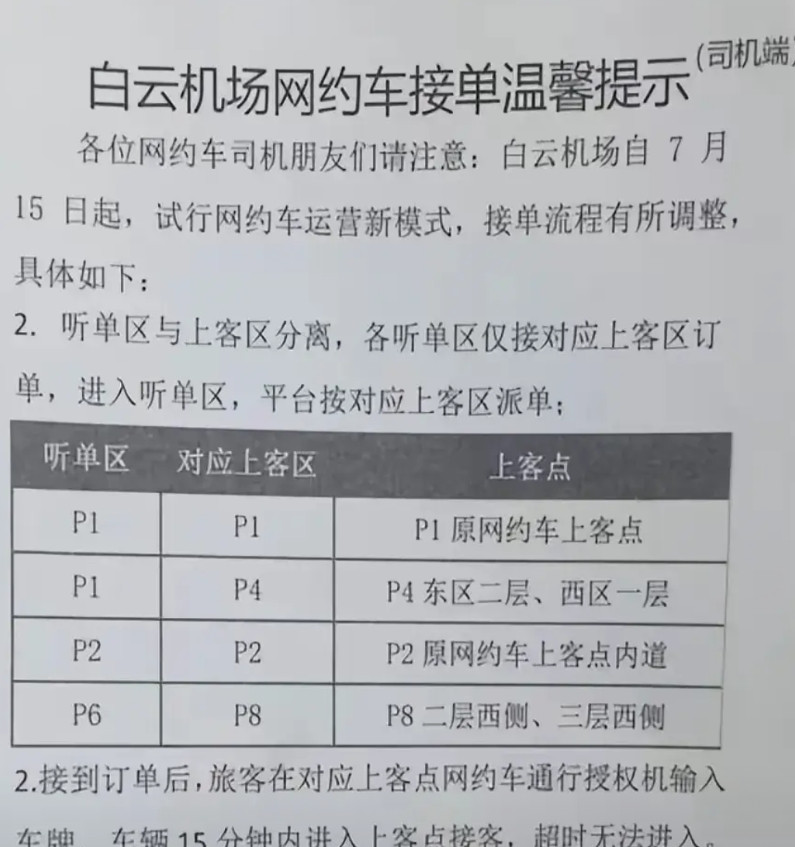
![我感觉现在人都太难了[哭哭]我家房子租给了40多岁的中年夫妇,男的在工地上当](http://image.uczzd.cn/1436235186180198233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