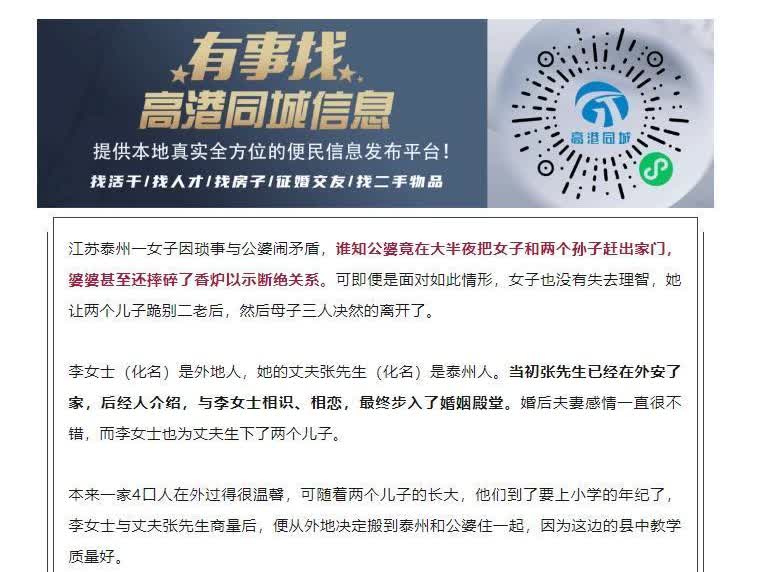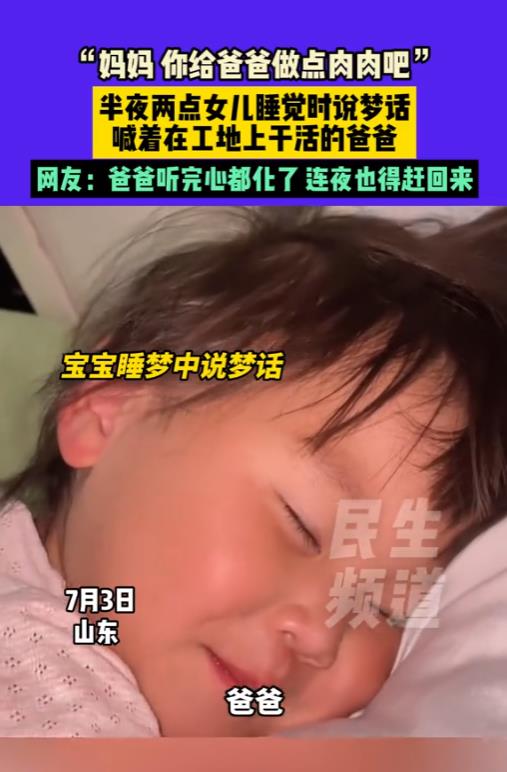昨天晚上远嫁外地26年的妹妹打电话问老家拆迁房能不能给她一套,想让外甥来江苏发展,让我和她嫂子商量一下。 挂了电话让我想起很多. 1998年夏天,18岁的妹妹高中毕业去苏州一家电子厂打工,第二年她和一个外地的男孩谈起恋爱。 父亲知道后对妹妹说:闺女,我就你这一个女儿,我不希望你远嫁! 娘也抹着眼泪劝:“隔壁村老李家闺女嫁去东北,十年才回来两趟,你要是走那么远,妈想你了可咋办?”可妹妹铁了心,婚礼那天,她穿着红嫁衣跪在父母跟前,额头磕在青砖地上发出闷响:“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一定接你们过去享福。” 后来的日子,妹妹确实寄回过不少钱。她在电话里说开了服装店,说买了新房子,可每次父母想去看看,都被她以“店里忙”推脱。直到父亲突发脑梗,我们连夜打电话,她才带着女婿孩子赶回来。飞机落地时,父亲已经闭上了眼。灵堂前,妹妹抱着遗像哭得撕心裂肺,白发的娘颤巍巍地拍着她的背,倒像是在安慰孩子。 从那以后,妹妹回来的次数更少了。有时过年视频,她身后是热热闹闹的年夜饭,我们这边,娘守着冷掉的饺子,对着屏幕笑:“别惦记家里,你在那边好好过日子。”挂断电话,老人偷偷抹眼泪,却把妹妹寄来的丝巾围巾全锁在樟木箱里,一条都舍不得戴。 如今老家的老房子要拆了,开发商给了三套房。我和妻子商量时,她把存折往桌上一拍:“当年咱盖新房,妹夫二话不说借了五万块。现在孩子想来这边发展,咱能帮就帮!”可儿子不乐意了:“凭啥给姑姑?她这么多年对这个家有啥贡献?”这话像根刺扎进我心里——去年娘摔断腿,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妹妹确实一次都没回来。 正纠结时,快递员送来了个包裹。打开一看,全是娘爱吃的桂花糕,还有封信。妹妹在信里说:“哥,这些年我总想着混出个人样再回来,结果越混越没脸。去年妈生病,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买好了机票又退掉——我不敢面对妈失望的眼神。现在孩子想回咱老家那边发展,其实是我想回家了......”字迹晕染开来,看得出写的时候落了不少泪。 妻子看完信,默默收拾出客房:“把最大那套房给妹吧,咱娘俩住一套,给儿子留一套当婚房。”我给妹妹回电话时,她在那头哭得说不出话,倒是外甥接过电话,声音清亮:“舅舅,我学的是建筑专业,听说老家在搞开发,正好能派上用场!等我安顿好了,就把我妈和姥姥都接过去!” 拆迁那天,挖掘机推倒老墙的瞬间,我在碎砖里翻出个铁皮盒。打开一看,是妹妹高中时的奖状,还有张泛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等我赚钱了,给哥买辆摩托车,给娘买新衣裳!”泪水啪嗒掉在纸上,模糊了当年那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的字迹。 如今,妹妹的新家就在我家隔壁小区。她每天早上都会来给娘送热乎的豆浆,外甥跟着工程队忙前忙后,晒得黝黑。偶尔路过拆迁前的老巷子,还能听见老邻居们唠嗑:“老李家闺女真是没白疼,不仅给老母亲养老,还带着孩子建设家乡!”这时,妹妹就会挽着娘的胳膊,笑得眼睛弯弯,像极了当年那个偷偷往我书包塞糖果的小丫头。有些亲情,或许会被距离暂时搁浅,但只要根还在,就总会在某个春天,重新抽出嫩绿的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