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关于莫言与浩然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张沛教授曾感叹:"浩然写的《金光大道》,太阳底下连个阴影都没有,那叫文学吗?那是宣传画!而莫言《蛙》里写接生婆手上沾血,这才是活生生的人间。"对此有人提出反对:"莫言获诺奖是因故意讨好、献媚、贿赂西方世界的结果,他的《生死疲劳》、《蛙》、《檀香刑》等长篇中暴露的是丑的一面,而这正符合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所以这些作品是专门为诺贝尔文学奖炮制的。 对这种看法,复旦教授栾梅健在读书会上举着《檀香刑》打比方:"你们见过乡下杀年猪没?屠夫越讲究手法,看客越觉得血腥。莫言就是把这种千年传下来的残酷仪式,掰开了揉碎了给你看。"他翻开书里刽子手的段落,"德国人看这个觉得猎奇,我们看这是老祖宗的手艺活,谁说作家非得给老家贴金?" 莫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作品总是扎根于现实土壤,又以超脱的视角审视民族与时代。在《蛙》这部小说中,他将笔触深入到人性的褶皱里,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勾勒出发展进程中的复杂图景。莫言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矛盾,并通过“姑姑”这一形象,将这种矛盾具象化,让读者在故事中感受到时代的重量和个体的挣扎。 “姑姑”是《蛙》中的灵魂人物,她的形象复杂而多面,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在故事开篇,她是一个充满圣洁光辉的“送子观音”。1953年至1957年,国家处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时期,人们生活富足,心情愉悦,妇女们争先恐后地怀孕、生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姑姑”作为一名接生员,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黄金时代。 她阶级观念虽强,但在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的那一刻,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沉浸在一种纯洁、纯粹的人的感情中。她开朗、情感充沛、嫉恶如仇、珍惜生命,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让她感受到生命的奇迹和伟大。她用自己的双手迎接了无数个新生命的到来,成为了乡亲们心中的守护神。 然而,命运的转折总是来得猝不及防。时代的浪潮席卷而来,她的想法也逐渐改变,她认为“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压扁啦。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为全人类做贡献。”这种思想的转变,既有时代因素的影响,也有她个人经历的烙印。她从一个充满爱心的接生员,变成了一个铁面无私的执行者,亲手断送了无数孩子以及母亲的生命。 除了《蛙》,莫言在短篇小说《弃婴》《爆炸》中,也塑造了类似于“姑姑”的形象。在《弃婴》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因为生活的困境,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遗弃。这个母亲在遗弃孩子的过程中,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无奈。她既想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又无力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种矛盾和挣扎,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困境。 这些作品中的形象,虽然着墨不多,但却都展现了在时代背景下,人性的复杂和无奈。他们既是生命的守护者,又因为各种原因“沾满了血污”;他们既有道骨仙风的一面,又有铁面无情的一面。这些形象何尝不是各行各业人物的写照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挣扎,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找平衡。 莫言“把自己当做罪人”来写的态度,体现了他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他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评判历史,而是以一种平和、客观的态度去审视那个时代。他让我们明白,历史是由无数个个体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有自己的无奈和挣扎。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评判历史,而应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尊重生命,尊重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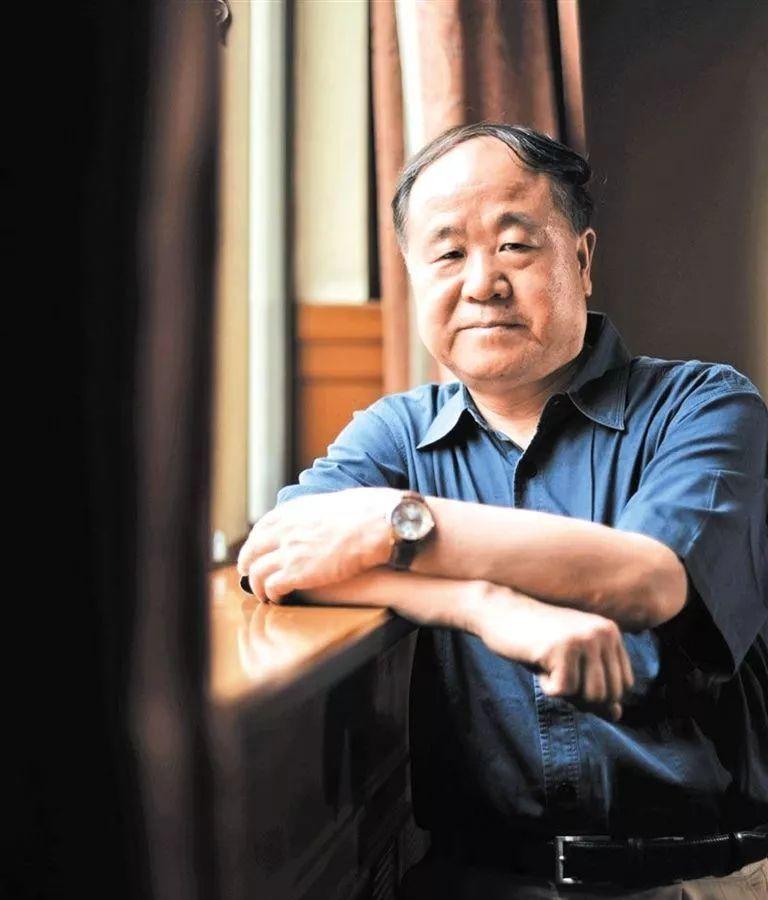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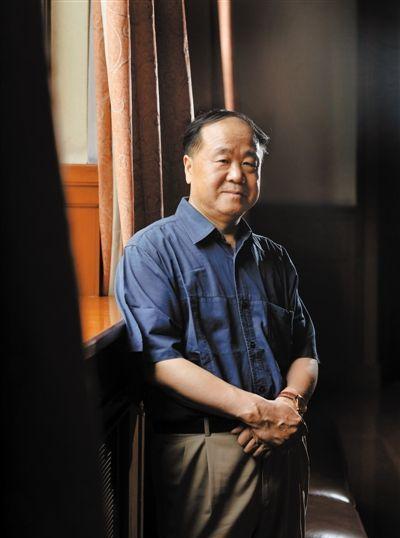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