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某药企王牌女销售,因拒绝从常州跨市调往南京并接受70%薪资暴降,竟被公司连环设局:先以“考勤违规”单方解雇,再派人事冒充猎头电话钓鱼!通话中,女销售为求职优化工作经历,反被公司断章取义指控“兼职”。两次解雇通知均未依法通知工会。女销售认为公司不厚道,遂诉诸法律。在诉讼阶段,女销售揭露公司调岗无凭无据、猎头通话系欺诈取证!经过审理,法院这样判决。此案撕开职场“软暴力”遮羞布——当调岗成变相裁员,当猎头是陷阱伪装,劳动者如何破局?司法亮剑给出答案!
(案例来源:齐鲁壹点)
陈晓芸(化名)是某知名药企资深销售代表,在常州及宜兴地区深耕医药推广工作长达六年。
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她的月薪始终稳定在万元以上,是团队中的核心骨干。
2023年12月,公司突然以"业绩不达标"为由,单方面将其岗位从大客户经理调整为零售经理,并要求其从常州调至南京总部报到,薪资骤降至3000余元。
面对这一决定,陈晓芸提出异议,强调公司从未提供其业绩不达标的书面证据,且调岗后需跨市通勤将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陈晓芸的丈夫和子女均定居常州)。
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她选择继续留在常州原岗位工作。
同年12月26日,公司以陈晓芸"未按新岗位报到、违反考勤制度"为由发出首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令人意外的是,2024年1月,公司再次追加第二份解除通知。第二份通知的解除理由更为离奇——称陈晓芸存在"兼职行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而这一指控的"证据",竟源于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公司人力资源部员工冒充猎头公司人员,以提供高薪职位为由诱导陈晓芸描述工作经历。
通话中,陈晓芸为争取机会对过往经历稍加润色,却被公司截取录音作为"兼职实证"。
事后,陈晓芸越想越气,认为被公司“套路”,遂申请了劳动仲裁,但结果并不如意,无奈,只能诉诸法院。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首先,公司单方调岗降薪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变更劳动合同。司法实践中,企业虽享有一定自主管理权,但调岗行为需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协商性三原则。
本案中,企业主张依据合同约定调整岗位,但公司以“业绩不达标”为由调岗,却未提供绩效考核标准、历史数据或书面评估结果,无法证明调岗的必要性。若企业仅以主观判断或模糊理由调整岗位,可能构成权利滥用。
而且,跨市调岗直接改变了劳动者的通勤成本、家庭生活安排等基本权益。在司法实践中,跨市调动需证明“生产经营必需”或“客观情况重大变化”,且需提供交通、住宿等必要补偿。本案企业既未证明业务必要性,也未提供补偿方案,显失公平。
此外,企业单方将月薪从万元降至3000元,降幅达70%,远超合理范围。若无法证明新岗位薪资标准的合理性(如行业平均水平、企业内部同岗薪资),则可能被认定为变相逼迫劳动者离职,属于“实质性解除”的隐蔽手段。
其次,公司以"兼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据是否合法有效?
公司以“兼职”为由解除合同的核心证据,是其人力资源人员冒充猎头诱导陈晓芸陈述的工作经历录音。
虽然民事诉讼未明确禁止“陷阱取证”,但《民法典》第七条将诚信原则列为民事活动基本原则。
企业通过虚构第三方身份、诱导劳动者作出特定陈述,已构成对劳动者知情权的欺诈,违背公序良俗。此类证据因取证手段违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十七条,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陈晓芸在通话中“美化工作经历”属于求职中的常见行为,与“实际从事兼职”无必然联系。企业若主张劳动者存在兼职,需举证其同时与其他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或实际从事营利性活动,而非仅凭单次通话片段推断。
企业未提供完整的通话录音或第三方机构鉴定,难以排除剪辑、断章取义的可能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规则,企业作为证据提供方,需对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承担更高证明责任。
同时,两次解除劳动合同的程序是否合规?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事先通知工会。
本案中,企业两次解除均未履行该程序,存在程序瑕疵。
企业辩称“第二次解除系补充证据完善程序”,但程序违法具有独立性,不能通过事后追加通知或重新作出决定消除。即便解除理由成立,未通知工会仍构成违法解除。
最终,法院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构成违法,判决公司自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陈晓芸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具体金额依其工资标准及工作年限计算)。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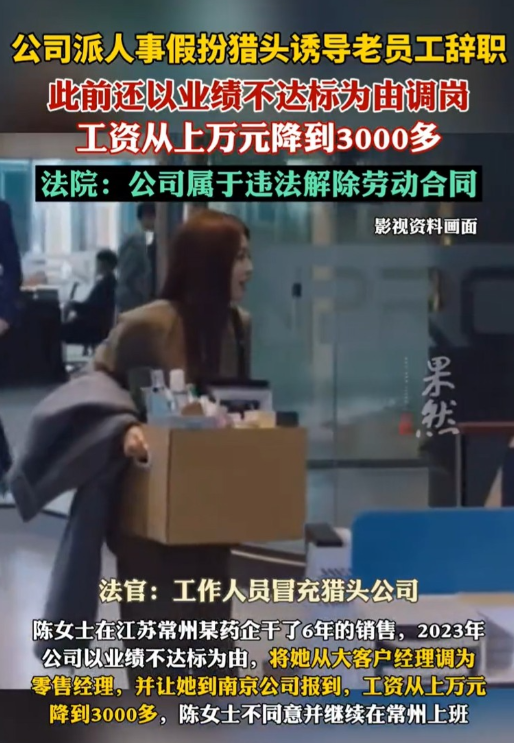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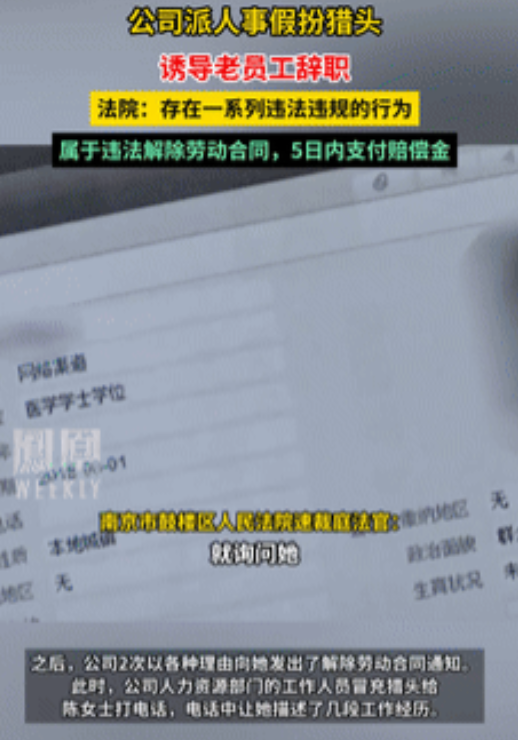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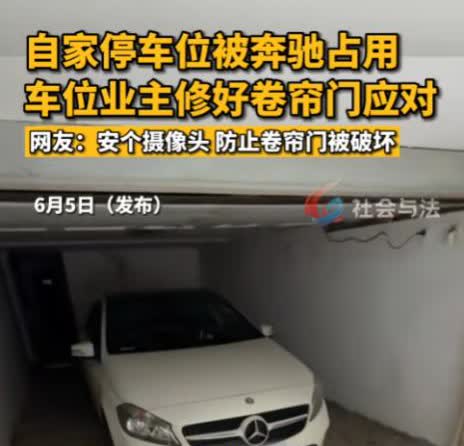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