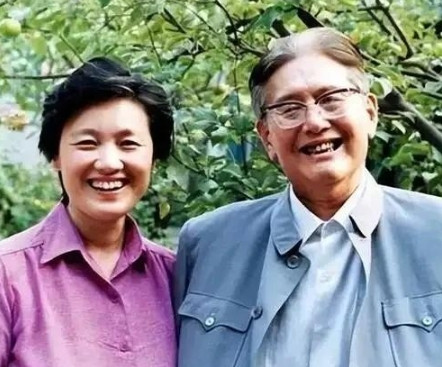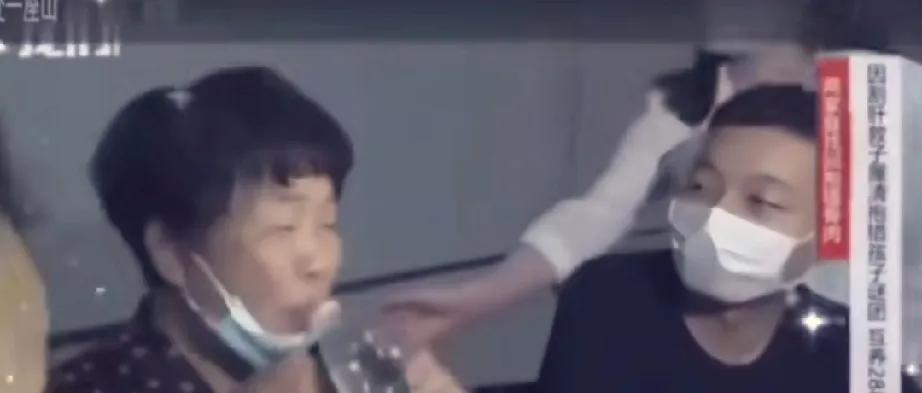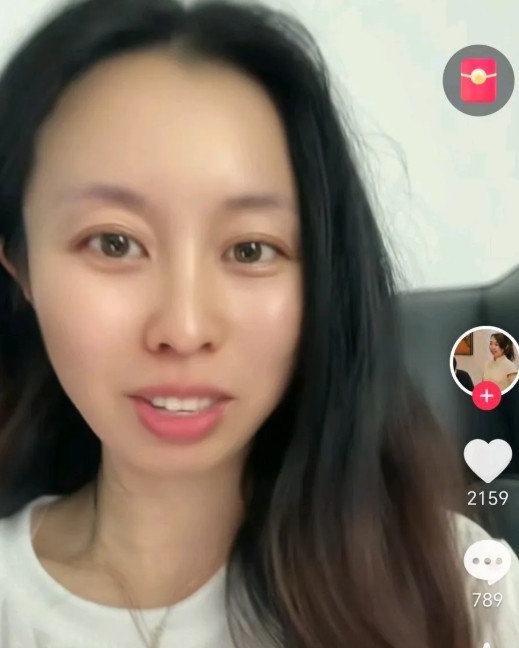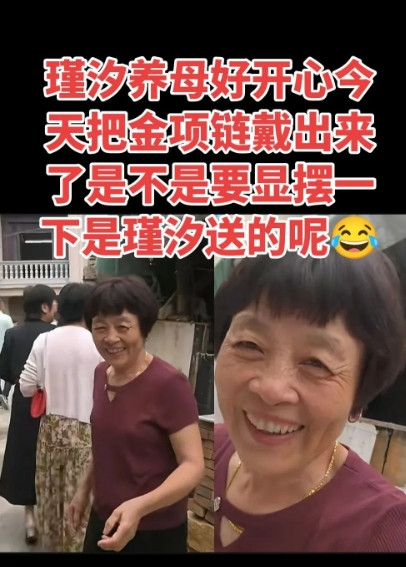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着急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1938年,在天津的混乱中,一对急于逃离战乱的白人夫妇,在一家教会医院迎来了他们的孩子。天津,这座城市在日本侵略军的压迫下,变成了人们争相逃离的地方。街道上,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在寻找离开的机会。
这对夫妇原本计划搭乘次日的飞机回国,但妻子突然临盆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在一阵手忙脚乱后,他们来到了教会医院。经过几小时的艰难生产,一个健康的白胖男婴降生了。医院里,新生儿的啼哭声充满了希望和生机,与外面的混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是,这对夫妇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决定。他们手头紧张,只买了两张机票,无力再为新生的孩子购买第三张。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继续留在中国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危险。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将孩子留在医院,自己逃离。
他们步入了一间昏暗的房间,四周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涂鸦,小床位于房间的角落。床是木制的,涂着淡黄色的油漆,显得既温馨又简陋。床上铺着一张蓝色小被子,上面绣着小动物的图案。他们轻轻将孩子放在床上,小心翼翼地调整他的姿势,确保他舒适。孩子的头发是浅棕色的,睡得很沉,脸上还带着微笑。
夫妻俩开始小心翼翼地将孩子用小被子裹住。他们的动作很温柔,但又透着一种迅速而机械的效率,仿佛是在遵循某种既定的程序。他们用被子把孩子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安详的小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不发一言,只是偶尔交换一个眼神,那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此时,一位护士走了进来,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一个笑脸图案的口罩。她温和地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并询问了一些必要的信息。夫妇俩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摇了摇头,表示他们不需要帮助。当护士问到关于孩子的个人信息时,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国籍,夫妻俩再次对视。这一次,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他们告诉护士,他们不希望留下任何信息,甚至连孩子的国籍也是未知的。
完成这一切后,夫妇俩站起身来,他们的动作显得有些僵硬。他们看了孩子最后一眼,那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痛苦。然后,他们转身离开了房间。走廊里安静,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响。他们穿过医院的大厅,走出了大门。
外面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温暖。他们没有停下来享受这美好的天气,而是直接走向了停车场。他们的车停在那里,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们上车,启动了发动机,车子缓缓驶出了停车场。
一路上,他们几乎没有交谈。车内播放着轻柔的音乐,但似乎谁也没有在听。他们的心思都在别处。车子驶向机场,沿途的风景一闪而过,但他们的心思都在那个小床上安睡的孩子身上。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孩子未来的忧虑,同时也为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痛苦。
时光流逝,那个孩子在新疆成长了几十年。从最初的无助,到逐渐融入这片土地,他经历了许多的变迁。在新疆,他逐渐成长为一名风华正茂的青年,最终成为一位坚韧不拔的中年人。新疆的环境艰苦,他的身体也因为常年的艰难生活而逐渐亮起了警报,无法再坚持在地质勘探的第一线。
国家考虑到他的健康状况和丰富的经验,决定将他安排到教育系统任教,希望他能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新疆的孩子们。他深感这是一份重要的使命,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他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经验整理成大约80万字的讲稿,并在新疆的56个县市进行义务讲课。他的讲课生动有趣,充满热情,深受学生们的喜爱。他向一代又一代的新疆学子们普及着我国的地质环境知识,激发他们对地质学的兴趣。
在新疆,他一待就是50年。尽管有人会因为他的肤色和眼睛而对他有所疑问,他总是微笑着回应:“我是外裔中国人,我永远为生在中国而自豪。”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归属感和自豪。
他的一生,虽然起初伴随着离别和忧虑,但最终成为了一段跨越国界和文化的美丽故事。他在新疆不仅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还获得了广泛的尊重和爱戴。他的经历证明了,无论一个人的起点如何,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对知识的热爱,就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