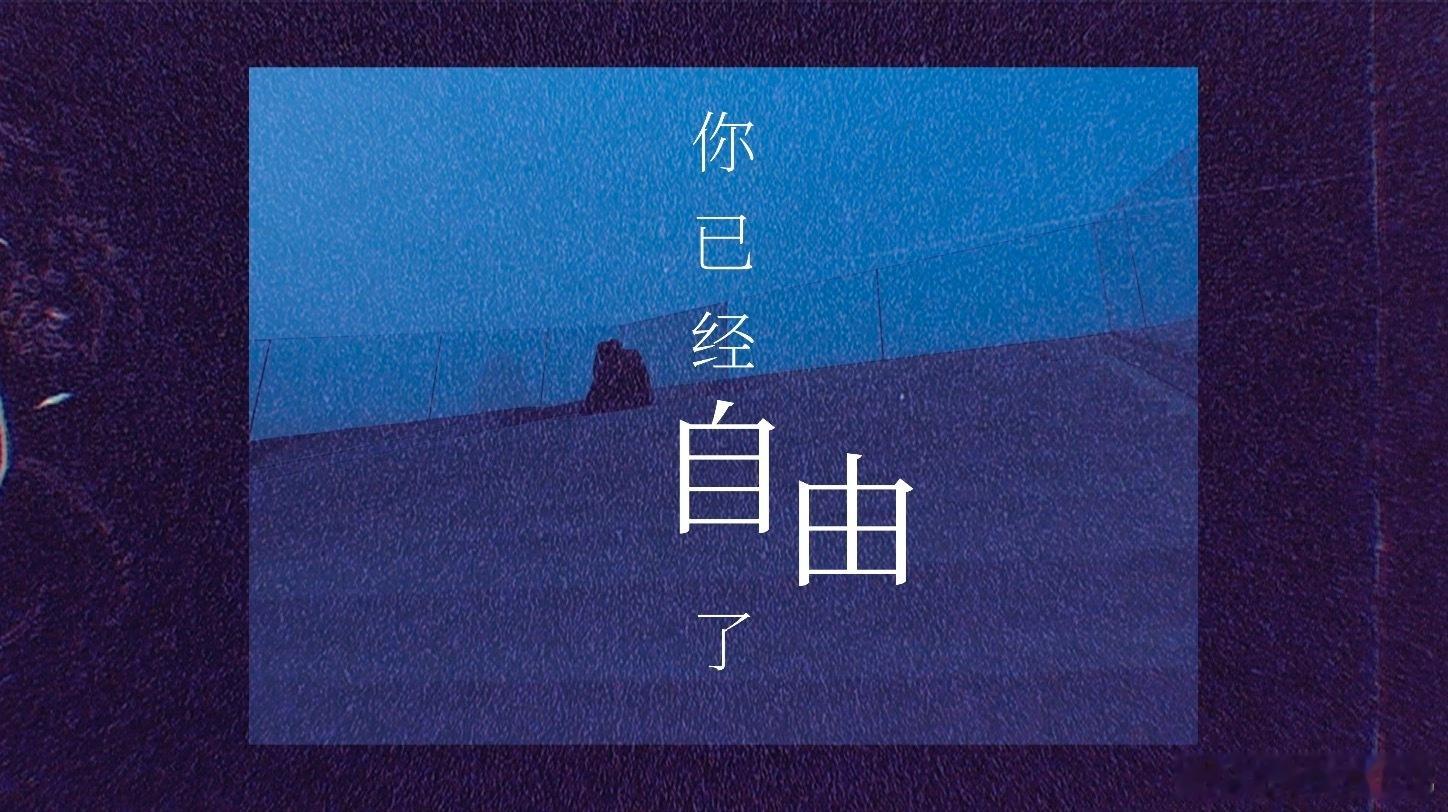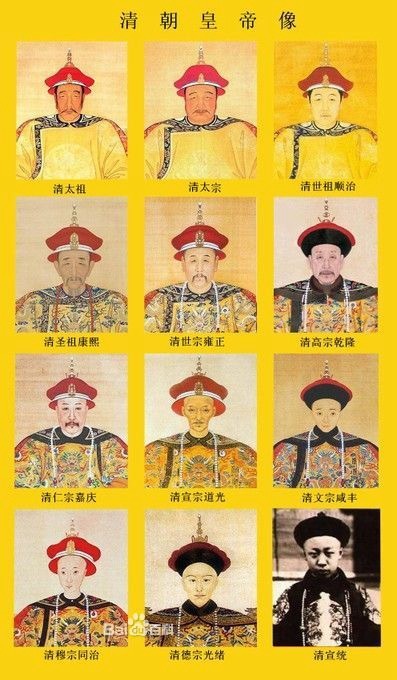1922年,22岁的张幼仪刚生下儿子,就被丈夫徐志摩逼着离婚。床榻上的张幼仪,接过文件,快速签上名字,把文件往地上一扔,冷笑道:“你的目的达到了,可以去找更好的太太了。”徐志摩吃惊得差点没反应过来!
张幼仪,名嘉玢,江苏宝山人,是徐志摩的结发妻子。15岁那年,她“轰轰烈烈”地嫁入徐家,那丰厚的嫁妆惊动了整座城市。可是,她最想依靠的那个人,却给了她一个冰冷的新婚之夜。
徐志摩不看她,也不对她微笑,甚至不和她说话。此后,他对她说的第一番话,竟然是“我要成为中国文明离婚第一人”。
她看他的眼神有些懵懂,在张幼仪的意识里,结婚了就是结婚了,是不可以离婚的。可是对徐志摩而言,结婚不过是完成父母交代的任务。
婚后不久,徐志摩便去上学,他们结婚3年,相处的时间加起来却不到4个月。在徐志摩眼中,张幼仪是空气一般的存在,他给予她最大的残忍,便是冷漠。
没有灵魂的碰撞,只有传宗接代的使命!1918年,张幼仪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徐积锴。于徐志摩来说,他并没有成为人父的喜悦,只有完成任务后的松一口气,徐家有了后代,他便终于可以过自己的潇洒人生。
徐志摩迫不及待地离家求学。1921年,徐志摩来到剑桥大学,也就是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个叫林徽因的女子。张幼仪的人生悲剧,从这里被推上了高潮。
徐志摩出国之后,张幼仪独自承担起操持家务、教育孩子、孝顺老人的重任。她事事仔细,处处小心,无半点差池,在徐家二老心中,只有张幼仪是他们最认可的儿媳。
离开了家的徐志摩,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纵情寻找所谓的浪漫和自由。他的风流韵事,终于传到父母耳中。为了不让儿子在国外胡来,他们决定把张幼仪送去国外,看住徐志摩。
他们原本是好意,不愿让一对夫妻分隔两地。可正是这次好心的安排,加速了他们婚姻的毁灭。夫妻重逢,徐志摩连嘘寒问暖都省却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写满了他的嫌恶。
在这样压抑的生活里,张幼仪竟然再度怀孕了。当时的徐志摩正热烈地追求林徽因,得知妻子再度怀孕,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黑着脸让她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有些委屈:“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而死掉。”徐志摩冷冰冰地回答:“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她还没来得及思考,徐志摩便一走了之。人生陷入绝境之时,她能想到的只有自己的亲人。于是,张幼仪写信向二哥求救,在二哥的帮助下,张幼仪辗转来到柏林,在万般悲苦中生下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孩子的出生,依然没能换来徐志摩的笑脸。于他来说,妻子和孩子,都是拖累他追求浪漫和爱情的包袱。还在医院里的张幼仪等来的不是丈夫的安慰,而是一纸离婚协议。
她同意离婚,唯一的条件是先告知父母一声。徐志摩却急不可耐,仿佛离婚已经刻不容缓,他说:“不行,不行,我没时间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张幼仪第一次用专注的眼神盯着徐志摩看了许久,看得他头皮发麻。她最终还是毅然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并且平静地说:“给你自由,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纵然是弃妇,也要做个好母亲。这是张幼仪对自己的警告。她在婚姻中吃了没文化的亏,于是决定留在柏林求学,她给公公写信,表达了自己求学的意愿,希望徐家能够出钱资助。
徐父是明理之人,很快给张幼仪回信:“儿子可以不要,贤媳不可不留。吾之家,即汝之家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徐父对儿媳张幼仪的关爱。
从一段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她活出了最昂扬的姿态。
上天或许是为了考验张幼仪的勇气,让一场生离死别兜头砸下。3岁的儿子因腹膜炎在柏林夭折,她拼尽全力想要做一个好母亲,残酷的命运却偏偏不给她这个机会。
她又变成了孤身一人,没有了儿子,异国便再无值得留恋之处。回国去吧,纵然那片土地有太多伤感,可那毕竟是故乡。
张幼仪回国后,她的世界豁然开朗,向来朴素惯了的人,突然有了打扮自己的欲望。从一件旗袍开始,张幼仪引领了时尚。她决定开一家服装公司,专门为女性量身定制高档旗袍。
李白有句诗叫“云想衣裳花想容”,她的时装公司便叫“云裳时装”。
没有了婚姻,反而获得了新生。张幼仪把时装公司开在上海,这是她天生的商业眼光。当时的上海,刚刚兴起旗袍之风,在云裳公司之前,还从未有过量身定制旗袍的时装公司。一时间,上海的大街上,凡是时髦女子,身上都穿着“云裳时装”的衣服。
整整30年,她忙着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爱情,被她轻轻关在了门外。
直到1953年,张幼仪才重新打开尘封的心门,一位名叫苏纪之的医生,住进了她的心里。与当年那场盛大的婚礼相比,张幼仪和苏纪之的婚礼简单至极,却让她感到温暖和幸福。
1988年,88岁的张幼仪因病逝世,她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四个字——“苏张幼仪”。这才是婚姻应有的模样:你给我幸福的余生,我的名字冠你之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