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七月的地铁口像个蒸笼,林小满踩着高跟鞋往阴凉处躲。柏油路上蒸腾的热气扭曲了"巴蜀风味"四个红字,她却在瞥见"豌杂面"三个鎏金小楷时,脚底生了根——那豌字三点水旁晕开些油星,倒像碗里晃着的红油。
玻璃橱窗里坐着口黑陶大瓮,浑圆的豌豆在浓汤里浮沉,表皮绽开的豆肉如絮,金灿灿的汤面浮着猪油花。穿靛蓝围裙的老汉正炒杂酱,铁勺刮过锅底的脆响里,肉末混着郫县豆瓣跳起踢踏舞,辛香混着豆香撞碎冷气帘。

"妹儿要干溜还是汤面?"川音烫着耳朵。林小满盯着价目表上"耙豌豆免费续"的字样,指甲掐进掌心——上个月在城中村吃的豌杂面,豌豆硬得能崩牙。
粗瓷海碗端上桌时,热气糊了镜片。豌豆堆成小山,金黄油润的豆泥从裂缝里淌出来,混着深褐色的杂酱往面底渗。林小满舀起半勺豆子,舌尖抵上去的刹那,瞳孔猛地收缩——这豆子竟比她老家后灶煨的还绵!
"泡足三十六个钟头哩!"老汉敲敲玻璃上的告示。原来这豌豆要经井水三浸三晾,砂锅文火煨到豆皮将破未破,起锅前还得焖在余炭里收汁。难怪豆肉酥而不散,抿在嘴里化成沙,甜津津的豆香里还裹着骨汤的荤。

杂酱是另场盛宴。肥三瘦七的坐墩肉剁成石榴籽大,甜面酱要用资阳老字号,煸出的油汁红亮如落日。林小满挑开酱堆,发现里头藏着碎米芽菜,难怪咸鲜里泛着发酵的酸香。最绝是那勺现舂的糊辣椒——二荆条与灯笼椒在石臼里交缠,粗粝的颗粒感截住油腻,辣得人天灵盖发麻却不烧心。
碱水面卧在碗底,黄澄澄的如龙盘踞。林小满学着邻桌壮汉的架势,筷子从碗底抄起翻搅。面条裹着豆泥与肉酱,麦香混着酱香往鼻孔钻,吸溜入口的刹那,后槽牙咬到粒漏网的豌豆,爆开的豆沙甜竟勾出两汪泪。
加醋时才发现是保宁醋,酸味裹着药香。榨菜粒切得比别家细碎,涪陵产的乌江榨菜,脆生生地截住满嘴荤腥。红油顺着碗沿往下滑,在一次性餐布上晕出个地图轮廓——竟像极了她大巴山老家。

续到第三碗耙豌豆时,老汉摸出搪瓷缸子:"妹儿川娃儿嘛?"林小满的筷子僵在半空。深圳七年,早被同事笑改了口音,此刻却被碗底残存的麻辣劲道破了功。
玻璃柜里泡着的灯笼椒晃啊晃,映出她初来乍到的模样——那会儿在岗厦出租屋煮挂面,偷放母亲塞的辣椒酱,呛得合租姑娘直擂门。后来试过十八家川菜馆,却再寻不到能把豌豆煨成沙的痴人。
末班地铁呼啸而过时,林小满攥着打包的辣椒罐想,明儿该带湖南同事来尝尝——让他们晓得真正的辣不是干呛,是豆沙般绵密的温柔刀。
玻璃门合上的刹那,后厨飘来老汉的川剧高腔:"豌豆耙又烫,乡愁莫得那么长哟..." 霓虹灯牌在夜色里愈发猩红,像极了老家灶膛未熄的火,煨着游子们化不开的馋与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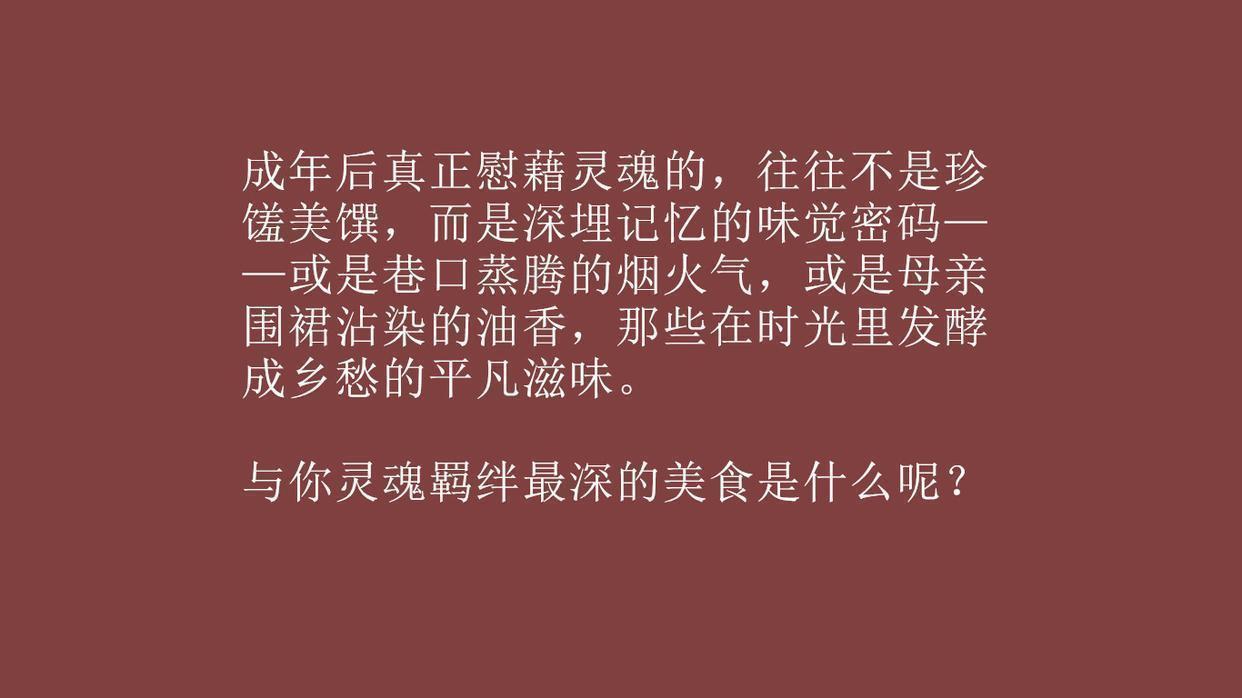
每日一个美食治愈小故事,若这些带着油盐酱醋香的故事曾牵动您的舌尖乡愁,诚邀您点击关注,愿这些故事能给您带来一缕暖光。
最后想厚着脸皮撒个娇~嘤嘤嘤~求鼓励~求关注~求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