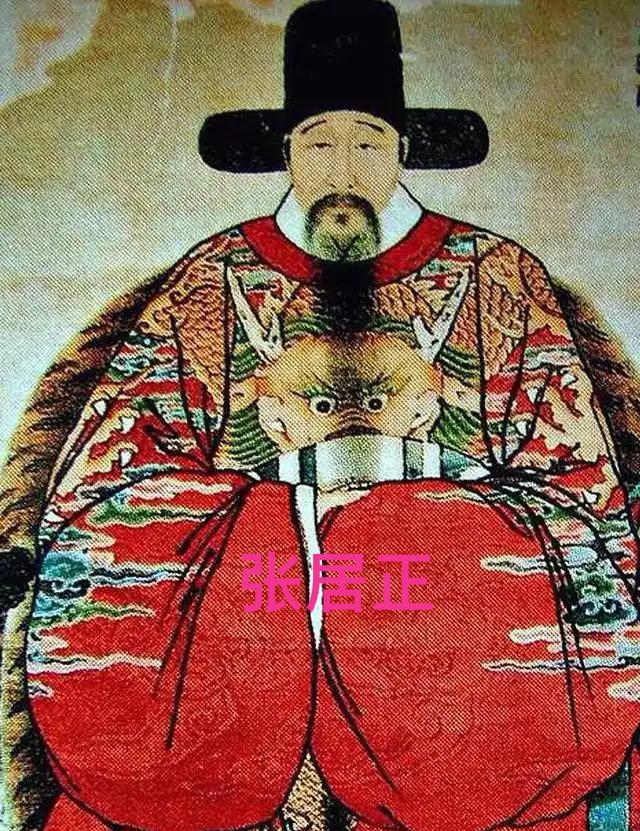1799年,和珅在被处死之前,嘉庆皇帝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贪的钱,能花完吗?谁料和
1799年,和珅在被处死之前,嘉庆皇帝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贪的钱,能花完吗?谁料和珅说了一句话,让皇帝当场愣住。嘉庆皇帝登基后,面对先朝权臣和珅,曾不无犀利地发问:“你贪的钱,能花完吗?”彼时的和珅,早已不是官场新人,他镇定自若,大言不惭地回应:“我贪财是为了在朝堂上好办事,况且这些钱大多花在了乾隆爷身上,”这番对话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汹涌。和珅的人生开局,并不顺遂,他年幼丧母,九岁丧父,身后还跟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十九岁的和珅满怀憧憬参加科考,虽熟读四书五经,甚至精通多语,却仍在竞争激烈的科场名落孙山,谁知,命运关上一扇门,又悄悄开了一扇窗,清朝有官位承袭制度,旨在维护权贵地位,和珅竟因此“因祸得福”,以文生员身份承袭了祖上的三等轻车都尉,这便成了他迈入官场的敲门砖。真正让和珅平步青云,也为日后大肆敛财埋下伏笔的,是轰动一时的李侍尧案,这位身兼大学士和云贵总督的高官因贪腐被揭发,乾隆震怒,随即派员查办,和珅在此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成功搜集了李侍尧及其党羽的罪证,还在案后,将李侍尧等人搜刮的部分巨额财产悄然收入自己囊中,此案告破,和珅不仅因功获赏大量金银珠宝,更重要的是赢得了乾隆的深度信任,一跃成为皇帝跟前的红人。即便知道他中饱私囊,只要不触碰谋反的底线,乾隆多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和珅深谙为官之道,他的“钞能力”此刻发挥到极致,他清楚,要巩固地位,除了博取乾隆欢心,还需在盘根错节的官场打点,而真金白银无疑是最佳通行证,更重要的是,乾隆统治后期,这位曾经励精图治的君主开始沉湎享乐,大兴土木,为彰显功绩数次南巡,就连诞辰也要办得奢侈盛大。每次南巡,不仅要顾及皇帝的吃喝玩乐,还要无数人鞍前马后伺候,这对国库无疑是巨大负担,即便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百姓也难以承受,为了讨好乾隆,和珅甚至包揽了乾隆第五次南巡的全部巨额开销,当乾隆尽兴返回宫中,惊讶地发现国库钱财似乎分毫未动,和珅这种为主分忧的“钞能力”,自然让乾隆对他更加倚重。据说,乾隆晚年因年迈言语不清,旁人多听不懂,唯独和珅总能准确领会其意,这份“知己”般的默契,有时甚至超过了乾隆的亲儿子们,同时,和珅还利用乾隆的信任,将部分人事任免也抓在手中,许多官员为求晋升,不得不贿赂和珅。而和珅也乐于“收钱办事”,在这方面做得十分“到位”,长年累月下来,积累了惊人财富,私下生活奢靡至极,有时穿戴用度甚至比乾隆还要铺张,他还将自己疼爱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嫁给了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使和珅与乾隆之间又多了一层亲家关系,这无疑让和珅的地位更加稳固。然而,乾隆皇帝这份“偏爱如山”,在皇十五子颙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眼中,却是另一番滋味,嘉庆对父亲如此纵容和珅早已心怀不满,他眼看和珅权势滔天,党羽遍布朝野,搜刮的财富比国库还多,心中自然愤懑,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和珅仗着乾隆宠信,屡屡干预朝政,甚至到了妨碍皇权交接的地步。和珅曾不止一次阻止嘉庆帝老师的晋升,更在乾隆帝准备遵循祖父康熙帝在位不超过六十年的承诺退位时,竟建议乾隆不要退位,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都传到嘉庆耳中,让他对和珅的放肆和干政厌恶至极,并发誓有朝一日定要收拾这个权臣。乾隆虽名义上退位为太上皇,但军国大权依旧在握,对嘉庆这位新君更是时常抱有警惕,有意无意试探儿子对自己是否不满,在太上皇乾隆和权臣和珅的双重制约下,嘉庆皇帝更像个徒有虚名的“傀儡”,实权甚至不如和珅这个臣子,眼看自己一步步沦为透明皇帝,嘉庆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而站错队的和珅,自然成了嘉庆的眼中钉、肉中刺。正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乾隆皇帝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和珅这个“二皇帝”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这消息对和珅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他最大的靠山倒了。嘉庆皇帝虽然表面沉浸在丧父之痛中,却并未失去政治上的清醒和果决。他主动将操办乾隆丧葬事宜的权力交给和珅,习惯了为皇帝打点一切的和珅,对此自然求之不得,却未料到这正是嘉庆为他精心布下的陷阱。果然,乾隆驾崩仅十五天后的正月十三,嘉庆皇帝便雷厉风行地动手了,他命人将和珅革职下狱,并迅速罗列其二十大罪状,诸如曾经象征无上荣耀的“紫禁城骑马”、“大内乘轿”等待遇,此刻都成了致其死地的罪证。随后便是抄家,结果震惊朝野,白银高达八亿两,还有难以计数的金元宝、夜明珠及奇珍异宝。这笔财富,据说相当于清政府当时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民间因此流传开一句童谣:“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最终,这位在乾隆朝呼风唤雨的权臣,在狱中接到嘉庆帝赐予的一条白绫,自缢家中,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他毕生聚敛的巨额家产,尽数充入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