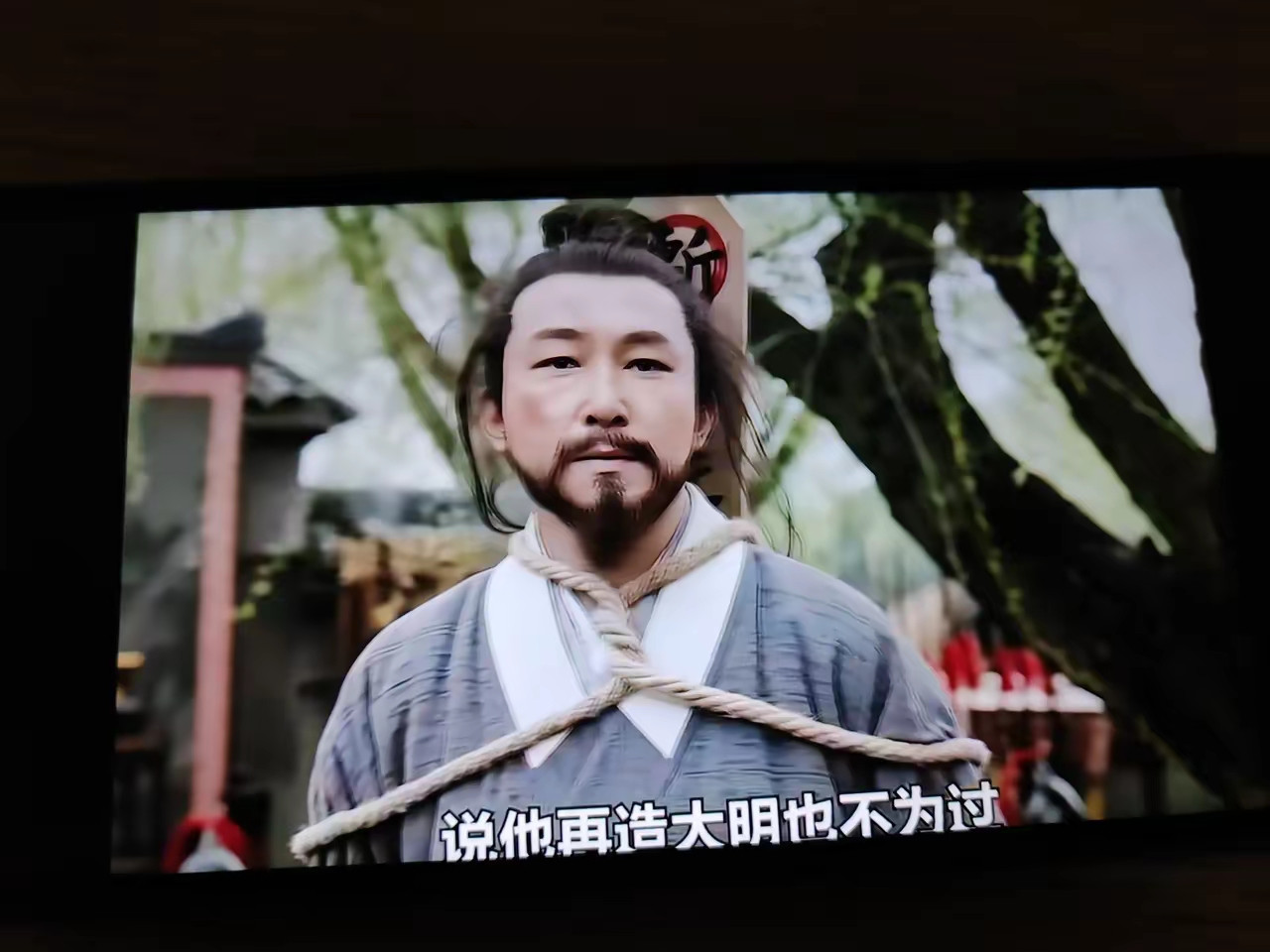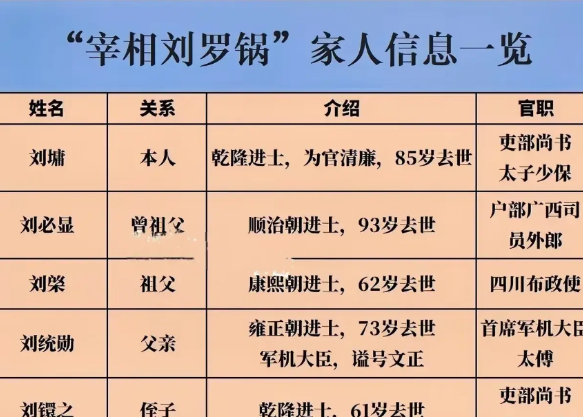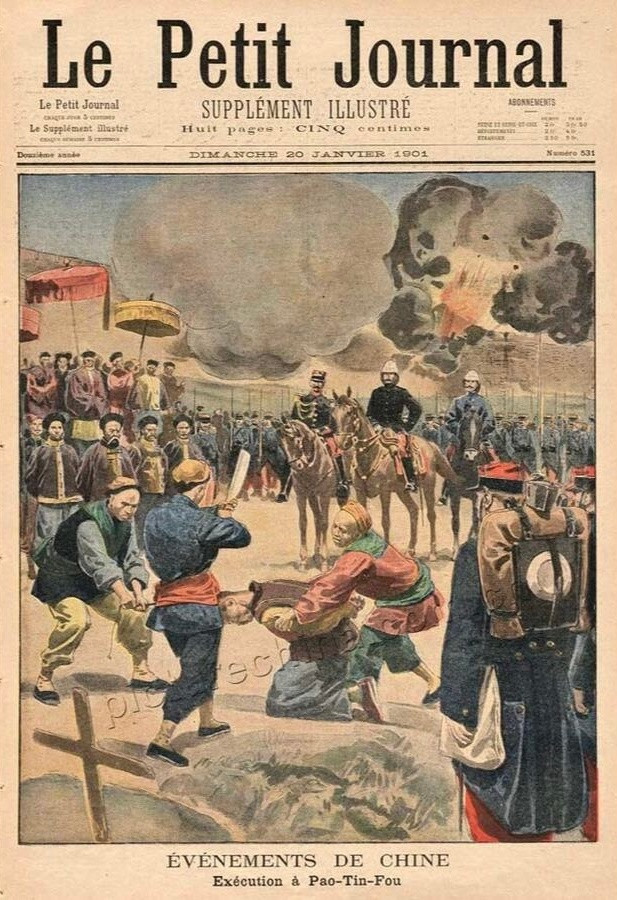清代凡是能问刑的衙门都设有监狱,能问刑的是指县、州、府和省里的按察司衙门,布政司以及督抚衙门则不设监狱。监狱之外,各级衙门有设立了数量更多的班房,所谓的进监狱、蹲班房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有读者对监狱和班房两个概念还不是那么清楚,御史借助相关的文献资料,来讲一讲有关方面的内容。
监狱的设置情况和管理办法《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中对监狱有详细的记载,外省各级衙门一般都设有“内外”两监,内监关押的是“重囚”,特指强盗和斩绞等犯;外监关押的是军流以下之轻犯,内外监之外,还专门设有一室单独关押女犯。
州县衙门关押的犯人一般都是初审时被定为较重的罪犯,如果是笞杖一类的轻微犯罪,则不必关押。不过,不论是州县监狱还是府监狱、臬司监狱,关押的都是未决犯,需要等到秋审后才能正式定罪。

清代对监狱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所有戒具、囚衣、囚粮、医药、亲属探视、监狱修缮、值班查夜,以及警戒、提审等环节,都有按照程序进行。一旦违反条例,相关的官员狱吏就要受到处分。
相对来说班房来说,监狱是在国家规定的条例下执行的,可操作的空间并不大,发生意外事故的概率也比较小。因为一旦事发,就会担责。
比如条例中就明文规定,所有戒具都要按时洗涤,冬设暖床,夏设凉席。犯人每日给米一升,冬给棉衣一件,病了还要给医给药。此外,年龄70以上、15以下的犯人还得分别关押,有病的和没病的也要分开。

对于狱吏们来说,防备罪犯越狱潜逃是重中之重,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故,那么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比如道光八年六月二十一日,浙江武康县监狱流犯李万和、王再兴等四人一同越狱脱逃。
浙江巡抚刘彬马上就上奏弹劾武康县相关官员,建议将武康知县和典史革职,并勒令三个月内缉拿逃犯。后来四个罪犯虽然被顺利拿获,但相关人员还是受到了降级留任的处分。
如果在监狱中发生罪犯无故病死,那么也属于情节严重者,知县和典史等最少也得要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所以说,州县官和狱官对在押的犯人,基本上不会动太多的手脚。
 班房的设置和管理办法
班房的设置和管理办法监狱是用来关押军流以上犯人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类犯人的数量很少。更多的是在刑事诉讼中的轻犯,这些人按照规定是不能收监的,可是鉴于审案的需要,又不得不加以羁縻,班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班房的性质就是州县差役私设的“看守所”。班房原是三班衙役的值房,起初的时候,轻微罪犯就被羁縻在班房,后来因为人数不断增多,且差役从中有油水可捞,便不断扩大规模,到了乾隆中期以后,州县衙门会单独腾出一个地方作为班房。
一个州一个县的班房数量很多,比如道光年间,广东南海县就有班房十七处,顺德县公开的班房就有八处。被临时关进班房的人数多达几百上千人,是入监犯人的十几数十倍。

班房是清代最黑暗的地方,康熙时期著名的循吏黄六鸿就曾说:
“查各府州县于监狱之外更设有班房,其名虽将犯人暂寄公所,实则高墙密禁,扭锁巡防,与监狱丝毫不异。况监中重囚经上司稽查开放,尚有定期,惟在羁禁班房者,操纵全在本官,索诈任于胥役,至有淹系数年,死而后已者。”
就连皇帝也不得不承认班房之弊,康熙帝在上谕中就说:“监犯逾限不行速审,以致狱毙者甚多”;嘉庆帝在上谕中也讲:“州县滥行收押,胥役勒索凌虐,或致人证负屈轻生,无干拖毙。”

被临时关进班房中的犯人生命是得不到保障的,是生还是死完全由财力决定,人犯刚进班房,胥役就会索贿,冠名为“常例钱”。给钱多的就能享受优越的待遇,会被单独安排在一个干净的房间中,或者是拨给一个小院子单独居住。
要是给钱少或是没钱给的,那么处境就很悲惨了,只能住进脏乱差的大通铺,床铺上盖着腐草,且犯人还会带着刑具。
比如道光初年,四川丰都县一个叫陈乐山的人被卷入一场讼案,被充军到安徽太湖县,他在四川、湖北、安徽各省监狱、班房辗转乐十几年,期间据他推算,四川每年死在班房中的人就达到六七千人,安徽也有三四千人,全国一年下来不少于数万人。
各省班房的弊端最高统治者都是清楚的,朝廷也颁布了很多关于狱政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禁令。然而这些法规都是一纸空文,州县官吏从来不会认真理会。

道理很简单,班房的存在让官府和胥役有了生财之道,同时也是欺压百姓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各级官府都是暗中支持班房制度的,究其原因,在于专制权力下的法制和治乱关系本身,就代表着暴力和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