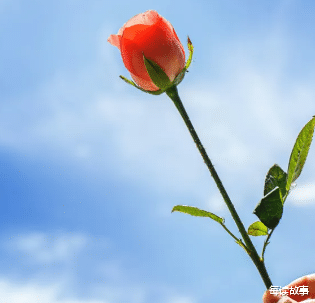我从没在那样亮的灯光下脱过衣服。
硕大的顶灯自上而下将我照得无所遁形,连灵魂仿佛都被烙印上轻贱的意味。
只因为我失手打翻了酒杯,弄脏了富家公子的裤脚,他便这样侮辱我。
众人兴致缺缺,似乎见惯了这样的戏码,但眼中的轻蔑依旧如刀落在我身上。
我攥紧拳头,看向座位正中那人。
邵仲山,正是我今晚的目标。
他捏着酒杯浅浅饮了一口,侧头听旁边人说话,目光却沉沉落在我身上。
看不出喜怒或兴味,同看桌上的果盘没有两样,却始终没有挪开。
角落里有人动了一动,程亦明掏出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烟。
“啪嗒”一声,如同发条钥匙插进了八音盒,旋转两下,便将其上的假人瞬间驱动。
我抿了抿唇,将滑落手腕处的披肩扔在地上,抬手摸上背后的拉链。
抹胸紧身裙是按照我尺寸定制的,量身前我还饿了两天,穿在身上严丝合缝,操作艰难。
时间流逝,众目睽睽,难堪犹如一只大手逐渐扼紧我的喉咙,手指开始发颤。
最后还是邵仲山解救了我,“别在那站着了,过来坐吧。”
此话一出,室内有短暂的寂静。
富家公子面色悻悻,“既然邵总开口了,那我自然没话说,权当被狗咬了。”
他犹自笑着,身侧两人却已然变了脸色,就连程亦明都露出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邵仲山果然顿了一瞬,将酒杯放到桌上,收回手时随意落在了我赤裸的大腿上。
语声平淡,却莫名渗出凛冽寒意,“怎么好让陈公子受损失,自然由我替她赔给你。”
富家公子面色剧变,才意识到邵仲山帮我解围并非是善心大发,而是动了别的心思。
“邵总,我不是……”
邵仲山摆摆手,缓慢站起身,垂眸问我,一副绅士温柔的做派,“要跟我走吗?”
简单一句话,却不只是简单的字面意思。
周围人目光落在我身上,有惊异也有艳羡,却几乎都已笃定了我的回答。
邵仲山是业界龙头邵氏的准继承人,最年轻的掌权者,资本背景雄厚,相貌和能力都拔尖。
向他自荐枕席的人不在少数,但成功者却无一。
不是他多么禁欲清高,而是他心里有位放不下的白月光。
他的皮夹里常年装着一张女生的照片,见过的人寥寥,却传得众所周知。
我猜应该和我长得很像,所以我才能成为最特殊的那一个。
克制住看向程亦明的冲动,我对着邵仲山点点头,站起身挽上他的手臂。
经过拐角时,膝盖不慎撞到桌角,猛地向前摔去,却被人从后扯住了手肘,又迅速放开。
眼前一晃而过的是碎玻璃的尖锐锋芒,转过头却看到程亦明晦暗的眼睛和蜷缩的手指。
邵仲山也跟着我看过去,同程亦明点了点头,带着我离开。
直到被幽凉的夜风吹透半边身子,我才想起自己忘了带走那件披肩。
作为顶级会所,哪怕是服务员的制服也是极精致的,拿去卖或许也能换来一个月的饭钱……
肩上骤然一暖,打断了我纷乱的思绪。
邵仲山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条毯子披在了我肩上,应该是新的,还有淡淡的羊毛味。
我下意识朝他身上看了一眼,听到一声低笑,“你该不会以为我会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你吧?”
“不敢,我没有这么想。”
“没什么不敢的,但是做人不能太蠢,对吧?”
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却只能沉默以对。
任凭他是贪色或者粗暴,我都有信心能应付,偏他是清淡疏离甚至礼貌的,倒让我无从下手。
上车时甚至主动给我开了车门,我看到旁边的司机面色明显一变,在邵仲山报出地址后,看我的眼神瞬间恭敬起来。
我却因此更加紧张,手脚僵硬着不知该如何放,还被突如其来的手机铃音吓了一跳。
邵仲山闭目养神,听到动静后微微点头,“看吧。”
我应了一声,打开手机,是程亦明发来的消息。
“别畏畏缩缩的,他不会喜欢。”
“你刚才为什么要出手扶我,万一被他看出什么端倪来怎么办?”
半晌之后他才回,“怕你毁容。”
“那样倒好了,没有这张脸我便没了用处。”
“那你弟弟便也没了活路。丛芷,说话前最好想想清楚,以后应对他更是!”
我深吸口气,没再回复,将对话框删除,却把他的话记在了心里。
汽车最终在一家中式庭院的门口停下。
矮小的木门上镶着门环,精致古朴,檐下挂着一盏灯,被夜风摇出缠绵光影。
院内花木郁葱,灯光顺着石路延伸到远处,逐渐模糊成一团雾。
此番踏入,前路未知。
我却别无选择。

认识程亦明是在一年前,当时我正在一家洗车店兼职。
按说以他的身家不可能来这种小店,但他那天恰好在附近办事,车胎又恰好被小狗给尿了。
洁癖如他,只能就近清洗。
所以我时常在想,我和他确实是有一些缘分在的,只不过是孽缘。
程亦明看到我的第一眼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眯着眼将我从头打量到脚,目光直白到冒犯。
我心头怒起却只能装作没察觉,僵硬着手脚加快速度。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突然接到了邻居的电话。
沈佑又犯病了,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已经被送去了医院。
我慌忙扔下抹布,同老板告假,不出意料被拒绝,只得在老板的呵骂声中辞了职。
程亦明从座椅上起身,“我送你。”
情急之下我顾不上思考其他,只是连声道谢,上了他的车,也就此改变了人生轨迹。
我做了程亦明的情人,因为我必须要救沈佑。
十二岁那年父亲与继母重组家庭,我和十岁的沈佑成了法律上的姐弟。
继母是个慈悲的苦命人,几乎丢了半条命才从家暴的前夫手下逃离,始终没放弃自己的儿子。
不久后父亲因病去世,她也没放弃我这个没血缘的女儿,受尽苦累拉扯我们两个长大。
眼看着我就快大学毕业,终于有能力报答她了,她却在一次外出中发生了车祸。
继母将我护在身下,当场死亡;沈佑头部遭受重创,连续做了三次开颅手术。
我幸运躲过一劫,看似毫发无伤,内里却已支离破碎。
巨大的痛苦从空洞胸腔漫出,如同无数荆棘爪牙日夜撕扯着我的血肉,让我痛不欲生。
我却只能强打着精神,处理继母的后事,借钱给沈佑治疗。
直到沈佑苏醒,还来不及欢欣,就又陷入了更大的灾难之中。
沈佑患上了继发性癫痫,时常发病,思维和行动能力也都严重受损,需要人看护。
我退了学,一边照顾沈佑一边打工赚钱,再苦再脏的工作我都干。
累得狠了就抱着沈佑哭一场,看到他身上磕碰烫摔的各种伤痕再哭一场,然后睡一觉,天亮了再继续。
攒上两个月钱,就送沈佑去医院做一个疗程的复健。
哪怕只有很低的概率,哪怕遥遥无期,我也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康复如初。
沈佑怕拖累我,不止一次想过要放弃,被我哄着骂着才坚持下来。
但断断续续的治疗效果甚微,近两年更是有恶化的倾向,有几次差点出大事。
医生建议住院进行长期治疗,但我根本凑不出医药费,只能一直拖着。
所以当程亦明提出时,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别说是我这个人,就是我这条命、全身的器官,都可以拿去卖,只要能换来钱。
很快,沈佑就被安排住进了最好的私立医院,还有专业团队负责。
我跟他道别后,跟着程亦明回了他的别墅,别墅坐落在半山腰,很适合金屋藏娇。
显然程亦明也是这么想的。
除了一个月可以去看一次沈佑之外,他不让我出门,只让我在家学习。
品酒、茶艺、珠宝鉴赏、插花、穿搭……种类繁多,唯独取悦男人的技巧不许我学。
他并没碰过我,甚至都很少来,似乎将我遗忘在了这座空荡华丽的牢笼之中。
我轻松的同时又觉莫名,但我不敢问,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
时间久了闲得无聊,我便找了些花在院中种下,浇水授粉,精心侍弄。
程亦明第三次来时,正是第一朵花开之日。
我蹲在旁边看,闻到酒味才骤然回头,他踉跄的脚步已然踏落,被我伸手挡住。
痛呼声中,程亦明醒过神来,沉下脸拉起我回屋,翻出药膏擦在我破皮红肿的手背上。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那破花比你手还重要?”
我抿唇,“它才刚开……还没给你看过。”
程亦明微怔,像是突然熄火的炮仗,没再说什么,当夜却主动帮我洗了澡。
带着薄茧的手掌游走过我全身,酒意丝丝缕缕氤氲在潮湿的水汽中,熏得人头昏脑胀。
我看到程亦明憋红的眼尾和急促的呼吸,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最终又缓慢放下。
他依旧什么都没做,将我抱到床上后就独自回了卧室休息。
那时我便知道程亦明是个狠人——能够对抗本能和欲望的男人,做什么都会成功的。
后来程亦明来得多了些,大多数时候都醉醺醺的,趴在马桶上吐得撕心裂肺。
我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是很有钱,但过得似乎并不尽如人意。
时常接到来电,对方像是长辈,对他口无遮拦地斥骂,用词污秽不堪。
他面色不变,显然已经习惯,手背上的青筋凸起,像是蜿蜒丑陋的伤疤。
我假装不知道,只是剪来几支盛开的花枝为他插瓶,故意磨蹭着时间同他讲些无聊的闲话。
他一般都不会理我,直到某次突兀握住了我的手,像是再也无法承受一般,吐露了他的困境。
原来他是程家的私生子,父亲让他当牛做马地卖命,却又不真心接纳他。
他越想证明自己就越被打压,才知道父亲只是要他当嫡子上位的垫脚石。
那些痛和恨在天长日久中将他磋磨得脆弱又孤独,颤抖着吻上来时竟然带了泪。
冰凉湿润在我唇上一触即离,却如火焰一般灼痛我。
我知道那是心疼,但我只能攥紧拳头,生生忍住想要安慰他的冲动。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程亦明心情都很不错,不忙的时候还会陪我一起养花。
眼神专注面容平和,似乎也在借由这些沉默却坚韧的生机来做短暂的逃避和解脱。
某夜突降暴雨,等我惊醒后跑出去时,程亦明已经在弯着腰给花枝做固定了。
湿透的衣服紧贴在身上,他不时抬手抹一把眼睛,在脸上留下泥土,又迅速被大雨冲刷掉。
我愣愣看着,恍然惊闻有轰隆雷声由远及近,许久之后才发觉,那竟是我的心跳声。
隐秘情意如同雨后的野草疯长,被我小心翼翼地藏于忐忑憧憬之中,伪作一场缥缈春梦,最终还是被程亦明亲手打碎。
“邵仲山手段了得,但心机深沉又极难接近,对我这种私生子更是不屑一顾。”
“所以我需要你去到他身边,成为他的女人,取得他的信任,为我办事。”
“这也是我当初带你回来的目的,如今时机已到,我会安排好一切,你照做就行。”
程亦明背对着我看向窗外,玻璃上映出他冷峻的眉眼,半边脸颊上还有一个清晰的巴掌印。
明明挨打的是他,我却像是被无数拳脚砸在全身一般,僵硬疼痛到几乎无法呼吸。
我咬紧牙关,“一定要这样吗?”
“对,我不要再做别人的垫脚石,我要赢。”
……那我呢?你就不要了吗?
我很想这么问,但又不想自取其辱。
他根本不在乎我愿不愿意,只要我听话。
大概是我沉默太久,程亦明不耐烦地回过身来,对上我的瞬间猛然怔住,我才发现自己哭了。
他顿了片刻,忽然跑进房间抄起一根高尔夫球杆冲到屋外,将满园花枝全都砸了个稀烂。
而后转头,隔着落地窗与我对视,眼神冷厉决绝,眼底有光斑闪动,只一下就归于黑暗。
“有些东西注定留不住,那就不该再贪恋。丛芷,你和我都一样。”
那是程亦明留给我最后的话,就此终结了我浅薄又悲哀的心动。
只剩满地残红,终究腐烂入泥。

我实在不知该说程亦明聪明还是愚蠢。
明知邵仲山难搞才想利用女人走捷径,却又笃信他会轻易被女人搞定。
这本身就很矛盾。
况且还是我这种没什么手段的女人,大概就只有这一张脸能用。
但邵仲山似乎也没多喜欢。
将我带回去交给佣人后,就径自上了楼。
偌大的别墅,灯火通明,却寂静得如同一座新坟。
家具陈设一尘不染,但从佣人对他的态度来看他应该并不常来,更别说带人回来了。
是以不断有好奇和探究的目光落在我身上,让我更加手足无措。
直到陈姨到来。
她是从小照顾邵仲山的,与他感情甚笃,为他一通电话就从老宅赶来了这里。
陈姨领着我参观别墅,还简单介绍了一下邵仲山的喜好和禁忌,语声平和,不亲不疏。
我静静听着,一路行到自己房间门口,进去前忽然被叫住。
“丛小姐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都可以问我。”
我摇头,“您交代的我已经记住了,其他不该问的我不会问,况且我也不一定会在这里很久。”
陈姨微怔,随即轻笑,“这话说得可不聪明,当心被邵先生听到。”
“……听到什么?”
背后的门突然打开,邵仲山换了衣服走出来,发梢还湿着,周身逸散出浅淡冷香,似檀非檀。
我忍不住嗅了几下,忽闻一声轻笑,邵仲山眼角微弯,“陈姨,你看她这样子像不像汤圆?”
陈姨拍了他一下,哭笑不得,“别胡说,没礼貌!”
后来我才知道,汤圆是他幼年时养的一只萨摩耶,吃得滚圆一团又十分粘人,才因此得名。
邵仲山很喜欢它,上学再忙再累都会抽出时间来溜它,直到他出国留学前夕才因病去了汪星。
那时我只以为邵仲山将我与狗相提并论,却不知道这是他十五年间第一次提起汤圆。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当时我只觉得无措,又庆幸话题被他岔开了,不用回答他那句问话。
“需要我做什么吗?或者我先去洗澡,然后去您的房间?”
我尽量淡然地发问,藏在身后的手却紧攥成拳,指甲在掌心抠出轻微刺痛。
邵仲山挑了挑眉,看似是个感兴趣的表情,脸色却明显冷下。
“有些事情说透了就没意思了,会显得很下流,我不喜欢。”
我呐呐点头,又听到他问:“会吹头发吗?”
这个说法会显得比较高级吗?有钱人确实“讲究”。
邵仲山的房间大而空,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只在床的对面摆放了一面巨大的落地镜。
我沉默地帮他吹着头发,不经意间抬眼,从镜中对上他沉滞的眼神,蓦地惊出一身冷汗。
手下失了轻重,不慎扯落了几根头发,邵仲山却似无所觉一般,拽下我的手。
“好了,回你房间去睡吧,夜里有需要就叫人。”
他说的吹头发竟然真的只是单纯地吹头发!
我为自己肮脏的揣测感到羞耻,更因这意料之外的状况感到困惑。
辗转反侧大半夜,也没想到什么迅速拉进距离的办法,快天亮时才睡过去,却就此错过了与邵仲山共进早餐的机会。
我僵立在楼梯上,看着空荡的客厅,一时不知如何进退。
手机震动两下,是程亦明发来的消息,“昨晚你们有没有……”
他竟然也有说不出口的时候?
我冷笑一声,如实回复:“没有。我主动问了邵先生,但他对我并不感兴趣。”
“谁让你自作聪明的!我从来不碰你,就是为了让你保留最青涩最真实的反应才能勾住他,你非要这么掉价吗?”
原来如此。
我胸口冷不丁一刺,有什么仅存的东西被利刃斩断,坠落后碎了一地。
“你以为邵先生不知道我是什么货色吗?勾勾手就跟着走的人能值什么钱,也就沈佑一年半的治疗费,不是吗?”
程亦明默了许久,像是开解又像是威胁,“丛芷,你想得到什么就必须付出什么来交换,这是规则,而你已经没有退路。”
这话犹如魔咒一般盘旋在我脑海中,不断拧扯着我的神经,一整天浑浑噩噩,食不下咽。
半夜犯了胃病,疼痛难忍,手边没有药也不敢麻烦别人,只得蜷缩成一团,将眼泪埋进枕头。
不断安慰自己天总会亮,只要忍一忍,疼痛很快就会过去,苦难也一样。
直到我被人从被子中扒出来,才发现自己浑身冷汗,意识昏沉,许久才辨认出眼前人是谁。
“邵先生,你怎么过来了……是需要我做什么吗?”
邵仲山皱着眉,“你还能为我做什么,连自己生病都不知道!”
“只是胃痛而已,老毛病了,不用管。”
“怎么不叫人?要不是我起来接电话,听到你的痛哼声,你还打算疼死在我家吗?”
“陈姨说你睡觉轻,我怕来回走动打扰到你,想着忍忍就过去了……”
邵仲山怔了下,没再说话。几分钟后房门被推开,陈姨领着家庭医生进来。
给我开了胃药服下,又给陈姨说了几个营养食谱。
一通折腾过后,窗外天光已泛白。
我缓慢坐起,歉然看向邵仲山,还未开口就被他抬手制止,径自接上了之前的话。
“忍耐可不是什么好习惯,以后得改改。”
房门开了又关,有风钻入屋内,也钻入我心底,吹皱丝丝缕缕的涟漪。

那天之后,邵仲山开始和我一起吃饭。
但他工作忙,别墅离公司也远,所以早起晚归的,每餐都吃得匆忙潦草。
连我都看出来了,陈姨更是明了。
我偶然听到了陈姨劝他,“你这样哪能吃好,还是在公司让专人送饭吧!至于丛小姐,有我在你还怕谁怠慢了她?”
“与她无关,我就是想试试在家吃饭的感觉,毕竟神仙下凡也得尝尝人间烟火不是?”
陈姨失笑,我也忍不住摇头,惊讶又新奇于邵仲山完全不同于众人口中的一面。
随性,幽默,偶尔幼稚,只在陈姨面前展露。
同时又严谨而戒备,四两拨千斤地避开话题,连陈姨也无法探知他真实的想法。
真是一个复杂且难测的人。
唯今之计,我必须先仔细观察,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之后再想办法。
首先从他的饮食习惯开始。
虽然厨师都是按照他的喜好做菜,但依旧能明显看出偏好。
不大喜酸,一般吃不过三口;喜欢辣,但因为唇周会被辣得发红也不大多吃;但是嗜甜,哪怕之后要去健身房跑一小时,也会坚持吃完一块蛋糕。
为此我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比如怎么在保留辣味的同时降低辣感,又或是怎么用木糖醇代替白砂糖,在保持甜度的同时降低热量值;
而后又花了很多时间去尝试制作,期间遭遇了各种困难,也受过几次伤。
陈姨按照我的请求没有告诉邵仲山,他自然也没发现。
不是不失落的,但我更知道惊喜的力量,于是只沉默而执拗的坚持。
第一次被问起是在半个月后,“这个慕斯蛋糕的口感好像不太一样,是换西点师了吗?”
陈姨笑吟吟地接话,“是丛小姐亲手做的,她学了好长时间呢。”
邵仲山手一顿,转眼看向我,轻轻点头,“好吃。”
我抿唇笑笑,将右手覆在左手上,遮挡住了虎口处烫伤留下的痕迹。
饭后,邵仲山叫我去了他房间。
再次看到那面镜子,我已经坐在了它的正对面,邵仲山的床上。
他坐在我旁边,低头往我左手上涂祛疤凝胶,“丛芷,你很聪明。”
语声幽凉,如同雪水落在我心尖,我不由地瑟缩,被他用力握住,硬着头皮装傻。
“是吧,我在烹饪方面有点天赋。”
“看出来了,而且美商也不错,我看你房间的插花很高级,应该不是出自佣人的手笔。”
“我自学过一段时间。”
邵仲山点点头,似乎只是随口一问,临出门前突然站定。
“家中无聊,你随时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我从来没要拘着你。”
“给你的卡也要刷,毕竟是跟着我的人,不捞点好处倒显得我小气了。”
“只有一点,必须要在我下班前回家,我喜欢有人等我。”
直到房门被彻底关上,我才长舒了一口气,突然发觉邵仲山是一个比程亦明更残忍的人。
因为他更加笃信且奉行等价交换——
我取悦到了他,所以他给我奖励,比如限定的自由,又比如金钱。
明码标价,银货两讫,当然我就是那个货。
虽然残忍,甚至耻辱,但我也换来了自己想要的。
时隔两月,我终于可以去医院看望沈佑了。
他比上次见面瘦了些,越发显得两个眼窝凹陷,精神也有些萎靡。
但见到我后明显很开心,兴奋地从枕头底下掏出他记事的小本本。
他记忆力下降,为了同我多聊会天,就会把想说的事情记下来,见面时再逐条说给我听。
无非就是哪个病友出院了,食堂的餐食咸了淡了,他的男护工又在追哪个女护士了……
总体上乏善可陈,就是他的生活。
被困在这间小小的病房,只有冰冷的仪器和做不完的复健,不知道何时是尽头。
我看得出他很累,但还是很努力地在逗我笑,想让我放心,又拐弯抹角地打听我工作累不累,其实还是怕自己住院花费太多。
“放心吧,姐姐现在很会赚钱的,养活咱俩没问题。你也要努力好起来,到时候姐姐就等着享福了!”
沈佑重重点头,眼神忽然飘向我身后,面色微变,欲言又止。
我顺着他视线看过去,透过门缝对上程亦明冷沉的眼睛。
他倚在楼梯间的墙壁上,掏出一根烟,在即将点燃时又放下,看得出烦躁。
“目前进展如何?”
“如你所见,获得了自由外出的权利,我还打算去找份工作,比跟着你时可好太多了。”
“我是让你去做事的,不是去享受的。”
“享受?这福气给你要不要?”
程亦明咬了咬牙,“口舌之争没有意义,就当是为了你弟弟,用心些,我不会亏待你的。”
我向前一步抵近他,“这是最后一次,不要再来这里,我不想沈佑知道我赚的钱有多脏!”
诛心之言,伤人伤己,我离开的脚步踉跄,转过墙角时突然顿住。
沈佑正扶墙站着,似乎是来找我的,走得艰难呼吸急促。
“姐,那位先生……我见过几次的,有时会跟我的主治医生谈话。”
“嗯,他是我朋友,跟这里的医生都很熟,你来这里就是他介绍的,安心住着吧。”
他向来听我的话,并不追问,吃了药后昏昏欲睡,我便趁机离开了。
我拿着准备好的简历去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应聘。
面试还算顺利,我当天就办理了入职手续,晚餐时主动告知了邵仲山。
他有些意外,却也没反对,说要给我配车被我婉拒后也没再多说什么。
倒是陈姨私下同我说何必去吃那份苦,还不如多用心讨好邵仲山,做美美的菟丝花。
我苦笑着摇头,暗道等我做坏事那天,你恐怕就要骂我是狠毒的断肠草了。
之后一段时间,我早上同邵仲山先后出门,晚上比他提前到家,至少亲手做一道菜。
研发了新的菜式,还成交了三套房子,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竟有种久违的安稳。
与邵仲山也亲近了不少,我会帮他搭配好第二天要穿的西装,偶尔给他打领带。
每当那时他总是沉默地垂眸看我,眼神专注,似竟真有几分情深之意。
但我知道他只是在透过我看另一个人。
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同性生出强烈的好奇。
要有多么好才会被如此念念不忘!
而我,却只配做个替代品。

邵仲山提出要带我去参加酒会,我是十分震惊的。
大概表情过于直白,他少见地掐了掐我脸,“不愿意跟我去?”
“……没有,只是觉得不合适。”
“除了你,没人敢这么觉得。”
话已至此,我无力再说,只是仰头绽开一抹笑,“好,我的荣幸。”
邵仲山虽然地位高,但是架子并不大,也没什么压轴的爱好,到得算是很早。
攒局的主家正是之前在会所时坐在邵仲山身边那位,叫做霍景珩。
他看到我时有瞬间的惊怔,随即轻笑,眼神意味深长。
邵仲山似无所觉,引着我往里走,到了座位才看到程亦明竟然也在。
我心尖猛地一悬,走神间双脚打绊,堪堪跌坐在了邵仲山腿上,被他搂住。
“在家倒不见你这么投怀送抱。”
“不是……你说过不喜欢的。”
“那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是怎样,宣誓主权?”
邵仲山到底在胡言乱语什么我根本就没有的东西啊!还没喝酒就醉了?
我讪讪一笑,连忙坐好,发现程亦明不知道何时离开了,才暗暗松了口气。
过了大约十分钟,人基本就来齐了。巨大的蛋糕推出来,我才知道是霍景珩的生日宴。
众人纷纷凑上去送礼物,只有邵仲山无动于衷,反而是寿星切了蛋糕将第一块主动送了过来。
言语间才知道,邵仲山竟然大手笔地送了霍景珩一个项目,听得众人羡慕不已。
程亦明站在人群边缘,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像极了他的处境,始终被排斥在核心之外。
他的哥哥也应邀参宴,于人群中左右逢源前呼后拥,程亦明却像个灰扑扑的影子,无人问津。
我忽而便能理解他的迫切与偏执了,正如我于沈佑的性命,是不能放弃的东西。
左肩蓦地一凉,随即传来浅淡酒气,不知是谁把酒水洒在了我赤裸的肩头。
邵仲山没发觉,我也没多嘴,只跟他说了一声,独自去卫生间打理。
出来时碰到了程亦明,他正在不远处的阳台上抽烟。
旁边还站着一位娇媚的年轻女子,没骨头一般倾靠在他身上。
程亦明抖了抖肩膀,语声不耐,“你收敛点,明知旁人诟病你的出身,还非要坐实了?”
“我妈是小三上位怎么了,那是她的本事!况且咱俩什么锅配什么盖,你还嫌弃上我了?”
“我只是想提醒你,虽然我答应了和你结婚,但不代表我就会随意被你们家拿捏。”
“无所谓,各取所需罢了。我们这种人,最不需要的就是真心和感情。”
程亦明默了默,将烟头按灭在栏杆上,“是啊,所以我只能把自己的心扔了,心里的人也是。”
说话间,他转过身来,对上我蓦地蹙眉,很快又恢复如常,大步离去。
直到坐回邵仲山身边,我都还在回想程亦明看我那一眼,心头隐约浮现出一个离谱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