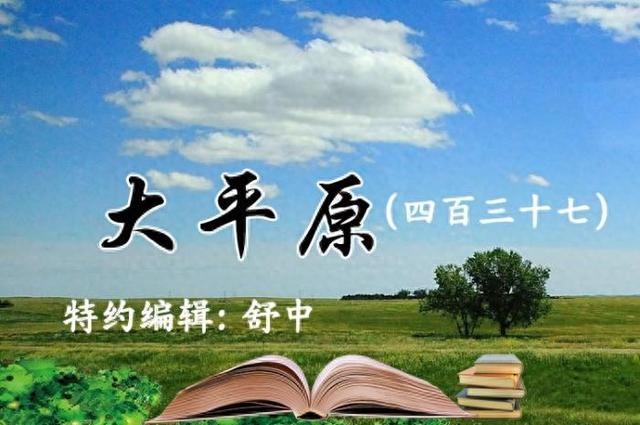
年近六十
文/周维东
到明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我便整整六十岁了。中国人称六十年为一甲子,天干与地支又要重新开始。世人多谓六十为老,我却不以为然。如今人至六十,身体尚健,记忆犹新,何老之有?况且天干地支重新轮转,岂非人生第二春之始?
我生于乡间,长于田野。幼时曾见村中老翁六十寿辰,子孙绕膝,俨然已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那老翁姓陈,整日坐着一把旧太师椅在他家大门过道里打盹,嘴角常挂着一丝涎水,孩子们都远远地避开他。而今日镜中的我,虽然头顶光明,鬓角斑白,但目光犹炯,步履尚健,与记忆中的“老人”相去甚远。想来是生活变好了,人亦随之而变年轻。今人六十岁,尚能登山涉水,与友人对饮至深夜,翌日清晨仍可精神抖擞地迎接朝阳。
前日得闲,翻检旧物。一只木匣中竟藏着我五年级下学期的作文本,纸页泛黄,字迹歪斜,有篇稚嫩的文章,题目为《我的志愿》。那时我想做一名东方红拖拉机手,开着那棕红的如装甲车般的大铁牛在无边的田野上奔驰。记得每逢秋耕时节,我便趴在田埂上看那东方红拖拉机轰鸣而过,驾驶员神气地手握操纵杆,身后翻起层层泥浪,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气息。后来志愿未遂,却也在胜利油田物探公司谋得一份文职,终日与笔墨为伍。如今回首,竟不知是得是失。或许人生本无得失,唯有经历而已。
妻常笑我愈老愈倔。譬如前几日修那北极星牌老式坐座,明明可寻匠人,我却偏要自己动手。那钟是父母的遗物、稀罕物,黄铜钟摆已泛暗绿,齿轮咬合处常有杂音。拆了装,装了拆,反复三日,我方得其法。其间手指被弹簧弹伤数次,眼镜滑落鼻梁无数回,妻子劝我歇息,我只作不闻。钟摆再响之时,喜悦竟如幼时首次在湖里钓得大鲤鱼一般。这等心境,岂是垂暮之人所有?
旧友渐稀,有的故去,有的迁居远方。每得讯息,不免唏嘘。前年文友老王走了,心脏病夺他而去。记得五年前的一个清明我们还相约去麻大湖踏青,他指着湖边的桃花说,来年他要写尽这满目的绯红奇香。送别那日,见他安卧花丛,面容平静,竟比生前少了许多愁纹。想来人生在世,劳碌奔波,到底所求为何?老王一生谨慎,临了却对我说:“悔不曾多醉几回。”闻之怅然。如今每经过酒楼,总要多看两眼,仿佛能看见老王坐在角落里独酌的身影。
今春我开始学作画。妻讶异,问何以忽然要画画。我答曰:眼尚明,手尚稳,此时不学更待何时?初时画竹,枝叶僵硬如铁条;近日所作,已略有风致。非为成名成家,但求心有所寄。每至黄昏,铺纸研墨,竟觉时光静好,不知老之将至。画室设在正屋内的南边窗下,窗外正对一株老桑树,常有雀鸟栖于枝头,时而探头窥我作画,时而振翅掠过窗前,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影子。
邻居前日来我家,忽问:“可曾害怕?”我愕然,问怕什么。他答曰:“怕死!前日你的同学不是因事故去世了?”我笑而答曰:“每日我有事要做,有画要学,有书要读,有文章要写,来不及害怕。”他似懂非懂,转身离去,边走边感叹曰:“不与常人同!”其实我何尝不怕?只是这怕,终究要让位于生之趣。就像小时候怕黑,但只要母亲点起油灯,看见墙上晃动的光影,恐惧便消散了。
近来得闲,便到湖里林荫路上去走走。不是看花,而是观人。晨练的老者,嬉戏的孩童,相依的恋人,各自有各自的悲欢。最爱坐在湖南边的长椅上,那里有一行行的国槐,四季变换着衣装。春日萌发新绿,夏日浓荫蔽日,秋日洒落金黄,冬日枝干虬劲。看那树下,有老人提着鸟笼遛画眉,有少年捧着书本默读,有妇人推着婴儿车缓缓经过。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不同的故事,而我也成了他们眼中的风景。
昨日遇故人之子,他已近中年,寒暄间称我“老先生”。初时不惯,转念便释然。称老何妨?老非终点,而是另一段行程的起点。如登山者,至一平台,略作休整,便可继续向上。记得二十八岁时登泰山,至半山腰已气喘吁吁,歇息片刻后竟一鼓作气直上玉皇顶。如今想来,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近日又开始第五次通读《诗经》,虽不能尽解其意,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之句,常让我想起小时候麻大湖的芦苇荡。计划明年开春去西北走走,看看西北怎样不同于鲁北的苍茫大地。身体虽不如青年时矫健,心境却较那时更为澄明。得失之间,自有平衡。
夜来独坐院中,见星河在天。想这宇宙浩渺,人生如寄,六十寒暑不过眨眼之间。然则即此眨眼瞬间,亦当有它的光彩。老与不老,不在年岁,而在心境。只要明日太阳升起时,心中还有期待,还有好奇,还有几分天真,便永远谈不上老。
如此想着,便觉六十将至,非但不惧,反而心生欢喜。第二春何在?就在每一个醒来清晨,每一次提笔作画,每一回与妻笑谈之间。今晨妻忽道:“你近来常哼小曲儿。”我这才发觉,不知从何时起,童年时的歌谣又回到了唇边。
人生百岁,六十方半。譬如行至中途,卸下不必要的行囊,脚步反而轻快起来。过往的悲欢都已沉淀为生命的底色,未来的日子则如宣纸铺展,待我用余下的光阴细细描画。这第二春未必绚烂夺目,但自有其从容淡定之美。
忽忆起十年前去绍兴寻根续家谱时顺路访苏州园林的情景,见一老匠人修剪盆景。问他需时几何修好,他答曰:“一辈子也不够。”当时不解,而今乃知:生命之美,正在这永无止境的修剪之中。六十岁,不过是换了一把更称手的剪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