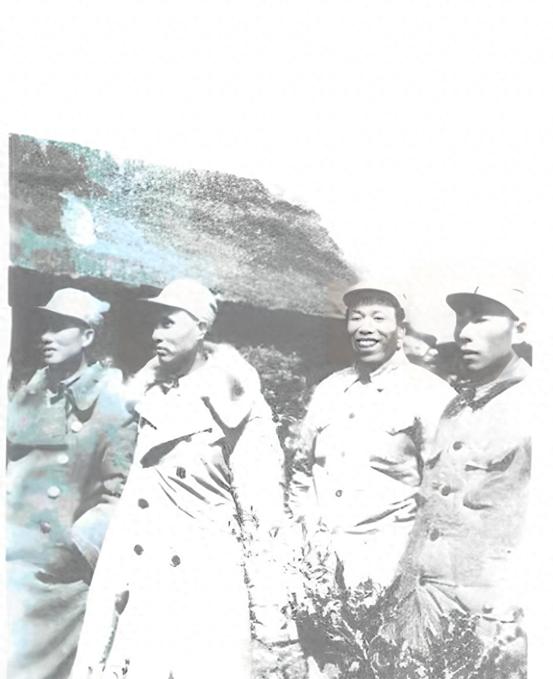他曾是中原军区2纵副司令,到山东当上师长,不知身兼军区副司令 “1946年9月,’别回头,冲出去再说!’周志坚压低嗓音,把仅剩的四名警卫推向夜色。”这句在大别山山脚的催促,标记了中原突围中一个并不起眼的瞬间,却决定了他此后几年的辗转与际遇。 周志坚那时的身份是中原军区二纵副司令员。王树声、李先念、王震各自率主力杀出重围,他却因奉命照料散失部队而留在最后。国民党层层封锁,山地、河谷、铁路线轮番堵截,散兵先后化装成挑夫、船娘甚至茶楼伙计,才最终凑出一条向西的暗线。途中,一位老乡探头问:“汉口走得通吗?”周志坚只回三个字:“只能拼。” 抵达汉口后,他找到驻军调执行部中共代表小组。这个点像拐弯处的交通灯,绿灯只闪一次。代表小组迅速为他办妥身份文件,路线却不是西北,而是东南——南京。原因简单:南京有中央代表团,跟随代表团撤离,安全系数要高;若翻过封锁线再去延安,半路堵截几乎是必然结局。 南京初冬的雨水凉薄,周志坚压根没料到自己会上到国民党眼皮子底下“中转”。他身上带走的只有突围简报、部队番号和几张牺牲名单。12月初,延安电台收到他的电报:“任务完成,请示归队。”不久,他从洛川机场下机,直奔前总司令部——彭老总等人对突围情况急需一手资料。 会上,地图摊了一地。彭德怀边听边问:“下一步想去哪里?”周志坚回答得痛快:“山东。”在座参谋疑惑:鄂豫陕根据地正缺老练指挥员,怎么偏挑胶东?周志坚的判断很直接——敌军主攻方向北移,山东战线比陕南凶险,正面胶着、两翼威胁,还要应付海上补给切断。换句话说,那里需要有经验又不要职务包袱的“急救员”。 彭德怀点头,但叮嘱一句:“换个环境,身份别太计较。”延安的任命电报很快飞出,给他的头衔写了两行:胶东军区副司令员、新编第五师师长。电报在半路被密码台截出两份:机要室只转交了“师长”部分,副司令的头衔因排版卡号被耽误在夹纸板里。这场“卡纸事故”让周志坚的“副司令”身份差不多尘封了四十年。 1947年春,他到达招远前线指挥部。许世友递上一根旱烟:“部队认你这面旗吗?”周志坚笑道:“人不熟,战法熟。”胶东兵多是海边渔民出身,野战经验尚浅。他把中原突围时的“小股穿插”“迫击炮跟排”“夜间定向拉网”三招改装为适合丘陵、海岸的打法。不到半年,新五师战斗序列成型,配属作战科、政治科、后方留守科“三科制”,打完黄县、牟平两战连创六个团规制战例,伤亡比以往降低三成。 有意思的是,新部队朝气虽盛,却难免生疏。一次战前准备,参谋长递来作战计划,页眉写着“请副司令审批”。周志坚看了直摆手:“写错了,师长签就行。”谁也没想到,他其实就是“副司令”。对此,许世友事后打趣:“算你小子藏得深。”周志坚只摇头:“打仗没有隐藏一说,派头小点更好管兵。” 1947年冬,山东兵团整编,第十三纵队挂牌,周志坚调任司令员,部队番号“新五师”改“十三纵三十八师”。编制一换,他自然而然进入兵团前指序列,仍沿用指导员连坐、后卫营滚动补充的老办法。淮海战役前夕,十三纵担任侧翼穿插,黄百韬兵团遭到合围,周志坚提出“两段截腰、封随助淮”。这条建议后来写进战役纵队协同条令,被徐向前称作“平原阻割的活教材”。 紧张的连续作战下,头衔依旧无人提起。文件流转快,军区、兵团、纵队公文约有十数种格式,缺谁名字都不稀奇。加之前线电报常常删减冗余抬头,小到营教导员常被错写为“指导员”,副司令员漏成“副”开头更不足为奇。时间久了,连师史登记本都写成“十三纵司令员(原中原二纵副司令、胶东新五师师长)”,副司令那行干脆空白。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十三纵改编为第二十军,南下广东。广东剿匪结束后,周志坚调入广州军区任副参谋长。那一年军区人事普查,他在履历表职务栏写道:“1947年—1948年山东军区某师师长。”档案员翻文件,发现一纸1947年4月红字任命:“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师长周志坚。”他被叫去补签字,才惊觉四十余月的“漏任命”。他只说一句:“补就补吧,该干的早干完了。” 值得一提的是,上级对干部使用的原则是“缺口在哪,干部就到哪”,并非简单的升降级计算。一次干部会议上,粟裕指着墙上作战箭头点名:“哪支队伍缺指挥,谁先到谁上。”这句近似口号的指令覆盖了整个解放战争后期的干部流动模式。周志坚的“降职”与“戴漏”不过是其中最典型的注脚。 有人质疑:高级干部身兼要职却浑然不觉,是否意味着组织管理混乱?事实却相反。当年通讯、交通条件所限,任命走纸质电报,夹在成堆情况简报里,出现延误再正常不过。更重要的是,战争环境下的干部考核重实战而轻印章,能否迅速把陌生部队打磨成敢死尖刀,远比头衔准确与否更具价值。周志坚的履历恰好说明这一点。 1955年授衔,他获少将军衔。授衔公示时,履历重新罗列——中原军区二纵副司令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兼新五师师长,十三纵司令员,二十军副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