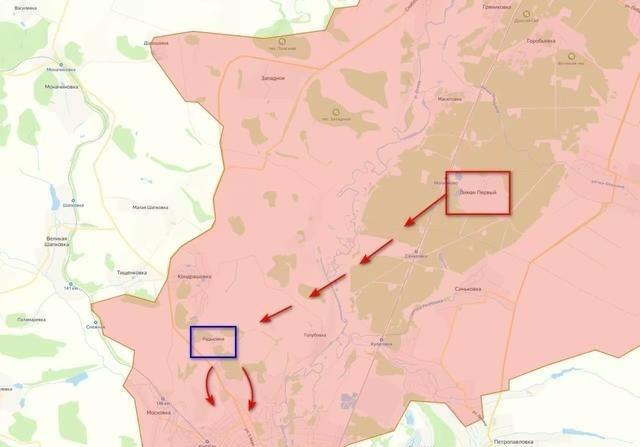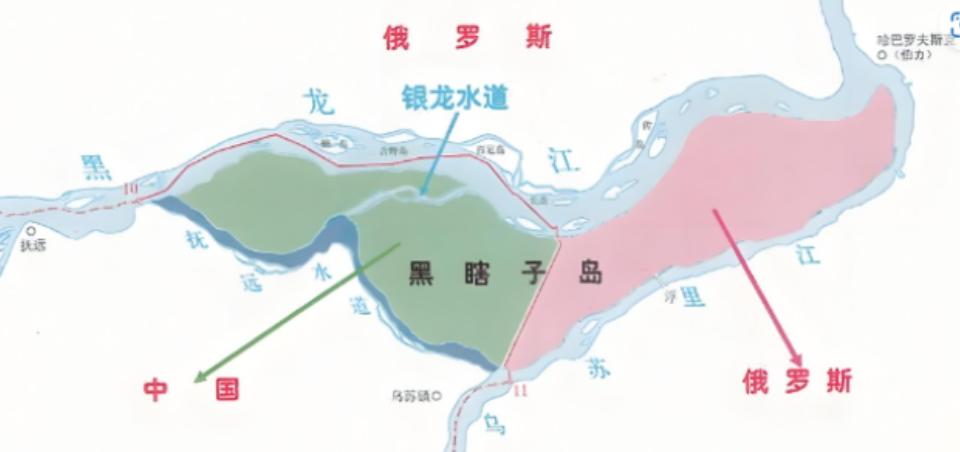转自:天津日报

1
渠阳县,两把刀,一把剃发,一把割骚。这是我给剃头匠周良和劁猪匠陈山编的顺口溜。陈山对周良说:“你我并列,让我感到荣幸。你的刀是对人,我的刀是对猪。你整上边,我整下边。你们这行是阳春白雪,我们这行是下里巴人。”周良憨憨地摇摇头说:“未必,当给日本兵剃头、修面时,我感觉还不如你。”
周良的剃头手艺在渠阳很出名,他每天会准时出现在南街集市上,好多人就是奔着他这把剃刀去的。周良用一根短扁担挑着一副挑子来到集市,挑子的一头是红漆长方凳,凳腿间有三个抽屉,上边一个放钱,钱从凳面上开的小长方孔里塞进去,下面两个抽屉分别放置围布、刀、剪等工具。挑子的另一头,是一个小炉灶,灶膛的木炭总是半明不灭地烧着,黑黢黢的铁桶里,微微地飘着热气,上面反扣着一个大沿黄铜盆,是烧水用的。
到了集市,周良把挑子摊好,拿出一尺二寸长的条铁“唤头”,左手拿着它端在胸前,右手拿一根小铁棍,潇洒地从条铁间的缝隙向上挑去,“唤头”便发出响亮、悠长的嗡嗡声。他围着摊子打了一圈“唤头”,然后就从腰间掏出铜烟袋,蹲到树下眯缝着眼抽烟去了。看见有顾客来,他眼里马上闪出兴奋的光,“当当当”地在鞋底敲掉烟袋锅里的烟,起身把烟袋别在裤带上,过去笑脸伺候。
下午上完课,我去找周良剃头。这时集市也散了,来剃头的人不多,可以静下心来聊天。
周良正在大树底下蹲着,举着旱烟袋,悠闲自在地抽着烟,看见我来了,指着凳子招呼我坐下:“大学士来了,蓬荜生辉。”
我自己兑好了水,洗了头,坐在凳子上。周良拿出了剃刀。这把剃刀确实是好钢锻造,看这刀,宽略盈寸,厚有一厘,长有一拃,配以檀香木的柄,真像是一件艺术品。近三寸的长刃,散发出温润的蓝光,刀刃薄如蝉翼,轻轻拂过面庞的那一刻,仿佛能感受到它带来的似啄似吮的独特触感。周良按住我的脑袋,只听得头顶上“嚓嚓嚓”几声响过,一簇簇湿漉漉的头发便应声落下。头顶剃完了,开始刮脸、刮胡子,直到把躲藏在耳朵边的一些散乱绒发也刮干净为止。
这天,我与周良聊到了太阳偏西。忽然,来了个人,连呼哧带喘说:“快,给我们家老爷剃头吧。挨了黑枪,要归西了。”周良说:“这活儿我接不了,你找别人吧。”挨黑枪这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劝周良:“没有往外推主顾的道理。我陪你去。”
到了那家,屋里屋外站满了人。我慢慢听出门道了,挨枪子儿的是维持会的头头,为日本人杀过共产党,结果让人打了黑枪,正一口紧着一口地捯气儿呢。
周良说过,给弥留的人剃头是要从后面剃,怕被临终那口气喷到。剃死人头,不好剃不说,还有流年不顺的禁忌。有人急了,催促周良:“快点剃啊,趁着老爷子还有气儿。”周良拿出剃刀,从中间往前推去,然后左右分别几刀,头发干净利落地剃下了。
周良收起了剃刀。那边人不满意:“把后脑勺也剃了。”周良慢悠悠地说:“到这儿就不给剃了。”那帮人不快,骂骂咧咧地说:“为什么?这不糊弄人吗,后面为什么不剃了?”
“留后。你们是不是不留后了?”
“你怎么说话呢,谁不想留后!”
临走,周良跟他们要了一块大洋。路上我问周良:“给死人剃头真有那么多讲究啊?”周良笑笑:“没有啊。这个主儿我知道,杀共产党,早该见阎王。我故意耍耍他们,让这家伙到了阎王爷那里也不好托生。”
2
今天来的这个主儿满脸横丝肉,脸上长满了痤疮,一看就不是个善茬儿,真是“刺猬的脑袋——不是好剃的头”。他大大咧咧往凳子上一坐,跷起二郎腿。周良赶紧翻开扣在炉灶上的铜盆,舀两瓢热水,伸出手指头试一试温度,感觉水温恰到好处,就甩开围布,准备给他围上。那人掏出哈德门烟卷,弹出一根,叼在嘴上,点着火,深深地吸了一口。周良说:“水温正好,您老先洗洗头。”那人一口烟朝周良喷来,把俩牛眼珠子一瞪:“没看见爷我正抽烟吗?”周良没理他,拿起剃刀,往炉灶边挂着的黝黑发亮的备刀布上“噌噌”地荡刀。
他的烟抽完了,把烟屁股一弹,飞出去老远。“听说,集市上数你的手艺不赖,我这个脸可以刮吗?”他指着布满红痘的脸。
“这是酒刺,还不少,您老是有福之人哩。把心放肚子里吧,肯定给您收拾得干干净净。”周良说。一般的剃头匠,谁也不敢揽这样的活,因为这样的脸一上刀,一不小心就要刮破痘,要是流血,弄得整条毛巾都是血渍。
他瞪起那双牛眼:“我这酒刺,割破了一个,罚你一块大洋。”
周良也来了气,问他:“那要是不割破呢?”
“不割破是你应该的,总不会每个主顾都给割得头破血流吧。”
哪有这么不讲理的!周良没好气地说:“那这可保不齐,要不您老去别家?”
“这不扯淡吗。你在这支摊,有活儿又不接,我看你这摊子干脆砸了!”
“别价,砸了我上哪儿喝粥去。”周良沉着地俯下身,按下他的脑袋,一下一下撩水洗起来,然后,把一条热毛巾敷在了他的脸上。
这个头的确不好剃,满脸的痤疮不说,头发里还有痦子、瘊子,脖子上有鸡皮疙瘩、小肉赘,后脖颈上面的皮肤还是松弛的,拱出一道一道的肉棱。周良看准了他的头部状况后,便从容地拿起了剃刀。
周良右手执握剃刀,刀刃向下,用右手的拇指抵住刀身凹面的刀窝,食指和中指按住刀柄,无名指和小指上挑,指根抵住刀柄,靠手腕的动作来运刀。他先从右边鬓角起手,手稳,刀平,刀刃成斜角,顺着头茬儿走,从鬓角、后脑至脖颈,最后刮头顶。然后再打另一半头的肥皂,从左鬓角到脖颈,再到头顶顺刮一遍。这是头遍,叫打糙儿。接下来是第二遍,先用温水把毛巾浸好裹在右手,把头转圈擦一遍,之后再拿刀戗茬儿刮,从脖颈往上刮。两遍下来,再用毛巾从头至脖颈擦洗干净,头就剃好了。这人一直惬意地闭着双眼,肯定是感觉舒服了。
周良轻轻捅了他一下,说:“好了。”他起身照了照镜子,那双牛眼一眨不眨地瞪着,看到自己的发须一根不剩,而痘竟然没有割破一个,由衷地赞叹说:“不赖,跟有个小手抓挠似的,舒服,往后我这脑袋就交给你了。”
“别价,一颗酒刺一块大洋,准让我倾家荡产。”周良开始慢悠悠地收拾东西。
他掏出一块大洋,“当啷”一下扔在铜盆里。
周良赶忙把大洋拿起来递过去:“我找不开,麻烦您给零的。”
“这就是爷的零钱。”他撇着嘴,趾高气扬地迈开步,一扭一晃地往前走。
周良赶紧追上去,把大洋塞进他的兜里:“承您赏光。您慢走。”
3
县教育局举办宣传“治安强化运动”的演讲比赛,每个学校出两名选手参加。渠阳师范学校是我和木兰参赛。校长说,你们是学校双璧,只有你们才能在河北省公署出人头地,把冠亚军揽入怀中。木兰死活不愿意参加,她一甩袖子从学校出来,她的书童胡宽赶紧追上去。
到了傍晚,还不见她们回来,我便到外面去寻找。转来转去,我到了南街,远远地看到木兰和胡宽在周良那里。
我过去,对木兰说:“你这头真不好剃呀。”
木兰说:“我才不给日本鬼子念喜歌呢。”
周良说:“不想去就不去,毕竟你们还是学生,这样的事能不掺和就不掺和。”
“你不去念喜歌,别人也会去念。”我跟木兰讲,“你愿意看着别人在神圣的文庙前大放厥词,讴歌‘中日亲善’吗?”
胡宽愤怒地呵斥我:“这不是把小姐往火坑里推吗?”
木兰沉思了一会儿,说:“好,我去。”
周良说:“比赛那天,我不出摊了,去给你们捧场。”
文庙院里,用苇席搭了一个棚子,上面贴着标语,标语是用红、绿、黄三种颜色的纸,裁成大大的菱形块,每块上面一个字,组成“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亲善”等句子。由于下了雨,上面的字迹已经模糊,雨水和着墨汁洇下来。席棚里面贴着我们演讲的主题——《国民的理想》。
万万没想到,比赛时,木兰大讲普通百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子孙满堂”的理想,只字不提“中日亲善”。
比赛结束,等我们准备离开时,侦缉队的过来要把木兰带走,说木兰的表现破坏了“中日亲善”,破坏了“共存共荣”。
正在我手足无措之际,有人拍了拍我的后背,我一回头,是周良。我当时就火了:“你就是这样捧场的吗?他们张牙舞爪地抓人,你连个屁都不放!”
周良赧然地低下头:“咱就是个手艺人,一介草民,能管什么用?”
三天后的中午,我和胡宽去周良那里,见他只是胡乱吃了块烙饼,就一直默默地抽烟。他把烟袋从嘴边拿开,眼泪下来了,期盼地问:“小姐有消息了吗?”
“你精心伺候的那个满脸长包的家伙,就是侦缉队队长刘举,就是他抓了小姐,真是连畜生都不如!”胡宽急得声音都变了。
原来刘举看上了木兰,想让木兰嫁给他,就借演讲发难,扣押了木兰。木兰的家人去找刘举,问他要多少钱可以赎人,刘举说:“我不缺钱,我缺人。把西施找来,木兰就可以回去了。明白吗?”刘举逼着胡宽去说服木兰:“说通了,有花轿坐;说不通,就坐班房。”胡宽不从,就被打了出来。
周良无奈地说:“你看看这集市上,为日本人卖命,最飞扬跋扈的就是刘举。”
我问:“刘举现在还是找你剃头、刮脸?”
“是,他使唤惯我了。”周良茫然地看着我。
我从身上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周良:“你把这毒药浸入水中,然后将剃刀泡在里面,等到给刘举刮脸时,只需割一个小小的口子,就能要了那小子的命。”
周良愣愣地看着我,好久才摇摇头:“不行,我不能乱了这行当的规矩,给祖师爷蒙羞。”
“那你就等着给小姐收尸吧!”胡宽哭着跑了。
4
这天快到晌午的时候,刘举带了三个日本兵过来,非让周良剃头。周良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日本兵,唯恐哪里出差错给自己惹祸。一个头剃下来,早已经汗流浃背了。刘举说:“哪天你就去侦缉队得了,当个御用剃头匠。”周良说:“您抬举,我可没那个福。”
两个日本兵闲得无聊,盯上了集市上一个孕妇,在争论那孕妇怀的是男是女。刘举哈着腰,跟狗似的在鬼子身边打转:“太君,我把她叫来,你们摸一摸就知道了。”
怎么摸得出来呢?刘举解释:“上怀,肚子比较圆,就是小子;下怀,肚子比较尖,那就是闺女。”鬼子一听乐了,摸!
刘举不由分说把孕妇拽过来,蛮横地说:“让太君摸摸,看看是闺女,还是小子。”
那孕妇一听,脸就变了色,使劲地挣脱了刘举的手,转身就跑。
刘举看着孕妇挺着大肚子跑步,动作很是笨拙,不禁哈哈大笑。鬼子冲他挥着手,他赶紧止住笑,迈步去追。按说,以刘举的步伐,很容易把孕妇追上,可他偏偏不紧不慢地撵着,挤对得孕妇满头大汗,一步一个踉跄。集市上的人看着这令人心酸的一幕,敢怒不敢言。
突然,孕妇猫下腰去捂肚子,裤脚下面滚出一股热流。一个老太太嚷道:“羊水破了,赶紧躺下,再折腾下去就是两条人命啊!”见刘举停下脚步,站在原地没动,大家这才敢围上去。
“这下正好,接生婆都省了,快看看是男是女。”刘举站在一边大笑着说。
好在老太太处理及时,孩子顺利出生,孕妇也捡回一条命。众人散去时,已是傍晚。
周良目睹了这一切,他靠在树上,脸色蜡黄,像得了一场大病。
5
转天一早,我去找周良,周良非要给我剃头,他一边剃,一边说:“今天你这个头是我这辈子剃得最用心的一次。”
“以前没用心吗?”
“用心,当然用心。你们这些读书人,将来都是国家的栋梁,我哪敢不用心。”
这时,刘举跟着个日本人过来了,冲着周良大嚷大叫:“快剃!快剃!”
周良恭顺地说:“好嘞,这就得。”他俯下身小声问我,“前些天跟你说的事,就是那匹枣红马,你备好了?”
我告诉他已经跟掌柜的说妥,钱都付了,随到随牵。
“那你完事就去牵马吧。我去八门城随个礼,得跑百十里路呢。”
“别唠嗑了,滚一边儿去。”刘举抬腿踢了我一脚。
“今天你好好伺候伺候米田太君。”刘举撅着屁股刷起了铜盆,腰后的手枪在屁股上一翘一翘的,像小鸡啄米。
我瞪了刘举一眼,解下围布,抖搂干净,然后一边拿小笤帚扫头上的发茬,一边示意周良快去招呼那个日本人。
刘举一边给米田洗头,一边炫耀地说:“剃头的,你知道渠阳最大的官是谁吗?”
“小人不知。”周良愣在原地。
“好好看着,这位米田太君是咱守备队队长,整个渠阳都是他说了算。”
周良突然六神无主起来,脸色难看得很。他哆嗦着用眼角扫着那个日本人,舌头好像打了结,说不出话来。
刘举得意了:“好好伺候,太君不会亏待你的。”
“你快走,我该干活儿了。”周良忽然举起了烟袋,敲了敲我,低声说,“把那枣红马给我备好,剃完这个头,我就用。”
“没问题,牵着就走。”我心想,周良今天怎么有些反常呢。
看他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很想站在一旁,给他壮胆,可是周良非要赶我走。没办法,我只好一边慢慢往外挪着步子,一边偷偷关注着他手里的动作。
周良小心地给米田梳理头发,米田的头前凸后凹,老百姓管这叫“前门楼后倒座”,活像一块芥菜疙瘩。周良的手一直在抖,好不容易把米田的头发梳平理齐。他拿出剃刀在备刀布上不停地荡,那刀口在阳光下泛着青光。米田一看,挥动双臂,冲周良吼起来。原来米田害怕周良的剃刀。周良赶紧解释,这是剃刀,用来剃头发的。周良伸出胳膊,用剃刀剃了几下自己的汗毛,噗地一吹,汗毛飞出去,米田这才拧着眉头,不再言语。
周良把剃刀夹在右手的食指与中指间,用其余八指去给米田的脑袋按摩,先用两手拇指在头部眉弓以上由中间往两边平行直推,动作轻柔、缓和,有节奏地回旋移动,然后用两手掌由太阳穴往下直到下颌的部位直推,再用拇指点按,用掌根按头部,动作连贯、协调,由轻渐重。米田舒服得卸下了防备,慢慢闭上了眼睛。周良把米田的脑袋一会儿摆向这边,一会儿摆向那边,没多久就听到了如雷的鼾声。
周良虽然额头上沁满了汗珠,但手上的动作越来越沉稳,看来是不紧张了。他抬起头四下望着,我们的目光隔了好远还是相遇了,只见周良冲我一笑,用下巴示意我快快离开。我这才放了心,加快脚步奔向马市。
身后突然一声闷叫。
我回头一看,周良正挥着剃刀,剃刀在阳光下闪着刺目的光。周良用剃刀割开了米田的喉管,一股黑血汩汩地喷射出来。
周良把米田的尸体一推,快步朝我这边跑过来,远远朝我喊道:“快,快去牵马!”
我疯了似的向马市飞跑,周良惊慌失措地追在我后面。
这时,身后响起了接连不断的枪声,就听到周良一声惨叫。我回头一看,只见周良的身体还在向前俯冲,脑袋已经栽到地上,身子依惯性朝上撅起,整个人都要倒立起来,随后便嗷的一声,摔倒在地上。
远处,刘举举着枪追了过来。
我赶紧加快脚步,跑到了马市,蹿上那匹枣红马,双腿一夹马肚子,飞也似的奔驰而去。
6
其实我知道,周良一直在找机会杀刘举,却临时改变主意杀了米田。
日军守备队队长被杀,在渠阳县引起轩然大波,刘举怕事情闹大,连夜便放了木兰。日本人觉得周良一定是共产党,把他的尸体吊在了城门示众。
几天后,我才敢再去集市。
南街集市,骄阳似火,风把棒子皮、麦秸吹得乱飞,几处马蹄印里,顽强地冒出几根鸡爪子草。走到周良曾经摆摊儿的地方,我停住了脚步,看着地上干涸的血迹,魂儿像被吸走了一样。阳光刺过来,照进旁边的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反着明晃晃的光。我使劲揉揉眼,走上前扒开杂草,发现了躺在草丛里的那把剃刀。我举起剃刀,看到刀刃在骄阳下幽幽发亮,折射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