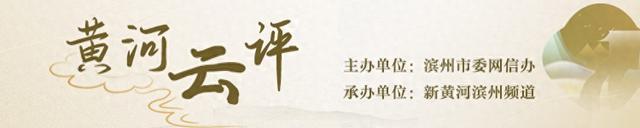
当灼目的烈晖悄然褪去其锋锐,第一缕裹挟凉意的风穿透积暑的帷幕,我们便在古老的时序更迭中,迎来了处暑。这并非一个简单的气候标签,而是镌刻在农耕文明血脉中的哲学符号——“处,止也”,标志着天地之气由疏泄转向敛藏的节气转折。在万物亢奋之极后,它昭示着一个更为深邃的命题:真正的进益,藏于适时而止的智慧之中。
天地不言,而四时行焉。处暑之“处”,是自然韵律的精密节拍。阳气至此不再恣意奔涌,转而沉淀为催熟万物的内在力量;繁茂渐次收束,草木之华凝结为果核中的精华。《管子》亦云:“秋聚收,冬闭藏”,将处暑置于“收”与“藏”的伟大过渡,其意绝非消极退避,而是能量形态的高维转化,是为下一次勃发蓄势的深谋远虑。这恰如兵法所云“藏于九地之下”,方能“动于九天之上”。
反观当下,现代性的迷狂正使我们深陷一场无休的“精神酷暑”。资本逻辑驱动下的无限增长癖、消费主义煽惑的欲望无限流、数字时空对注意力的持续劫持,共同构筑了一个“吴牛喘月”的时代。“内卷”的狂潮与“倦怠”的综合征,正是生命节奏失序后触发的集体高热警报。我们如同夸父,在追逐一个个绩效太阳的征途中,耗尽了内心的清凉与从容。当扩张被奉为唯一法度,收缩与静观便被斥为失败的代名词,这无异于一种文明层面的“处暑”缺失症——只知生发,不懂敛藏;只慕奔腾,不习沉淀。
故而,处暑节气如同一面穿越时空的明镜,映照出我们时代的症候,更是一剂苦口良方。它谕示我们:生命的丰饶,不仅在于夏花的绚烂夺目,更在于秋实的丰硕坠向大地。它呼唤一种战略性的自觉:于个人,或是在信息洪流中筑起心斋的堤坝,守护精神的沉默与专注;或是从奔竞喧嚣中抽身,向内培元固本。于社会,则意味着从对速度与规模的单向度崇拜,转向对可持续发展与生命质量的深刻关怀,重拾“收敛”以求“厚积”,“节制”以达“持久”的古老辩证法。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处暑之妙,尽在这由喧腾转入澄明的枢纽之境。它提醒奔忙于尘世的我们:观天之象,察时之变,法其敛华就实之德。唯有在张弛有度的生命节律中,方能规避“盛极而衰”的倾覆,涵养“安舒从容”的底气,最终收获一个不仅丰硕,而且敦实的完满人生。
(作者左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