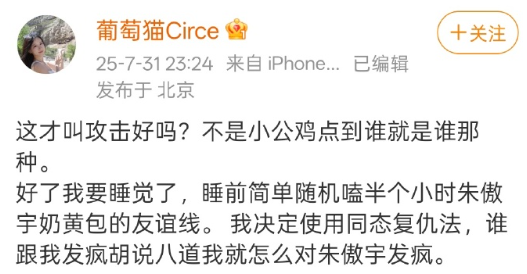天宝六年,安禄山一边喊着“三姨娘”一边攀上了杨玉瑶的床榻,杨玉瑶在安禄山的纠缠下,只能半推半就地从了。事后,她叹息道:“可惜你是胡人出身,无法成为宰相!”可安禄山却豪迈地回应:“宰相之位何足挂齿,要做就做皇帝!” 天宝六年那会儿,安禄山趁着夜色溜进了杨玉瑶的香闺,俩人就这么悄没声地搞上了。要说这杨玉瑶啊,可是杨贵妃的亲堂妹,杨家的大红人,唐玄宗疼得跟眼珠子似的。安禄山呢,本是个胡人,但靠着拍杨贵妃的马屁,愣是爬上了高位,跟皇族套上了近乎,权势那是噌噌往上涨。 杨玉瑶手里的银簪“当啷”掉在锦被上。 烛火晃得她眼晕,安禄山身上的羊膻气混着西域香料的味道,像团密不透风的网,把她裹得发慌。她抬手想推,却被他铁钳似的胳膊箍得更紧,胡人的眼珠在暗处亮得吓人,哪还有半分平日里给杨贵妃磕头时的谄媚。 “三姨娘当我是说胡话?”安禄山低笑,满是横肉的脸蹭过她的颈窝,“您在这长安城里,见谁的轿子比宰相的更威风?还不是那龙椅上的老头?” 杨玉瑶的指尖掐进掌心。她想起上个月兄长杨国忠跟宰相李林甫在朝堂上互啐唾沫,俩人争的不过是皇帝跟前多一句少一句的体面。可安禄山说这话时,眼神里的野气,像极了草原上盯着羊群的狼,根本不是争什么体面,是要把整个羊群都拖进狼窝。 “疯了。”她别过脸,声音发颤,“你可知这话传出去,杨家满门都得跟着你掉脑袋?” 安禄山却从怀里摸出个沉甸甸的锦盒,打开时晃得人睁不开眼——里面是颗鸽卵大的夜明珠,在烛光下滚着幽幽的绿。“去年我打契丹,从可汗帐篷里搜出来的。”他把珠子塞进杨玉瑶手里,掌心的粗茧磨得她皮肤发烫,“三姨娘你说,这珠子配不配做皇后的朝珠?” 窗外的梆子敲了三下。 杨玉瑶捏着那颗珠子,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往心里钻。她忽然想起刚入宫时,姐姐杨玉环拉着她的手说:“咱们女儿家,靠的不过是男人的疼惜。”那时她信了,靠着杨贵妃的光,她从蜀地一个小吏的女儿,成了长安城最风光的贵妇,连皇帝见了都得笑着喊她“三姨”。 可安禄山的呼吸喷在她耳后,带着血腥味的野心像藤蔓似的缠上来。“您以为杨家的富贵能撑多久?”他的声音压得极低,“李林甫恨杨国忠入骨,太子早就瞧不惯外戚专权,哪天皇帝老儿醒过神来,你们杨家……” 他没说下去,但杨玉瑶懂。就像去年冬天御花园里冻死的牡丹,前一天还被皇帝夸着“国色天香”,一场寒雪下来,连根都烂在了土里。 “我帮你。”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却异常清晰,“但你得答应我,若真有那么一天,不能伤我姐姐。” 安禄山笑得露出两排黄牙,把她往怀里按得更紧:“三姨娘说了算。” 第二日清晨,杨玉瑶对着铜镜描眉,发现鬓角多了根白头发。 她用镊子拔掉那根白发,看着镜中依旧娇媚的脸,忽然觉得可笑。前几日她还跟姐妹们比谁的胭脂更艳,谁的钗子更贵,如今却揣着个能掀翻大唐的秘密,连描眉都觉得手抖。 这时侍女进来回话,说安禄山派人送了些西域的葡萄,颗颗紫得发黑。杨玉瑶捏起一颗放进嘴里,甜得发腻,却带着股说不清的涩味。她忽然想起安禄山说的“做皇帝”,那口气里的理所当然,好像龙椅不是金铸的,是他家草原上随便搭的毡房。 可她又不得不承认,安禄山的话像根刺,扎进了她心里最软的地方。杨家的富贵是浮在水面的油花,看着热闹,风一吹就散。可若真能扶着安禄山坐上那个位置……她不敢再想,却忍不住对着铜镜里的自己,轻轻抚了抚鬓角。 后来安禄山回了范阳,每次派人进京,总会给杨玉瑶捎些稀奇玩意儿——有时是波斯的地毯,有时是突厥的弯刀。杨国忠见了总骂“胡人就是粗鄙”,却不知那弯刀的刀柄里,藏着安禄山写给杨玉瑶的字条,字歪歪扭扭的,却透着股狠劲:“三姨娘放心,我在范阳养的兵,比长安的麻雀还多。” 杨玉瑶把那些字条都烧了,灰烬混着胭脂水粉倒进荷塘。她依旧每天陪杨贵妃打马球,陪皇帝掷骰子,笑得跟从前一样娇俏。只是偶尔风吹过宫殿的飞檐,她会忽然想起那个雨夜,安禄山说“要做就做皇帝”时,窗外闪过的一道闪电,像极了要劈开这盛世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