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唐玄宗李隆基在神龙殿中绝食三日,默默咬碎玉碗,只说了一句:“告诉三郎,我在黄泉路上等他。”没过多久,唐肃宗李亨也吐血而亡。 那年,父子二人接连去世,一个曾经开创盛世,一个在乱世中掌权;一个被称为太上皇,一个坐在帝位之上,他们之间,既是血脉亲情,也是权力博弈。 盛唐的终局,就埋在这对父子的恩怨里。 李隆基的晚年,是一场缓慢而持续的失重。他年轻时意气风发,斩太平公主、肃清武周残余,一手打开开元盛世。那时候,他是帝国的象征。可到了天宝年间,他开始倦了。权柄开始下放,政务交给了李林甫、杨国忠等人,自己沉浸在笙歌与美人之间,整座长安城的节奏也悄悄变了。直到安禄山起兵,他才意识到,局势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安史之乱是一场彻底的动摇。兵锋所及,洛阳、长安相继沦陷。李隆基仓皇出逃,带着皇族与一千多名随从,朝着西南奔去。行至马嵬驿,军中兵变爆发,杨国忠当场被杀,杨贵妃也被逼自缢。一场荒诞又残酷的清洗,在逃亡途中完成,皇帝的权威在这次“家变”中碎了一地。而太子李亨——他的三郎,并没有跟着继续逃。李亨提出“分兵平叛”,随后带兵转向灵武,独自起事,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路。 那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未等李隆基首肯,便自立为皇。登基三日后,他才派使者将消息送往蜀地,语气恭谨,实则先斩后奏。这封“请安”的信,让还在成都兴庆宫里发罪己诏的大唐皇帝彻底明白:天下已经不是他的了。他没有动怒,也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但谁都明白,这话里不止有成全,还有彻骨的不甘。 表面上,父子并没有决裂。李亨尊李隆基为太上皇,每年节庆送礼问安,书信往来都称“臣亨谨奏”。但实际上,太上皇这个身份,像一个体面的外壳,遮住的,是一个被夺权后的孤独老人。他在成都依旧住宫殿,身边有近臣服侍,照旧饮茶、练字、听乐,但朝廷的节奏已与他无关。他虽在,却仿佛已经不在。 等到长安光复,李亨亲自派人迎接太上皇回京。过程庄重得很:三千精骑护送、百官列队、肃宗亲自到望贤驿相迎,甚至在见面时跪地抱足,泣不成声。李隆基也回敬了一出情深戏码,亲自披上黄袍,依旧风度不减。这一幕被史官记录得极其细致,写得像是一场父子重逢、帝位交接的典范。可这场面越煽情,越掩不住背后那种“你让我回来,但别指望我再插手”的冷意。 从那以后,李隆基居于长安兴庆宫,不再过问政务。肃宗对他的尊号越加繁冗,什么“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一个比一个好听。但实际上,他的旧臣、高力士、陈玄礼一个个被遣出,留下的,全是肃宗与李辅国信任的人。兴庆宫被逐渐孤立,消息闭塞,太上皇也慢慢发现,自己身边的每一层都成了笼子。 李辅国的角色不可忽略。他原本只是李隆基身边的一个宦官,谨慎、机敏、极有眼力。可到了肃宗朝,却摇身一变,成了搅动朝局的关键人物。他劝肃宗说,上皇住在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谋不利于陛下”。这话一出口,整个气氛立马变了。太上皇的马匹被扣,出行受限,连一个旧人都不能探望。他从昔日君主变成一个“需要监控的对象”,外界已经开始用“幽禁”二字来形容他的处境。 最让李隆基感到屈辱的是“搬宫”一事。他原本住在熟悉的兴庆宫,那里有回忆,有习惯,也有尊严。可李辅国奉旨让他搬到西内,那是一处偏僻得连太监都不愿常住的地方。他坐在车上,听到消息,整个人震得发呆,甚至差点从马上摔下来。他没有抗命,但从那天开始,他不再进食。他只说是“辟谷”,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心灰意冷。 不吃荤,不问事,不发话。他把自己关在神龙殿,任谁劝也无动于衷。时间一天天过去,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旧臣被贬、宫女被撤,他像被掏空了一样,只剩下躯壳。762年四月,他终于在沉默中死去,终年七十八岁。他临终前说了句“告诉三郎,我在黄泉路上等他”,像是在索命,又像是在追问。 这句话不到两周后便应验。李亨也病倒在宫中,吐血身亡。他在位七年,从兵乱中走出,却始终未能摆脱内外困局。父亲死了,他也撑不住了。两人前后脚离世,一位曾是盛世的奠基者,一位是乱局中的平衡者。但他们谁都没活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他们之间没有公开冲突,没有刀兵相见,可政治的杀伐比刀剑更致命。他们是父子,但更是帝位的竞争者。李亨夺位成功后,不敢让父皇留有权力;李隆基退位后,不甘心失去影响力。礼法、孝道、天命,在这场角力里都成了用来包装现实的外衣。骨子里,是防备、算计、孤立、消解,直到把彼此都推向了末路。 盛唐在他们手中终结。不是因为安禄山,而是因为宫廷里的亲情早就烂掉了。那些看似隆重的仪式、热泪盈眶的叙礼、洋洋洒洒的尊号,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李家父子,一个在忍,一个在逼,一个咽气,一个吐血。 唐朝还会延续几十年,可开元盛世那种从容气度,从这对父子的死开始,就再也没回来过。历史是靠人撑起来的,人倒了,气也就断了。 盛唐的骨,埋在马嵬驿那场变乱里;盛唐的魂,散在神龙殿的那口绝食气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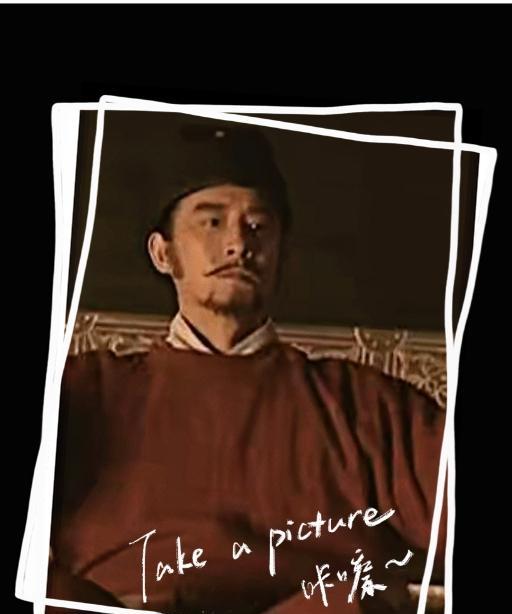
评论列表